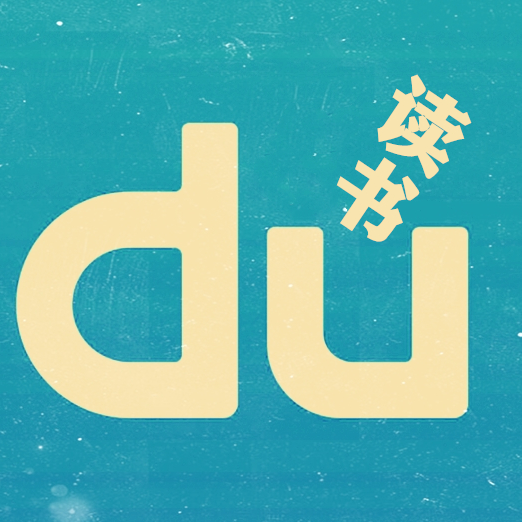别说读书苦,那是你看世界的路——
晚上群众大会的会场,照例在清风店的小学校。宽大的教室里,房梁上高悬着两盏大玻璃罩子煤油灯。火炉烧得轰轰响,老曹克星坐在主席台上,手端着一根猫眼儿绿翡翠嘴儿大白铜锅长杆儿烟袋。烟杆上,还挂着有颗翡翠坠子的绣花烟口袋。头上端端正正戴着一顶狐狸皮帽子。被那挂在房梁上的大玻璃罩子煤油灯,照耀得如同火焰一般红。
瞧他敞披着老羊皮袄,浑身上下都表现出一种全村“老座儿”的庄严气派。来会场之前,他到家里打了个照面儿,吩咐闺女在家照看母亲,不必参加今晚的群众大会了。他觉得这丫头不太保险。
已经抽过四、五袋烟,喝掉半壶开水了,可是抬眼打量一下会场,竟是空空荡荡,连段顺全家都算在里头,数个来回儿,还不到七八个人。借口回家堵鸡窝,关二门楼子,还溜掉了两个。
“要么陈贵呢?”老头子脸上带着不满意的神色,大声说,“这半天还没有把人召集来?”
“别着急,”离主席台不远的老段顺满有把握地说,“谁家吃了饭,不得洗刷碗筷,堵堵鸡窝什么的?刚才我来,陈贵正在街上喊叫人哩!”说完端起肩膀,往鼻子里揉了一撮鼻烟,然后探过身子去,拿手指头弹了一下蓝瓷鼻烟壶,在老曹克星伸过来的手心里,倒了一小撮,老头子拿一个手指头在手心里点了点,便吸溜着揉进鼻孔里去了。他偏脑袋,仄起耳朵,眨巴着眼睛,说:“怎么听不见陈贵喊叫?”
陈贵喊破了嗓子,不见有人出来,便亮着手电筒,挨门挨户地去招唤了。“喔嚯!”走进一家院里的时候,在什么物件儿上绊了一脚,差点跌倒,跳到一边,“今儿晚上咋这不顺当!——我说,你们怎么还不去开会呀?”他闪出电筒的白光,在那有许多人影的窗纸上晃了晃,高声说着走进屋里,见满满一炕人,有的在嗡嗡地摇着纺车,纺线,有的稀拉哗啦搓玉黍,有的纳鞋底子。

“还不快去开会!”陈贵在地上跺脚喊叫说,“怎么不知道今晚上叫你们给常四起提意见?”
妇女们都互相交换着眼色,一个女子一边拿针锥子扎着鞋底子,回答说:“快喊有意见的人去吧。我们去了也就是白占地方罢了!”
陈贵往前跨了两步,两眼扫视着人群,着急白脸的,拿巴掌拍着炕沿说:“常四起不报灾,大伙少分多少粮食?就这一条儿吧!”
立刻有人打断他的话:“要我说,受灾还超产了几成,这是清风店的光荣。”
陈贵直瞪着眼睛,在脑子里寻找反驳的词句,转念一想,他还有紧急任务,不得不压下心头的火气,温和地劝说道:“快去开会,听听别人的,你们就明白啦。”
“我说陈贵咋这积极呀!”有人用拖得长长讥讽的语调说,“一个劲儿往里直掺合!”
立刻有人脸上装出神秘的表情,两眼环顾着人群,用报告重要新闻的口气说:“怎么你们不知道?人家马上就是副队长啦!”
说的陈贵晃动着头发蓬松的脑袋,脸上一阵红,忸忸怩怩,好像是害臊,其实心里很得意。忍不住咧开嘴巴笑了笑,便转身掀帘子跑出去了。从院里送来他半带命令半带威吓的声音:“快去开会!要不曹队长生气啦!”
陈贵转悠半天,也没有喊动几个人。无法交令,傻小子混充聪明,来到会场,瞪着眼珠子瞧瞧一排排空空荡荡的座位,跑得流汗的脸上,装出吃惊的神情说:“嘿?没有来?都说随后就到吗!”
老曹克星拧着眉毛,沉默了片刻,摆了个姿势,脸上现出有权威的神情,大声命令陈贵:“再跑一趟,告诉大伙儿,谁来开会,给他划十个工分儿!”
这回,虽然没有像老曹克星猜想的那样,挤破了门,倒也来了一二十个,稀稀散散地坐下来,抽烟,说话儿,就不算太冷落了。
民德老汉在离主席台远远的黑灯影儿里,刚坐下来,就有人在他耳边说:“你不是说不来吗?”
民德老汉往后闪着身子,眨着眼,瞧瞧那人,嘿嘿的笑着说:“怎么,兴你白捡十分,就不兴我白捡十分儿,大长的夜,哪儿不是呆着。”
老曹克星拿烟袋锅,当当地敲着桌子,大声说:“静一静,静一静!”
常四起来了,穿一身青布棉袄,为了不让风钻到里面去,腰间系了一条搭包。他一边迈着缓慢沉稳的脚步,往主席台前走着,一边把头上狗皮帽子垂下的两个耳山推上去,在他有如少女一般长长睫毛的阴影里,两眼扫视着西边的人,带着尊敬的笑容,向老年人问好,并回答别人的话。他在老曹克星侧面的板凳上坐下来。向老曹克星说了声“开会吧!”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片裁好的卷烟纸和烟口袋。默默地用冻得发麻发痛的手指,往纸上撒烟末,却不看曹克星。
而老曹克星,一声不响的,用那种敌视的目光,盯着常四起,足有三分钟,这才宣布开会。
“大家给常四起同志提了不少意见,”老头子站起来,把狐皮帽放在坐位上,端正着姿势,极力把语气说得温和,“今天常四起同志回来了,大伙儿有意见继续提!”说着,脸色不由的庄重起来。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有意见大胆地提呀!”他用带有明显鼓动性的语气说。但是,全场沉寂,没有人说话。
“我说两句,”段顺说着站起来,一边躬起背把鼻烟壶塞进内衣的口袋里,“我是拥护常四起同志的,可以说哪儿都拥护!他躲开老曹克星惊讶疑问的目光,把脸转向全场。“就是有一件事我不拥护,为什么常四起不向国家要救济粮?还给国家缴征购?请问,这是为什么?”为了帮助说话的语气,他朝前探着身子,脑袋使劲划了个圆圈,“常四起同志在上级面前得了脸,我们清风店各户,可就少分不少的粮食啦!”他拍响着巴掌说。会场有了低语声。
常四起吸着烟,蓝色的雾,在他头上飘荡着。嘴巴上挂着一丝几乎辨察不出的镇定和轻视的微笑,默默地,两眼直望着段顺。
老段顺给常四起深深一眼,直瞧到自己心里。他有些慌乱了,乱眨着眼睛,嘴里嘟囔着坐了下去。
“我唯一的错误,”常四起心里说,“就是仅仅撤销了他的会计职务,没有在群众面前揭露他……”
会场又变得沉寂了,可以清楚地听见有人把烟袋抽得吱吱叫。老曹克星咳嗽了一声,用暗示性的目光,向陈贵盯了一眼。陈贵便好像被碰动了机关的机器人儿,腾地站起来,拿出羊顶架的姿势,眼盯着常四起说:
“我有意见:为什么他当上村书记以后,把段顺表爷的会计撤掉,换上郑雨山?除了亲属关系,郑雨山的父亲给常四起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是不是受贿?”
“注意,”曹克星插嘴说,“都听见没有?这是丧失革命立场的行为呀!”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管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