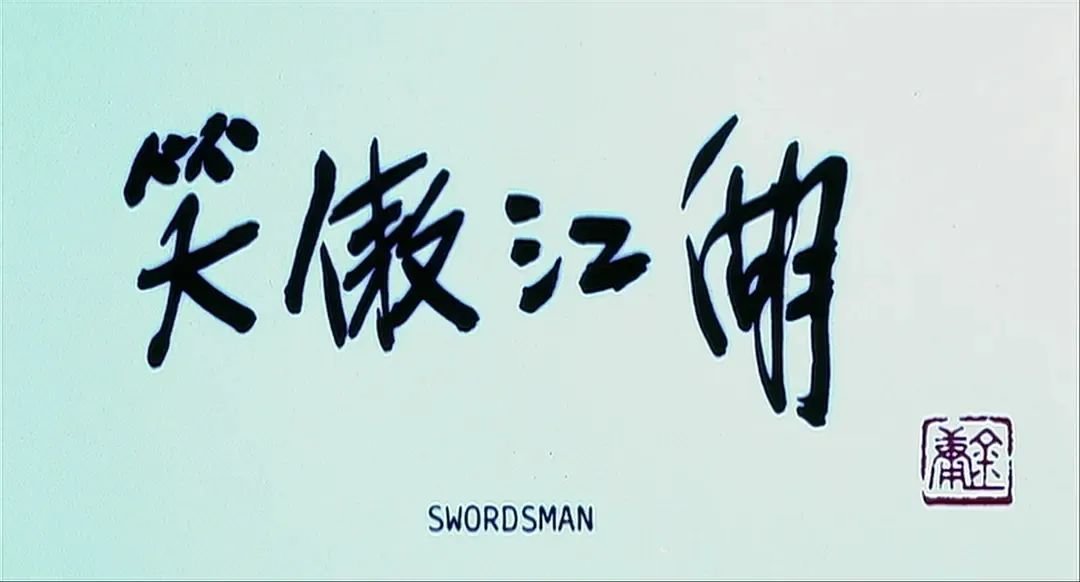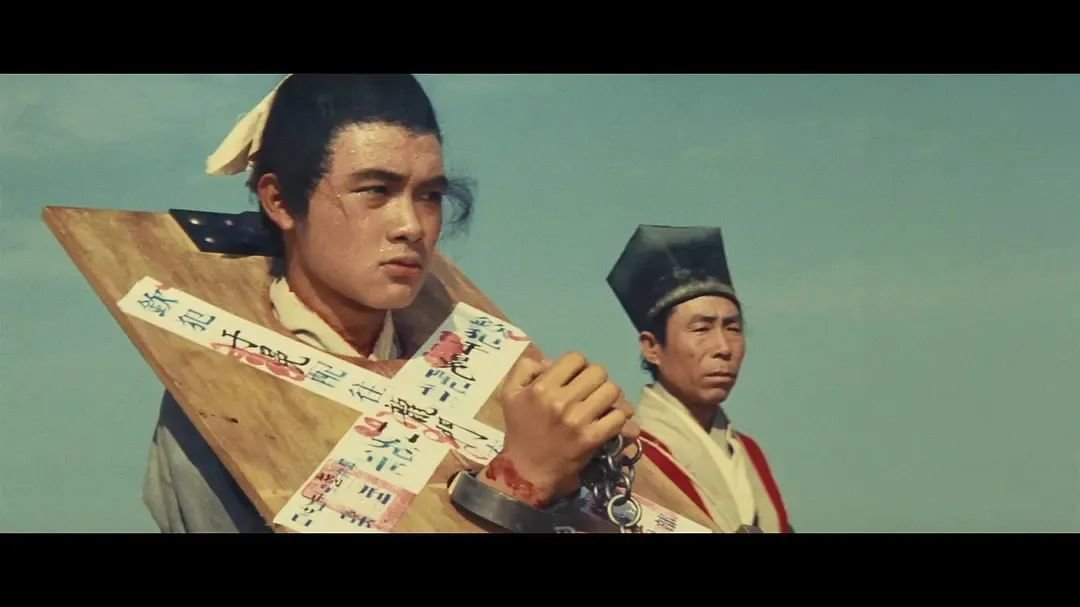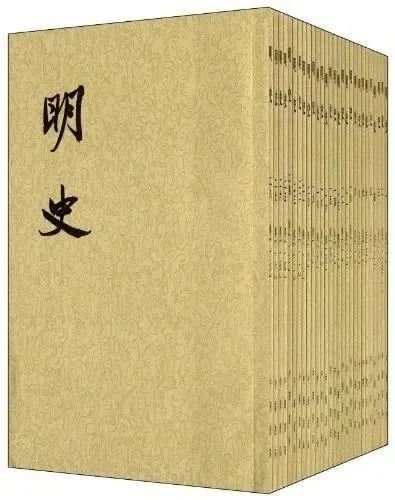1990年,电影《笑傲江湖》于1月和4月在中国台湾、香港上映,票房分别是1800万和1600万,在《赌圣》《赌侠》以4000万票房雄踞冠亚军的当年,不算亮眼。

时年四十岁的导演徐克却因为这个武侠大热IP惹恼了两位老人。
一位是小说作者金庸,电影《笑傲江湖》勉强接受,到了第二部《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气得金庸放出话来“朋友照做,但版权不会再卖给徐克”。
另一位是署名电影《笑傲江湖》导演的胡金铨。
他本是被徐克作为前辈偶像请来当导演,没想到不欢而散。
胡金铨被气得住院,义兄李翰祥直接宣称“宁可饿死,也不和徐克合作”,而徐克接受采访时则说,拍《笑傲江湖》最大的错误就是请了胡金铨。
《笑傲江湖》是香港新旧武侠片的分水岭之作,也是旧式武侠片导演胡金铨与新式导演徐克的唯一一次合作。本来可以成为新老携手的影坛佳话,结果成了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
肉眼可见的是,由《笑傲江湖》开始,胡金铨正式退出武侠片创作,而徐克开启了武侠电影新征程,成为港片武侠的执牛耳者。
当下的观众,记住了《笑傲江湖》之后的徐克,淡忘了《笑傲江湖》之前的胡金铨。
徐克如同步步开挂的令狐冲,成了冉冉升起的新星,如今年过古稀仍奋战长津湖,铆足劲想拍金庸的另一部小说《神雕侠侣》。
胡金铨如同退隐思过崖的风清扬,要靠着新星的传颂才得扬名。其后一直生活在无投资和被遗忘的落寞中,直到1997年去世。
影评人文白说“最终,我们还是‘遗弃’了胡金铨”。
如果仍健在,他今年刚好90岁,也许会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样在光影大地上继续耕耘,将每一部电影都拍成代表作。
1、聚气
1932年,火爆一时、风头无两的系列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被一纸禁令叫停,执法依据是1930年公布实行的《电影检查法》,执法机构是电影检查委员会。
三年之内连拍18集的“火烧红莲寺”至此偃旗息鼓,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被《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扣上了“内容荒诞不经”“以免流毒社会”的帽子,谈武侠而色变。
正是这一年,影院林立的北平胡门望族添了一位男丁,取名胡金铨。
谁也不会想到,在武侠电影极度萧条甚至成为禁忌的年头,竟然迎来了一位日后重整武侠乾坤的电影大师,将被404的武侠题材拍成了yyds。
不过直到去香港之前,胡金铨从没想过自己会和电影发生联系。虽然他爱看戏,父亲胡源深是长安大戏院的股东,胡金铨自幼就把京剧看个饱,而且深深爱上了京剧。
成年之前,他一直都过着读书看戏的少爷生活。
将满18岁,只身出门远行,脑袋里装着老北京的戏曲记忆,手中提着沉甸甸的三箱书籍。戏曲与书籍后来成为他拍电影的灵感和考据源泉,也是胡金铨电影能够传世的文化符脉。
从来到香港四处打杂到跻身邵氏四大导演,胡金铨用了16年时间,靠一部打开新武侠电影大门的《大醉侠》。
每一代都有新与旧,在1960年代,胡金铨是新人,他的《大醉侠》一如1990年的《笑傲江湖》,成为新与旧的分水岭。他颠覆了此前盛行的神怪武侠片和黄梅调电影,重新定义了武侠片。
1966年上映的《大醉侠》是胡金铨在《大地儿女》(1965年)票房惨败之后的逆袭之作,当时邵氏掌门邵逸夫对这部标新立异的武侠片并不看好,险些烧掉底片。
看惯黄梅调的邵逸夫,对胡金铨的京剧技法嗤之以鼻,却不知胡金铨正在成为武侠片的新生代盘古。
《大醉侠》将胡金铨自幼看饱热衷的京剧元素淋漓地发挥出来,人物有脸谱设计,陈鸿烈扮演的反面角色像曹操一样脸部涂白,既符合“玉面虎”绰号,也符合奸诈人设。
故事大部分场景空间是在封闭的客栈之内,开启了胡金铨的“客栈宇宙”。胡金铨是带着对京剧的热爱和钻研来拍电影,他最常提及的一部戏就是《三岔口》——经典的客栈戏范本。
狭小有限的空间放大了矛盾冲突的张力,打斗场面集中爆发,热闹好看。也可借助门窗暗格的视觉误差,展开捉迷藏式打斗。
打斗场面靠京剧鼓点烘托,快慢缓急都可做衬。金燕子进入客栈,与群贼的较量,完全搬来京剧的念、做、打,无唱。每人发招前,要说一句隐含招式的念白。如果以铜钱为武器,就说“该我请客”,出招之后,还需摆个造型。
有传统,也有创新,胡金铨在打戏上强化了轻功的设计,现场用弹床,后期用剪辑,制造出飞檐走壁的视觉效果。
弹床加蒙太奇,成了胡金铨武侠片的固定配置,即便后来威亚满天飞,胡金铨只在《画皮之阴阳法王》中少量运用,能不用钢丝就坚决不用,固执坚持原来的配方。
凡此种种,初显了胡氏武侠片的拍摄范式。从《大醉侠》开始,客栈成为常见场景和意象,京剧鼓点成为打斗标配。
胡金铨首创武术指导制度,启用武术指导韩英杰,二十多年间,胡氏武侠片几乎都由韩英杰设计动作。因此,胡金铨的打戏一直保持同样的套路、风格、水准。
胡金铨自承他的打斗不是功夫和格斗技,是京剧的电影化处理,不是武功,而是舞蹈。
如果说《大醉侠》是胡金铨的武戏发轫,那么次年推出的《龙门客栈》(1967年)在延续了《大醉侠》武打操作的同时,更成为胡金铨电影文戏的蓝本,“考据狂魔”正式上线。
为了还原电影中的明朝服化道,胡金铨翻阅的资料包括《古今名画300种》《古今名画大观:人物画册第二集》《春游晚归图》《风壑曳舟图》《桐阴清居图》《西山雪霁图》《仿唐人人物画》等,生生将武侠片拍成了历史片,连明史学者都竖起大拇指。
除此,胡金铨也显露了“等云达人”的本色,《龙门客栈》的结尾,因为看到一片难得的云海,一定要将这片云海拍进去。此后,等云等风等太阳,成了胡金铨电影剧组的常态。
《龙门客栈》1967年10月21日在台北上映,3家影院联映5周,总收入达445余万元,成为卖座冠军,打败了同期上映的《音乐之声》。
但《龙门客栈》也埋下了胡金铨电影不再卖座的伏笔,尤其是“考据癖”和“等云症”两个属性,拉长周期,增加预算,票房易失利。果然到《侠女》(1970年)开始折戟。
2、倾心
《侠女》拍摄三年,当年香港票房67.8万,可谓不佳,却是胡氏打斗的巅峰之作,地上打斗除了京戏风格,加入了排兵布阵打法,同时升级了空中的轻功视觉。
后来被李安、张艺谋致敬的竹林大战即源于此片,惊艳的蒙太奇剪辑一举获得第二十八届戛纳电影节技术大奖。
《侠女》让胡金铨此后的武戏处于重复状态,那段经典剪辑,在《空山灵雨》中再次用在曾经主演《侠女》的徐枫身上,在《忠烈图》中用在洪金宝身上。
洪金宝当过韩英杰的副手,但“七小福”的参与对胡金铨的武打并无改变。后来演员徐枫变身制片人,希望邀请程小东担任武术指导,胡金铨极力反对,他对所谓的新派设计不感兴趣。
虽然程小东、洪金宝这一代的武术指导都有京剧功底,但他们的招数和风格绝不是胡金铨想要的京戏范式。
胡金铨拒绝程小东不止一次,尽管他和程小东的父亲——导演程刚很熟,程小东很小就在胡金铨的电影中亮相,《大醉侠》中被匪徒刺瞎眼睛的小和尚就是程小东。
后来徐克邀请胡金铨拍摄《笑傲江湖》,胡金铨坚决抵触程小东做武术指导,坚持要自己拍,徐克力荐力保,胡金铨才勉强同意,此是后话。
《忠烈图》之后,胡金铨等于放弃武侠片拍摄,直到联合执导《大轮回》(1983年)时,才重拾武侠题材。
其间创作的《空山灵雨》《山中传奇》更是彻底“放飞”,将山水写意、哲学禅意、镜头诗意熔于一炉建构电影世界观,以“考据癖”和“等云症”作为执行方法论,将作者属性推向极致。
他成了纯粹的风格美学大师,虽然谈论电影时,他将故事放在首位,但更强调“意念”,最后才是故事的讲法和演员,电影要为“意念”服务,因此他以梵高的“印象派”自况。
《空山灵雨》尚有顺叙的故事,讲述权力斗争,放大了《侠女》中超长的鼓点奔跑戏,在寺院、深林、山崖,都植入大段奔跑,以空间扩展填充着时间飞逝。
取材自《西山一窟鬼》的《山中传奇》,片长3个小时,后经删减才得上映,嵌入了补叙、插叙的讲述,充满了大段的自然万物镜头和冗长的击鼓斗法情节。
为了辉映男欢女爱的激情,交替出现了蜻蜓、荷花、水塘、云彩等画面,暗示女鬼作祟时,又出现了色彩斑斓的交尾蜘蛛。
这次胡金铨将隐藏于画面外的鼓“请”到了画面中,成为神妖斗法的道具,击打起来可以持续几分钟之久,完全消解斗法的感官热闹,必须作为内行才能品出鼓点的门道。
《空山灵雨》《山中传奇》两部风格巅峰之作,均在1979年香港上映,票房分别是129万和73.5万。这一年,一直自认是胡金铨徒弟的许鞍华,导演的“新浪潮”作品《疯劫》票房210万。
同为“新浪潮”导演的徐克拿出了处女作《蝶变》,票房115万。徐克自称胡金铨的迷弟,大学论文研究的就是胡金铨电影,评价胡金铨的武侠片“惊为天人”。
但《蝶变》并未看出他对胡金铨的继承,且大量使用了胡金铨极其反感的钢丝。炸药成了终极武器,这在胡氏电影中只是特效,绝对不会成为武器,哪怕是以抗倭为主题的《忠烈图》,仍是刀光剑影、飞镖弓箭。
醉心于个人风格的胡金铨应该没看过这部《蝶变》,更不会想到这个崇拜自己的后生仔以后会让自己如此头疼。
二人的交锋在《笑傲江湖》之前就已有端倪,1983年,胡金铨执导的《天下第一》上映,这是胡金铨文化考据的集大成之作,除了服化道高度还原五代时期,更还原了古人行医、作画的真实细节。
他最得意的是“天下第一神医”边诊断边唱歌的段落,大夫会将病症、用药剂量、诊费“唱”出来,这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也是其他古装作品绝无仅有的,胡金铨有首创之功。
但这部电影因预算和档期而草草结尾,剧情戛然而止,让胡金铨郁闷良久。据说一个紧要因素在于,有一部香港武侠片要赶在《天下第一》之前上映,就是徐克执导的《新蜀山剑侠传》。
果然,两部电影都于1983年2月在台湾上映。二者都是古装片,都是武侠片导演作品,都借鉴了敦煌壁画的创意。
《天下第一》的开场就是在敦煌壁画前唱词,而《新蜀山剑侠传》以敦煌壁画来布景造型,林青霞的装扮俨然破壁而出的飞天神女。
《新蜀山剑侠传》还请来了震撼全球的“星球大战”制作团队,依靠西方科技打造奇幻景观。
当胡金铨一头扎进东方文化不可自拔,力图用电影展露文化之魂时,徐克等人的电影中已满是西方之技的光怪陆离,当我们试图挖掘光怪背后的文化韵味时,胡金铨竟成了文化的介质。
3、夺帅
1983年之后,胡金铨几乎无戏可拍,直到1988年,徐克找上门,邀他拍《笑傲江湖》。
按照胡金铨的说法,徐克之所以邀请他,因为他和金庸是老友,金庸希望他来拍。徐克是借胡金铨之名来赚金庸授权。版权到手,老胡赶走。
徐克开始大包大揽,横加干涉,光剧本就写了十六稿,完全架空了胡金铨的主导权,正应了小说《笑傲江湖》的第三十四章标题——夺帅。
胡金铨希望将《笑傲江湖》设定在明朝,虽然原著没有明确朝代,但有迹可循便是明朝。《葵花宝典》是太监所著,与《龙门客栈》里白鹰扮演武功奇高的曹少钦如出一辙。
文武戏都合拍,而且他觉得自己以往拍的武侠片描写太多政治斗争,这一部要“更浪漫”。
结果,胡金铨的“考据癖”和“等云症”再次发作,于是胡导演等云等太阳的故事讲述人,由倪匡、蔡澜、李翰祥,扩充到了徐克、程小东,徐克还加上一句“黑泽明也喜欢等太阳”。
将胡金铨与黑泽明并列不是徐克胡诌,早在1978年,胡金铨被英国《国际电影指南》评为当年世界五大导演之一,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国际最出色50位电影导演之一,仅有三名亚洲导演入选,其他两人是日本的黑泽明与沟口健二。
但正如黑泽明不被投资方喜欢一样,胡金铨遭际相同,哪怕资方自称晚辈,仍对他的拍片方式无法认同,电影里的故事推进慢,电影外的拍摄进度慢,后辈果断接手,以“唯快不破”的观念替代了“慢工细活”的意念。
《笑傲江湖》最终署名胡金铨、徐克、程小东、许鞍华、李惠民、金扬桦。虽然保留了胡金铨的部分印记——开场的针线绣花、长队的跋山涉水,但也抹杀着胡氏印记。
正如剧情中的两次弑杀,张学友扮演的欧阳全用火枪打死了刘洵扮演的古今福,许冠杰扮演的令狐冲用独孤九剑击败了刘绍铭扮演的岳不群,这种具有“弑父”意味的情节几乎不会在胡金铨电影中找到。
纵观胡金铨的电影,父亲是缺席的。《大醉侠》中“金燕子”的哥哥被强盗所掳,负责营救的不是手握重权的父亲,儿子直接说父亲不会管自己,结果只有妹妹孤身营救,父亲自始至终没有露面。
《龙门客栈》《侠女》中,主人公要么是为了解救失去父亲的忠良之后,要么自己作为忠良之后偷生世间。《忠烈图》中的抗倭虽有君王开场,但没有君父观念;
《空山灵雨》虽有师父,但师父的影响感化已经清零,更多的是如何取代师父、成为师父;《山中传奇》的两个厉鬼家庭只有母亲,没有父亲。
“无父”的意象贯穿于胡金铨的电影中,所以才有了暂寄身躯的客栈,风吹涛响的山林,渺茫无界的天地。
人在客栈无法久留,在山林奔跑穿梭,在天地渺小如蚁,暗合了胡金铨自离开北平之后去国怀乡的飘零心境。
他说自己是“过客”“难民”和“中间的人”。最后一部作品《画皮之阴阳法王》建构了一个“阴阳界”,孤魂野鬼在这里既无法成佛,也无法做鬼,只能漂泊幻灭。
这是胡金铨的乡愁写照,在《他乡与故乡》中,“流浪在美国”的胡金铨无法确定故乡的方位,说香港是故乡,也要加一个“算”字。
或者可以说,胡金铨已经用一部电影标题官宣了故乡,那就是《大地儿女》,大地是父母,是故乡,无远弗届,标注不出具体方位,就做一个天地孤鸿。
这只孤鸿虽然躲开了原籍故乡的政治冲击,但对政治运动和权力机关的恐惧如影随形。
他电影中的政治斗争极少斗争过程,多是斗争结果,作为强权象征的锦衣卫、东厂制造出铺天盖地的恐怖阴影,是胡金铨口中的“支配阶级”,被支配的恐惧充斥着他的作品。
即便侠客们能够手刃鹰犬,也只是暂时胜利,阴影从未消除。
胡金铨最沉迷的时代是明朝,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时代,也是间谍战最激烈的时代,他希望揭露间谍战的愚蠢可笑。
而可笑的内核是以可怕作为表象,胡金铨对于权力机关的生杀予夺既恐惧也厌恶,连带讨厌起俨然取得杀人执照的詹姆斯·邦德。
对于政治与强权,他既有不得不反抗的志气,也有战胜不了的悲观。
他成了《笑傲江湖》中的“潇湘夜雨”莫大先生,对政治过程心照不宣,对政治结果心知肚明,不满但无法改变,只能寄情于高山流水,琴中藏剑,剑发琴音,不求快意闻达,只求在乱世中做个有坚守有寄托的君子。
4、传剑
这样的纠结无奈,在徐克这一代导演这里已经剥离了历史的沉重,转化成都市化的文艺抒写,徐克翻拍自《龙门客栈》的《新龙门客栈》,虽然也是“救救孩子”的主线,但徐克借梁家辉扮演的周淮安之口说出了“这个没名没姓的时代”。
如果说胡金铨的作品执着于通过文化寻根溯源而索引姓名,那么徐克取消了姓名的索引功能。姓名需有父源,是历史和文化的乡愁,已经完全融入现代大都市的徐克,已无这样的乡愁。
他的传统文化展露更多源于胡金铨电影、金庸小说的“二传手”。
《新龙门客栈》里运用了《三岔口》的暗室打斗桥段,但灵感来源绝非《三岔口》,而是化用《三岔口》的胡金铨电影,正如很多读者知道“问世间情为何物”是源于《神雕侠侣》,而非元好问。
自《笑傲江湖》分道扬镳,胡金铨既被徐克一代所抛弃,更为徐克一代所汲取。正如《笑傲江湖》中古今福、岳不群可以被抛弃,但风清扬始终是神一般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胡金铨的演员班底随胡金铨退出而退出,扮演林震南的岳华连补拍都不愿意,只好换了演员甘山。
胡金铨“旧部”只剩下扮演风清扬的韩英杰,作为胡金铨的御用武术指导,这次是在后辈程小东的指导下施展“独孤九剑”。
新旧两代之间,并非决然的泾渭分明,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对应和融合。
比如《新龙门客栈》与《龙门客栈》《迎春阁之风波》的故事空间设定,《倩女幽魂》《青蛇》与《山中传奇》的奇幻鬼怪纠葛,《智取威虎山》与《忠烈图》的剿匪卧底桥段,《棋王》与《终身大事》的城市症候把脉。
再早一点的《新蜀山剑侠传》与《天下第一》的敦煌美学重现,《刀马旦》与《大醉侠》的京剧角色化用。
胡金铨首创的东厂服饰、藤编书箱被后世无数次沿用,包括徐克。
胡金铨的拍片技法和题材设定,也在李安、侯孝贤、许鞍华、张艺谋、贾樟柯、路阳等人的作品中频繁闪现,才有了《卧虎藏龙》《刺客聂隐娘》《江南书剑情》《十面埋伏》《天注定》《绣春刀》。
李安说“胡金铨的影响不只是电影的武戏,更是中国影像的塑造”。
纵览胡金铨电影,无法单纯地定位他是武侠片导演。从他想拍而未拍的作品来看,包括《武松醉打蒋门神》《华工血泪史》《利玛窦传》《咆哮山村》《毒药》《深海的战争与和平》,也是题材多样、类型多元,《深海的战争与和平》还是一部动画片。
胡金铨去世于1997年,在香港票房榜单上,仅存的武侠片硕果是《黄飞鸿之西域雄狮》。导演是曾经出演过胡金铨电影的洪金宝,监制、编剧是徐克。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华工戏份,而胡金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拍成《华工血泪史》。
只是这已是不同历史维度的华工群像。如果说胡金铨是由过去到当下顺叙来呈现历史,徐克则是用由当下向过去倒推来讲述“中国往事”,用的是截然相反的方法论。
风清扬虽然传授了“独孤九剑”,令狐冲还需要有吸星大法、易筋经傍身;莫大先生在乱斗之中无法所向披靡,但一曲《潇湘夜雨》始终未成绝响。
胡金铨是武侠电影的传剑者,也是作者电影的长奏者。剑光乐声中,传递着他对电影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他给自己学生许鞍华的信中有四字激励——“宁静致远”,要拍出可以媲美瓷器、丝绸的好电影。而香港才子蔡澜在悼念胡金铨时写过“老友是古董瓷器,打烂一件不见一件”。
胡金铨本人就是瓷器,他的作品亦是瓷器。在时间黄土的掩埋中,坚硬的铜铁会腐烂,而瓷器始终如新,供一代又一代的人摩挲鉴赏,成为无价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