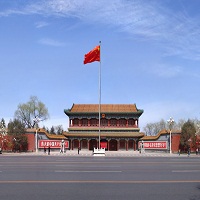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是大道,后来者需要注意什么误区
财经纵横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是不是在研究当中放进了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我的看法不是。因为我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这才叫新结构经济学。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这才叫新结构经济学。如果你的研究不是去研究结构是怎么决定的,是怎么演变的,也就是没有把结构内生化,即使你放进结构,那你也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它还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就像拿个比喻讲,今天金刻羽教授提出的模型是有结构的,假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跟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一样。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新结构经济学?不是,因为这个模型没有把结构内生化,是把结构假定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的。我是强调必须把结构内生化,也必须把结构的演化内生化。当然我这个定义是比较窄的,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定义是有目的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在经济学里面当然有人去研究结构的内生化,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几种方式。比如说用技术偏向性,就是阿西莫格鲁的论文;也有用家庭偏好的差异性,来推导出不同的结构,把结构内生化;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那么为什么要用要素禀赋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文献,可能还有其它的,都可以去内生产业结构。因为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是结构的内生性,还研究结构的演化的内生性。那你要想,从技术偏向性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可以说有一个结构有内生,它由技术的偏向性决定,但你很难由这边来推论将来的产业结构会怎么演化。另外,你比如说从家庭偏好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偏好到底应该是给定的,也许有差异,但是一把它给定以后你就没有办法研究将来的产业结构等等的演变。
我想,从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来内生化的产业结构,并且由此推动结构的变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在每一个时点上是给定的。我们做任何研究分析,必须从一个给定的参数作为切入点,才能去内生那个时点的很多其它东西。如果这个本身是内生的,那你就没办法去内生其它东西。
它还有一个好处。昨天有人讨论说,是不是国际资本流动以后,要素禀赋给定这点就能推翻掉?我觉得不能推翻掉。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往发展中国家流动,但绝对不会流动到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的程度。因为这是违反理性的。你比如说,发达国家的资本一定是有人拥有的,然后他在配置资源上面的目的是什么?回报的最大化。如果说他到发展中国家来的话,怎么样让他的回报最大化?一定是到发展中国家中,能够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劳动密集型。
所以,绝对不会说,发达国家的资本拥有者流动到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这是违反理性的。我当然知道在很多模型里面,它是假定国际资本可以流动以后,人均资本就不重要了,可是这样的一个假定本身就违反了新古典最基本的理性原则。
因此,即使国际资本可以流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禀赋结构来说,这是可以忽略的。就像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为了验证重力加速度,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假定没有空气阻力,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现在从要素禀赋出发,假定在每个时点上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给定,即使有国际资本流动也可以舍项掉,因为它不会根本改变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的不同。然后,我们研究的是发展,很需要(变量)的一点是每一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是随时间是可以变化的,如果不能变化,那么即使这个变量非常重要,但是也无能为力。就像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为什么北美发展比较好,拉丁美洲发展比较差,他当时的一个假定就是,在拉丁美洲因为气候非常热,去的时候死的白种人很多,每个人活的概率非常小,所以在殖民的时候就要大量的掠夺,形成了掠夺性的制度安排。
北美的国家天气较好较温和,落脚在那里的人都能活着,能够一起工作,就形成了一个社区的、相互帮助的、权利界定清楚的制度安排。他也可以写一个模型,好像也很有说服力。假定他是对的,拉丁美洲的人就永远没希望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时光机器可以倒回去四百年前,而且还要说服上帝把北美的天气改到拉丁美洲去,你说有办法吗?如果没办法,知道了也没用。但是如果我们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因为资本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不能变化的,但是随时间可以变化,这就让我们有个抓手来改变这个结构。
第三个是最根本的。我们经济学家分析问题,一般最重要的(工具)是income effect(收入效应)跟substitution effect(替代效应)。比如张五常常讲说他只有一句话,就是substitution effect,相对价格效应。因为他研究的都是比较微观的问题,也不是长期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他只要看substitution effect就可以。但是我们研究长期发展的问题,那就还有income effect(收入效应),这两个效应其实是除了像研究statistics(统计学)或者做econometrics(经济计量)那种方法论的之外,所有经济学家作分析,不管再复杂的理论或是概念,到最后不是讲income effect,就是讲substitution effect,也就是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同时决定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总预算,跟它们的相对价格。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和分析参数。
再从马克思来讲。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是生产方式、生产结构。但是马克思还只是从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的经济基础,来研究组织等一系列的上层建筑,但是生产结构是怎么决定的?要素禀赋决定的嘛。所以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我完全是从经济基础开始,只是从经济基础的更基础,把生产结构生产方式都内生化。所以这里继承了新古典,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新古典,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那为什么内生性很重要,为什么我强调必须去研究内生性?因为不研究内生性,经常会误导。前面提到金教授的研究,但如果这个模型是对的话,发展中国家同样无能为力,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注定流到发达国家去,去帮助发达国家。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型没有解释现象。你们想想看,为什么发展好的国家,它并没有资本外逃,而且是资本流入。只有发展得不好的国家才资本流出,流到美国,流到瑞士银行。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把产业结构内生化。这个模型的出发点就是假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而且也没有比较优势的概念,一个在非洲生产咖啡的国家,同时有资本很密集的钢铁业,就直接把这个当成出发点去研究了。所以我觉得不够根本,如果没有把结构内生化的话就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要内生化就要从最根本的出发,最根本的外生,或者最根本的给定因素出发,这样才不会把中间的一层作为出发点,这经常会误导。从最根本的出发的好处,就是不会好像从中间因素出发那样,从中间因素出发得出的结论正好是相反的;从中间因素出发得出的政策含义,如果被认真采取的话,就会是误导性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如果你从最根本的出发,那其实这样的路径是最灵活的,能解释最多现象。你比如说,我在整部《中国的奇迹》中,讨论中国的各种变化、各种的制度安排,我很自信地讲是一以贯之的。到后来的马歇尔讲座,我把它扩展到解释整个发展中国家六十年来的变化,我也一以贯之,而且可以谈论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我不仅讨论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我还谈论最优金融结构、教育结构,还有潮涌现象,等等。很多现象你都能解释,而且每个现象你都可以写一个很严谨的模型,并且这些现象到最后都是可以加总的,因为它背后的所有出发点是一样,所以变成一个体系。所以我强调内生性,而且强调最根本的,我还没有找到比要素禀赋更根本的经济参数。我跟大家强调,是因为现在的主流里面,除了研究国际贸易的人在Hec-kscher—Ohlin(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时候还讨论,现在又放弃了。
比如说,现在讨论企业异质性,那确实在每一个产业里面有异质性企业,只有比较好的企业才会出口,这个我同意。但有没有可能,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的企业,去跟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很密集的产品?不可能,它还是要从禀赋决定的。还有一个讨论是特殊化。其实保罗·克鲁格曼自己说得很清楚,特殊化谈的是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贸易还是必须用Hec-kscher—Ohlin来解释。我们研究的是发展,发展怎样逐步地趋向发达国家。这样我们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怎么决定,然后逐渐怎么变成发达国家。从要素禀赋来切入是最有说服力,而且叠加的可能性是最好的,可以解释的现象是最多的。
那么目前来讲,从新结构经济学,要努力的是什么?其实一个是怎么把它模型化,一个是怎么样用更好的数据来检验。这点张乾上午做报告说过,只要逻辑清晰,应该都可以模型化。我相信新结构讨论的这个应该逻辑是很清晰的,应该是可以模型化的,无非就是说有没有找到好的数学工具罢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要在引进结构以后把它模型确实是不容易的。你说王勇花了几年?他刚和我做的时候比现在年轻多了。还有邢海青教授也是好几年,我看他也是两鬓越来越白了。(付才辉:老师我要辞职)你不用辞职,我给你买染发剂。
我也同意,王勇跟鞠建东老师做的这篇论文当然不是完美的,里面有很多特殊假定。但基本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至少它把我们新结构经济学所要表达的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有结构,并且结构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结构的变化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推动。基本的精神已经表述出来。里面基本上是马歇尔的体系,什么东西都完美的:完全信息、没有摩擦。如果把信息不完全、有摩擦等引进来,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讨论了。如果再扩张一点可以再讨论金融的作用等等。所以我觉得可以以那个论文作为切入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野心也可以大一点。我也跟才辉,跟陶勇讨论,确实可以把阿罗-德布鲁进行扩张,让它成为一个特例,因为它本身没结构。我知道要引进结构很难。阿罗-德布鲁要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体系完全用数学很简洁地表示出来也是很难。所以他找了一个数学家,而且他本身数学也是非常好。当然他们对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体系整个机制是什么都很了解,然后他找一个合适的数学法表示出来。但是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结构。我们现在认为结构很重要,而且结构必须由要素禀赋的差异跟要素禀赋的积累所带来的变化所推动。
目前,这还没有一个在最一般的状况之下的模型,我们能接受王勇他们的那个有很多特殊假定的模型。但是到最后的目标还是必须把这些都放松,然后把这些特殊假定的东西放弃掉。我也同意回到张乾讲的,只要思路清楚,一定可以用数学表示出来,无非就是不知道哪个数学工具。那就要去找。你比如说,当年理性预期革命就是这样子,他发现凯恩斯主义的东西不合适,他对这个现象了解得很清楚,他要找一个数学工具,然后他就去找,找到贝尔曼方程式(Bellman Equation)。那我们现在同样的道理,我们知道结构非常重要,而且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演化必须由要素禀赋来决定和推动,那用什么样数学方式能够表述出来?大概目前的微积分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泛函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试一试。在这一点,我也同意才辉和陶勇他们,万一成了怎么办呢?而且,泛函不行我们再找另外一个。既然逻辑这么清楚,一定能用数学表达出来。一定要有信心。所以你要是怕白头发,没关系,我再每个人送你一瓶。
但是,必须有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到最后,当然是把阿罗-德布鲁的东西当作特例,不是推翻,是我们的体系里的一个特例,你要退化到阿罗-德布鲁。但是,我们可以把不同发展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都用同一个体系把它表示出来。但这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单单JME那篇文章就用了六七年时间,我们不能六七十年以后才做成嘛。当然你们都还年轻,六七十年以后几岁啊?在这种状况下,我接受鞠老师的说法,我们每年应该有五篇文章、十篇文章,理论模型的、即使局部有特殊假定的,再加上一些实证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这必须是我们今天晚上在座各位共同努力设定的目标。你写的文章不用是完美的,写文章的目标是,只要逻辑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漏洞,即使有特殊假定也没关系,这个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舒尔茨跟我说的,他说如果你要等到一篇文章是完美的时候再发表,那他到现在可能一篇也没发表。这是他拿到诺贝尔奖后讲的话。
我的意思是,诚实地,在你能了解的尽量不要去犯错误,即使犯错误也没有关系,有很多拿到诺贝尔奖的人,后来人家发现他拿诺贝尔奖的那篇文章数学是有问题的。因为到底经济学最主要的是一个idea对不对,只要你的idea是对的、认识是对的,即使你用的数学有点问题,人家还可以改你数学。但是当大家都不知道那个idea,你先把那个idea讲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詹姆斯•莫里斯也承认,他那篇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大贡献的论文,其实数学有问题。还有其他的也这样。
现在有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这个东西现在要做什么。当然了,佳君老师已经有很多构想了。我想,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来推动理论模型构建,这个中心会有几位核心的、在中心工作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但是我们希望以中心作为一个网络、平台,来联系大家,推动大家一起研究。我们可以经常开会,经常来这边交流、辩论。这是一点。
第二个,这个中心应该去收取尽量多的数据,用这个数据来支撑大家去做实证检验。一方面,如果理论模型要发表,你必须把事实特征描述得很清楚,你必须有经验数据。而且,理论模型还应该有很多推论,或是说模型还没做出来,推论可以先拿出来,那我就可以做实证实验。
新结构经济学中心还希望推广应用。我一向是行动主义者,我受王阳明影响太大了: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我如果认为这样是对的,我们就要这样去做,而且做得必须产生我当时认出来的结果,那这样才能说,我当时的认识是正确的。现在佳君和才辉都在努力,我们一方面是在做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同时也希望把这个理论框架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帮助地方政府、帮助我们国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做政策,来看按照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了解结构是什么决定的,什么东西决定结构变迁,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企业、市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又实际做出来给人家看,一方面可以引起更多人相信,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努力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你的理论不能改造世界,那这样的理论是无用的理论。如果不能改造世界,理论通常不正确,只是逻辑游戏。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也希望作为实践平台。你那边将来可以合作,还有你们如果回到你们学校、你们单位去,需要实践的话,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来推动实践。
这几天有人跟我提到说成立一个协会,出一些新的杂志。我觉得是努力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可能比较好的还是按照华秀萍教授的意见:不是一下子我们自己出个杂志,然后自己封闭性地内部讨论;我们应该打出去。所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的话,一个是我们每年开一些研讨会,选一些主题,然后找一些有名望的期刊去出专题讨论。我发现,在学界里面专题讨论看得人会多,在有名的期刊发表,这些论文大家比较接受。
除了专题讨论,我觉得我们还要有勇气,直接到排名前五、前十的期刊去投稿。因为专题讨论人家会觉得你已经开了会,已经选择过了,你发表这些主题很重要,当然大家会注意。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做:一方面大家去建模、做严谨的实证——题目很多,可以瞄准主流杂志;另外我们每年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话题,我们来开研讨会,开完研讨会以后,我们还是有挑选有讨论,找一个现在在国外已经接受的杂志出专题讨论。也许这样过五年十年,我们再出自己的期刊,当然学界就不会说关起门来自己讲话。这要有策略性,往后推一点。
非常感谢大家花了至少四天,有的人六天时间,这么密集的智力讨论,其实非常累。早上8点多,晚上9点多结束。我相信这样的讨论对大家有很多帮助,包括对我,至少我马上知道有什么东西别人还不太清楚。那你们可能经过这样的讨论,对事情认识会增加。也感谢会议组织者!
责编:邢深;初审:程子茜;复审:李雨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