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英国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le Carré)于当地时间12日晚去世,享年89岁。勒卡雷创作颇丰,经历奇幻,由间谍而创作,以谍报类型小说闻名于世。比起著名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勒卡雷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回应,他笔下的人物相较于邦德,与社会的互动更为真实,外表也不怎么突出。小说中少有掺杂动作惊悚的元素,例如武术或是高科技设施;剧情中的主角也有相当透彻的智力分析。可以说,勒卡雷是以深沉内敛的写作风格确立了其在20世纪类型小说文学中的地位。
选文摘自勒卡雷的自传《鸽子隧道》。所讲述的其实是勒卡雷在巴勒斯坦的见闻和经历。为了《小鼓女》的小说取材,勒卡雷深入中东,他和阿拉法特的交往也就发生于此。小说仍旧是间谍题材,但是故事的背景被放置了中东。为了小说创作,作者不得不在巴-以两地辗转穿梭。相较于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的游历就带有了颇多的战地色彩和异域风情。文章的细节刻画让人印象深刻,阿拉法特的柔软胡须,裹着巴勒斯塔国旗坐在游行花车里举枪指向落雨天空的战士,战地医院被炸断双腿的7岁儿童,在轰炸期间举办的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足球赛……由于环境的独特,文章在蒙太奇般的场景切换中一直笼罩着一层诡秘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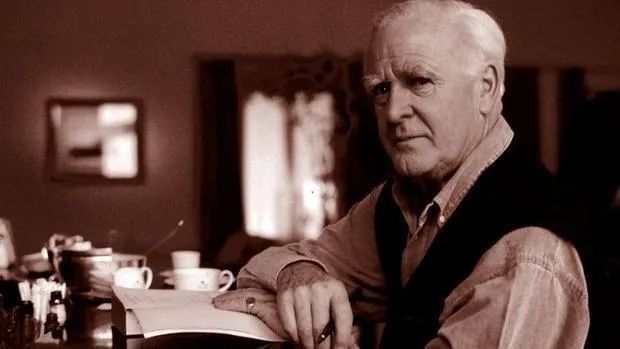
晚年的约翰·勒卡雷
实景剧场:与阿拉法特共舞(节选)
继续等,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清晨的阳光出现时,躺在酒店的房间里数着窗帘上的弹孔。下半夜的时候,蜷缩在海军准将酒店的地窖酒吧里,倾听那些已经忘了如何入睡的、疲惫的战地记者若有所思的絮叨。这个晚上,我正在酒店洞穴般毫不通风的餐厅里吃着十英寸长的春卷时,有个服务生兴奋地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我们主席要见你,现在。”
我首先想到的是酒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他要把我赶出去了?我没有支付我的账单吗?还是在酒吧里冒犯了什么人呢?又或是他想要我帮忙签本书?然后慢慢地,我才恍然大悟。我跟着服务生走过大厅,踏入滂沦大雨之中。一辆沙色沃尔沃旅行车打开了后门,旁边徘徊着身穿牛仔裤、全副武装的战士们。没有人说话,包括我。我弯腰,坐进了沃尔沃的后座,战士们也跳上了车,两个战士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两边,还有一个坐在副驾驶座。
我们在飘泼大雨中疾驰过这座被摧毁的城市,一辆吉普车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不断变换着路线,不停地换车,飞奔进小巷之中,又在车流繁忙的双车道上猛然撞向中央隔离带。迎面而来的车辆纷纷闪避,以至于撞上了马路牙子。我们再次换车,我又被检查了四次或者六次。我站在贝鲁特某条被大雨冲刷的人行道上,周围全是帽子上滚动着雨滴的、全副武装的战士。我们的车不见了,一扇临街的门敞开着,有个人召唤我们进到一个弹孔累累的公寓大楼里,里面既没有窗户也没有亮光。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走上铺着瓷砖的楼梯,一群幽灵似的武装人员列队在旁。走上两段楼梯之后,来到一处铺有地毯的平台, 我被领进一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刺鼻气味的电梯。电梯猝然一晃,迅疾上升,而后又在巨大的震动之后停了下来。最后,我们抵达了一间L形的客厅,靠墙站着的战士有男有女。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没有人抽烟。这时我突然想起来,阿拉法特不喜欢烟味。有名战士开始对我进行搜身,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我心中突然有种没由来的恐惧感。
“谢谢,我已经被搜过很多次了。”
他张开双手,仿佛是特意要让我看看他手里其实什么也没有,然后他笑了笑,又退了回去。
在L形房间较窄小的那个角落里,阿拉法特主席此刻正坐在桌子后面,等着我去发现他。他戴着白色头巾,身上的卡其色衬衫有着挺括的折痕,一把银色手枪,收在塑料制的棕色手枪套里。他没有抬头看他的客人,正忙着在文件上签名。直到我被领到他左侧的木雕宝座时,他都还忙得完全没有注意到我。
最后,他终于抬起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很愉快的事儿似的,先是露出了笑容,然后转向我,同时猛地跳了起来,高兴得令人意外。我也猛地站了起来,像是两个串通好的演员一样,我们凝视着彼此的眼睛。我已经被事先提醒过,阿拉法特本人在和人交往时,总是呈现出那种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感觉。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此刻也正处于舞台上。我和他一样,是个表演者,我们面前有着活生生的观众,或许多达三十个呢。他身体往后烦斜,伸出双手,向我表示欢迎。我握住他的手,这双手柔软如孩童。他凸出的棕色眼睛里流露出热情又恳切的神色。
阿拉法特
“大卫先生!”他喊道,“为什么会想来见我呢?”
“主席先生,”我以同样高昂的语气回应道,“我来这里,是为了让我的手有机会贴近巴勒斯坦人民的心啊。”
我们事先排练过这场戏吗?此刻,他已经引着我的右手贴在他卡其色衬衫的左襟上了。衬衫上有个钉着纽扣的口袋,熨烫得非常完美。
“大卫先生,就是这里!”他热切地呼喊道,“就是这里!”他重复了一遍,以便我们的观众能够听清楚。
屋子里的人全体起立。看来我们的演出大受欢迎。我们进行了阿拉伯式拥抱,左,右,左。他的胡须并不是硬邦邦扎人的那种,而是丝绸般柔软的毛发。闻起来像是强生婴儿爽身粉一般的味道。放开我之后,他开始对观众们讲话,一只手还是占有性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在巴勒斯坦人之间自由行走,他当众宣布道——这个从不会睡在同一张床上两次,掌控着自己的安全,坚持表示自己只属于巴勒斯坦的人如是说。就是这样,我可以去见、去听我想见想听的一切。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必须写出真相,说出事实,因为只有真相才能令巴勒斯坦自由。
他会把我委托给他的战士首领,也即我在伦敦见到的那位——萨拉赫·塔马利。萨拉赫会亲手给我从年轻战士当中挑选保镖。萨拉赫也会带我去黎巴嫩南部,给我讲解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之间的伟大斗争,他会介绍我认识他的指挥官和部队。我所碰到的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会直率坦诚地与我交流。阿拉法特要求我跟他合影,我婉拒了。他问我为什么——当时他的表情看上去十分高兴,又多少带着些戏弄逗趣般的神色,因此,我鼓起勇气,诚实地回答道:
“因为我还指望着比您更早一些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啊,主席先生[1]。”
他放声大笑起来,于是,我们的观众们也都笑了。但事实上,这句实话实在有点太过头了,我刚说出口就已经后悔了。
以巴以冲突为创作背景的《小鼓女》
见过阿拉法特之后,其他一切事情都感觉很正常了。所有的法塔赫[2]年轻战士都归属于萨拉赫麾下,其中有八位当了我的私人保镖。他们的平均年龄最多不过十七岁。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在我位于顶楼的床边围成一圈睡觉,或者甚至连觉也不睡,因为他们接受的指令是一直坚守在我的窗边,以便观察来自陆地、天空或者海洋上任何可能发生的攻击征兆。当他们觉得无聊的时候(这个工作很容易令人觉得无聊),他们就会举起手枪,射击藏在灌木丛中的流浪猫。不过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用阿拉伯语互相低语,或是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找我练习英文对话。他们早在八岁的时候便已加入巴勒斯坦童子军,也就是所谓的“阿什巴”。在十四岁时,他们已经被认为是羽翼丰满的战士了。根据萨拉赫所说,他们用手持火箭筒瞄准以色列坦克的技术无人能及。还有我可怜的查莉,那位“实景剧场”里的明星演员,一定会爱上他们每一个人。我一边思索着,一边把她的各种想法匆匆记录在我破旧的笔记本上。
有萨拉赫的带领,以及如同密友一般陪伴着我的查莉,我拜访了以色列边界的巴勒斯坦前哨基地,在以色列侦察机的轰鸣声和一阵一阵的零星枪声中,烦听战士们的传奇故事——至于那究竟是真实还是想象,我也不甚明了——在夜间突袭时开着橡皮艇穿越加利利[3]。他们并非是要吹嘘自己的英勇行为。实际上,仅仅只是“抵达那里”就已经足够了,他们强调:为了实现梦想,即便只有几个小时,也是值得冒着死亡或者被抓的危险去做的;穿越途中,你需要短暂停下在黑暗中行进的小船,吸一口来自故乡的、花朵和橄榄树还有农田的芬芳,聆听家中山坡上羊群的咩咩叫声——这就是真正的胜利。
有萨拉赫的陪同,我得以去探访位于西顿[4]的儿童医院。有个双腿均被炸断的七岁男孩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查莉之前从来没有如此身临其境过。在我们造访过的那些难民营里(我记得最清楚的要数拉希迪亚和奈拜提耶这两处营区),民众确实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权利。拉希迪亚以足球队闻名,遍布沙尘的球场常常会遭受轰炸,因此,比赛全都准备得很仓促,随时可能开始,也随时可能结束。这里好几名最出色的球员最终都成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殉道者,遗照就直接摆放在他们生前所赢得的银制奖杯之间。在奈拜提耶,有个穿白袍的阿拉伯老人注意到了我脚上穿着的棕色英国皮鞋,以及我走路时或多或少带有的殖民地色彩。
“你是英国人吗,先生?”
“我是英国人。”
“你看一看。”
他口袋里有份文件。那是一份证明书,用英文印刷,有英国委任官员的签名和盖章,证明文件持有人是伯大尼村外某块小农场和橄榄林的合法所有人。日期是一九三八年。
“我就是这个持有人,先生,现在你看看我们,我们这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心里涌起了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羞耻感——全都来源于查莉的愤慨之心。
在一天的奔波劳碌之后,晚餐是在萨拉赫位于西顿的家中进行的,那里有种被施了魔法一般的、宁静祥和的幻觉。这座房子或许弹痕累累;或许有枚从海上发射过来的以色列火箭弹曾经射穿过某一面墙,却没有爆炸。可是,此刻在花园里却有懒洋洋的小狗和鲜花,壁炉里燃烧着簧火,餐桌上摆着烤羊排。萨拉赫的妻子,迪娜,是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公主,曾经嫁给约旦国王侯赛因[5]。 他在英国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在剑桥的格顿学院主修英语语言文学。
迪娜和萨拉赫以极具知识素养且富于幽默感的巧妙方式,带领我认识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查莉坐在我的旁边,紧紧挨着我。上次在西顿展开激战的时候,萨拉赫骄傲地告诉我,迪娜这个素以美貌和坚韧品格闻名的纤弱女子,毅然开着他们那辆旧捷豹车进城,去面包店买了一大堆比萨,开赴前线,坚持要亲手发给战士们。
十一月的夜晚。阿拉法特主席和随行人员驾临西顿,庆祝巴勒斯坦革命十七周年。天色墨蓝,风雨欲来。当我们和其他上百号人满满当当地挤在观看游行的狭窄街道上时,我的保镖除了还有一个确实站在我身边之外,其他人全部消失了。剩下这位神秘莫测的迈哈茂德,并没有随身带枪,从不在萨拉赫家窗户那儿射杀小猫取乐,英语说得也最为流利,全身上下总是笼罩着某种神秘而又疏离的氛围。过去的三个晚上,迈哈茂德完全不见踪影,每天都是直到黎明拂晓时分才回到萨拉赫家里。现在,在这条挂满了横幅和气球,人群密集拥挤,人心激荡不已的街道上,只有他坚守在我身边:一个矮矮胖胖、戴着眼镜的十八岁男孩。
游行开始了。首先进场的是风笛手和旗手;紧随其后的是大声播放着口号的广播车。魁梧的军人们全都身穿制服,政要官员们则身穿黑色套装,聚集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阿拉法特的白色头巾在他们之中格外引人注目。整条街道爆发出连绵的欢呼庆祝声,我们头顶上先是喷射出绿色的烟雾,接着又变换成了红色。尽管下着大雨,在真枪实弹的支援之下,“烟火”也照常燃放。我们的领袖一动不动地站在舞台上,手指伸出,比出胜利的姿势,在闪烁的灯光与焰火之中,仿若一尊他自己的雕像。
现在出现的是佩戴着绿色新月徽章的医院护士方阵,接下来是因战争致残的、坐在轮椅上的孩童,再就是阿什巴的男女童子军,他们挥舞着手臂,步伐不太一致地前进着。现在驶来的是一辆拖着花车的吉普车,花车上站着身裹巴勒斯坦国旗的战士们,举起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指向下着大雨的阴沉天空。紧靠我站着的迈哈茂德,拼命地朝他们挥手,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也整齐一致地转向他,向他挥手致意。花车上的那些男孩,恰恰就是我其他那些消失不见的保镖。
“迈哈茂德!”我把双手拢成喇叭状向他喊道,“你为什么没有跟你的朋友们一道,用枪指着天空啊?”
“我没有枪,先生。”
“为什么没有呢,迈哈茂德?”
“因为我做夜间工作!”
“可是你晚上都在做些什么呢,迈哈茂德?你是一名间谍吗?”——在喧闹声中,我尽可能地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大卫先生,我不是间谍。”
即便在目前的一片喧闹嘈杂声中,迈哈茂德仍旧犹豫着要不要把他这个最大的秘密告诉我。
“你一定看到过那些阿什巴制服前胸上印着的、爸爸[6]阿拉法特主席的照片,对吗?”
我见过,迈哈茂德。
“我一整夜——都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拿着熨斗,亲手把爸爸阿拉法特的照片一张张地熨烫到阿什巴的制服上。”
这么多人里,查莉一定最爱你,我想。
阿拉法特邀请我到一所巴勒斯坦殉道者遗孤学校共度新年夜。他会派一辆吉普车到我住的酒店来接我。酒店仍旧是那间海军准将酒店,“一辆吉普车”实际上指的是一整支护航车队当中的一辆。车队里的车一辆紧跟着一辆,在婉蜒的山路上疾驰,穿越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检查站。天气,同样是滂沦大雨——这好像是我每次会见阿拉法特时都要被迫承受的困扰。
眼下这条道路是单车道,尚未铺设好路面,就已经在暴雨中分崩离析。前方吉普车卷起的松动石块不断朝我们的车子飞来。路旁几英寸之外就是山谷,隐隐显露出数千英尺之外地表上的一小簇灯火。领头的车子是一辆红色装甲路虎。 据说里面坐的就是我们的主席。 不过,当我们开进学校时,警卫才告诉我们,他们这样说其实是耍了我们。 那辆红色路虎是个诱饵,阿拉法特本人早已安全地待在楼下的音乐厅里,准备迎接他的新年宾客们了。
从外部来看,这所学校不过是任何一幢大小适中的两层楼房该有的样子。 一走进去,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正身处顶楼,因为房子的其他部分是沿着山坡逐步往下盖的。 注视着我们下楼的,除了那些常规的、戴着头巾的全副武装的男战士之外,还有胸间横跨弹带的年轻女子。 音乐厅本身是非常宽敞的圆形剧场型,里面挤满了人,前方有个升高的木制舞台。 阿拉法特站在舞台下方的第一排,当他拥抱他的客人们时,拥挤的大厅里就会轰隆隆地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天花板上垂下庆祝新年的彩带。 墙上则装饰着各式革命标语。 我被推操着走向他,他再次给了我一个传统的拥抱,而其他头发灰白、身穿卡其粗斜纹布服装、背着枪带的男士则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声说出新年祝语。 他们有些戴了名牌,有些,比如说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布·杰哈德,会在名牌上使用假名。 还有些根本没有戴名牌。
表演开始了。 首先是由巴勒斯坦那些失去父母的女孩围成一圈唱歌跳舞。 接下来轮到没有父母的男孩。 再然后就是这些孩子聚在一起跳阿拉伯跺脚舞,他们随着众人打拍子的节奏,彼此传递着木制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站在我右边的阿拉法特伸出了双臂,站在他另一边的、看上去面色凝重的战士冲我点头示意,于是,我便抓住阿拉法特的左手肘,两人合力,把站在我们之间的阿拉法特用力推上了舞台,然后自己也跟在他的后面爬了上去。
在他所热爱的这些孤儿中间旋转跳舞——阿拉法特似乎在孩子们的气息当中迷失了自我。他抓起自己头巾的尾端,使劲甩了起来,就好像亚利克·基尼斯在电影《雾都孤儿》中扮演的费金那样。他此刻的神态,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真情流露。他是在笑还是在哭?不管是哪种情况,他的情绪都如此清晰可辨,是哭是笑已不重要了。此时,他冲我做了个指示,要我搂住他的腰。另一个人则搂住了我的腰。终于,我们所有人——高级指挥官、营区平民、狂喜的孩童(毫无疑问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间谍,因为阿拉法特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被监视得最多的人)——在我们领袖的带领下,串成了一条大鳄鱼。
鳄鱼下到水泥过道里,又走上一段台阶,穿过走廊,又下到另一段台阶上,我们跺脚的砰砰声取代了鼓掌的声音。在我们后面或者上方,如响雷般整齐的声音唱起了巴勒斯坦国歌。我们就这样跺脚踢踏,拖着脚步又回到了舞台上。阿拉法特走到众人面前,停了下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他跳水似的向前一跃,扑进了他那些战士的臂膀之中。
在我的幻想中,我那位欣喜若狂的查莉也为他欢呼喝彩,声音穿越屋顶,直冲云霄。
八个月后,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三十日,以色列正式入侵后,阿拉法特和他那些高级指挥官被驱逐出了黎巴嫩。在贝鲁特的码头上,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们,愤然不服地对着天空鸣枪,接着便搭船来到了突尼斯的码头——布尔吉巴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正等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城郊外的一家奢华酒店被匆忙改装成了阿拉法特的新总部。
几个星期之后,我到那里去看他。一条长长的车道通向这座位于沙丘之中的优雅白色宅邸。两名年轻的战士要求我具体通报我来这里干什么。此处没有劲头十足的微笑,没有惯常见到的阿拉伯式礼仪。他们问我,我是美国人吗?我便给他们看我的英国护照。其中一个用粗鲁讥讽的语气问我,是不是碰巧听说了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7]。我告诉他,我前几天刚去过夏蒂拉,对那里的所见所闻深感悲痛。我告诉他,我是来见爸爸阿拉法特,表达我的哀悼之情的。 我说,我们以前在贝鲁特见过几次,还在西顿见过,以及我在殉道者遗孤学校和他共度了新年云云。 其中一个男孩抓起电话。 我没听见他说出我的名字——尽管他手里抓着我的护照。 然后,他放下了电话,厉声说道: “过来! ”紧接着便从他的皮带里抽出手枪,抵着我的太阳穴,迫使我将双手放在脑后,拽着我走过长长的通道,来到一扇绿色的门前。 他打开了门锁,交还了护照,把我推出门,来到室外。 在我面前的是一块骑马场,环绕马场的一圈沙子已经被踏遍了。 亚西尔·阿拉法特,戴着白色头巾,骑在一匹漂亮的阿拉伯骏马上。 我看着他骑完一圈,又一圈,再一圈。 然而——他要么根本没有看见我,要么就是根本不想见我。
巴解组织
与此同时,我曾经的黎巴嫩东道主、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指挥官萨拉赫·塔马利,由于他是迄今为止落入以色列人之手的最高阶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正遭受着酷刑。他在以色列最臭名昭著的安萨监狱被单独囚禁,接受我们近年来比较乐于称呼为“强化审讯”的审问。他逐渐与来访的杰出以色列记者阿哈隆·巴尼亚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促成了巴尼亚那本《我的敌人》的出版。这本书除了申明双方在各个方面的共同主张之外,还印证了萨拉赫对巴以共存的赞同——而非接连不断、永无希望的军事冲突。
[1] 一旦勒卡雷与阿拉法特的合影登上巴勒斯坦报纸,勒卡雷就会被以色列拒绝入境。故有此说。
[2]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简称。由亚西尔·阿拉法特建立,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最大的派别。
[3] 巴勒斯坦北部地区。
[4] 黎巴嫩西南部城市。又名“赛达”。
[5] 迪娜实际上是侯赛因的远房表姐。两人在英国相识,婚后一年即离婚,留下一女阿利亚由侯赛因照管。
[6] AbuAmar,阿拉法特被巴勒斯坦称为“AbuAmur”,即为“开创者之父”,此处按中文意思译为“爸爸”。
[7] 又称贝鲁特大屠杀,于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发生于贝鲁特的萨布拉街区和夏蒂拉难民营,凶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
本文节选自
《鸽子隧道》
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译者:文泽尔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年:20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