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产的善政》发表于《人民日报》“大地”副刊(2009年12月27日),距今12年有余了。看标题,这是一篇“歌颂性杂文”。偶翻闲书,看到另外一些史料,一个子产,判若两人。
鲁迅谓二十四史是“相斫史”,是“独夫的家谱”(《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7),并不尽然。悠悠5000年中国史,如果只是“吃人史”、“相斫史”,哪来璀璨的古代文明。历代的御用文人竭力粉饰王朝的皇权统治,美化帝王的文治武功,涂抹在竹帛上的笔墨,难免会记录下一些虽非“善政”亦非“恶政”的史实,也许由于价值差异,时空错位,或歪打正着,多少有些价值罢了。
春秋时迁都后的郑国,不过今日郑州附近之一隅,且夹于晋楚两强之间,国际环境十分困顿。子产成为郑国的相国,不毁乡校一节,只是其应对舆情之一面。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2年。子产拒绝了然明拆毁乡校的建议,以此体现了一个执政者重视社情民意的政治胸襟。为了叙述方便,原文抄录如下: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春秋左传注(修订版)》下册,杨伯峻著,中华书局,1990年,页1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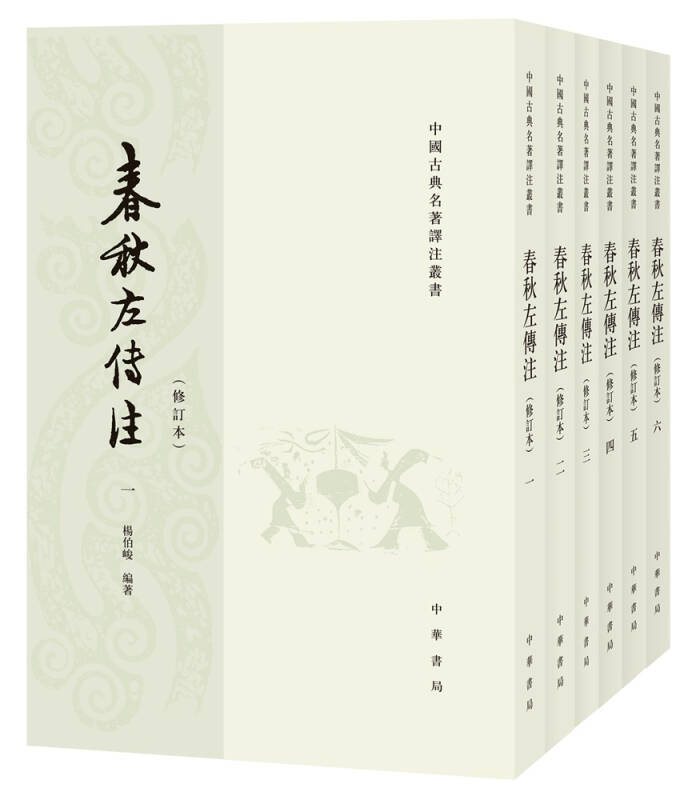
子产这段议论,有三句话特别精辟,一是百姓“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这大概是古代中国的优良传统。这与邓小平强调的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决策方针是一致的。二是“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讲的是消除“民怨”的途径和方式。“忠善”的方式是“说理”的方式,“以人为本”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作威”的方式是“强制”的方式,“权力至上”的方式,“解决‘问题人’”的方式。三是对待民意,犹如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措词是否很熟悉?这话正是来自“周厉王弭谤”那段史实。巧了,郑国的首任国君郑桓公恰恰就是周厉王之子。子产作为相国,大概不会忘记这段本国历史。
子产这段佳话在历代“资治”的著作中多有提及,甚至孔夫子也评价甚高。不过,当时孔子只有10岁,他的评价是他人伪托,还是后来追记,不得而知。后来有人将此作为郑国曾经言论自由的佳话加以推崇。然而,这样的佳话,与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毕竟不可同日而语。黎澍先生的《言论自由古史辨》发表于1945年,对古代的类似事件作过评论,他认为,“中国自古无言论自由。不但没有产生过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也没有存在过类似言论自由的事实。”(《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35)尽管如此,在2500多年前的古代,一个当政官员,把给当局提意见的百姓当作老师(“是吾师也”),把百姓的意见当作药品(“吾闻而药之也”),毕竟十分难得。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发生在郑简公二十四年。郑国还是那个郑国,子产还是那个子产,四年之后(公元前538年),却爆发了强烈的民怨: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下册,页1254-1255)

一项决策,一起风波。这项决策是子产的“作丘赋”,其实是一项税收政策。由于其加重了国人负担,当然引起了国人不满。此时的民怨已经不是乡校对时政的“议”,而是国人对相国的“谤”,子产父子两代都遭到民众唾骂与诅咒,原因很简单,子产的“重赋毒害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子产的三点反应:一是决策依据。他宣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自古以来的统治者,为政决策往往打着为了社稷,出以公心的旗号,再悲惨、再邪恶的结局,也会把动机打扮得公正长远。二是权力傲慢。在自我标榜的同时,子产表现出十足的权力傲慢,“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焉”,最豪横的是这一句,“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即百姓不可放纵,决策不可更改,决心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此时的子产,如同换了一个人,四年前“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三是一意孤行。郑国大夫子宽就此提出批评,制订法令不厚道,后果尚且贪婪;制定法令存贪念,后果将会怎样?……决策不遵法度,放任长官意志。人心各有不同,谁还尊重上级?然而,这些话如东风过马耳,子产并不回应。

子产作为春秋时的政治家已载入史册,不毁乡校一节,作为一项善政,其嘉言懿行流传后世。唐代大儒韩愈甚至作《子产不毁乡校颂》专门歌之颂之。(《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67)这则史实至今仍广泛见于各类文集与教材之中。然而,《郑子产作丘赋》却少有人提起。当然有人曲为之辩,道是“春秋之世,兵革数兴,郑在晋、楚之间,尤当其剧。”如不加重赋敛,“岂得全无赋乎?”内政外交需要钱啊!不过,也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子产于牛马之外,别赋其田”,“一丘出两丘之税”。(《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203)这显然罔顾民生的苛政,而“苛政猛于虎”,则是孔子后来的总结。且不说子产的无视民意、权力傲慢、刚愎自用,仅就加重税赋,激起民怨本身,至少不是一桩善政或仁政。
两个事件,相隔四年,诚如黎澍先生所说,子产不毁乡校,不过是耍点惠而不费的小手段,装出尊重民意,沽名钓誉而已。其实在古代对于子产的评价也是多元的,比如,孟子说过,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孟子·离娄(下)》),苏轼也说子产“有及人之近利,无经国之远猷。”(《三苏全书》第三册《论语说》,语文出版社,2001年,页237)正因如此,我在早前的文章中曾经写道,在古墓葬、线装书中寻觅当代文明的因子是徒劳的,历史只是前人的记录,并不具有多少“为鉴”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