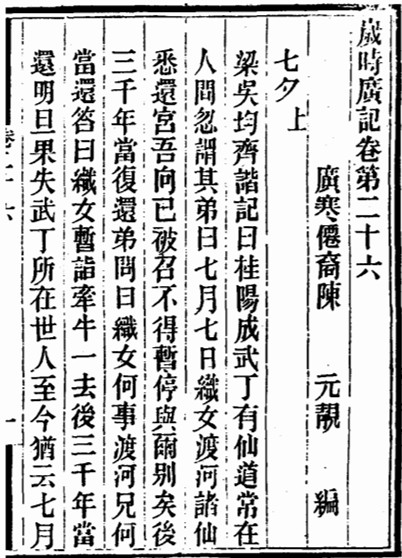历来关于七夕的传说中,都说牛郎织女在这一天是通过“鹊桥”渡过天河相会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作为两人相会桥梁的“鹊”乃指喜鹊,但这其实未必是故事的原貌。台湾学者洪淑苓在《牛郎织女研究》一书中发现:“为牛郎织女搭桥的,又有喜鹊、鹌鹑、与百鸟之不同,有一个笔者未收录的鹊桥传说故事,甚至说是乌鸦搭桥的。”
她所说的乌鸦搭桥的故事,在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记录的广东省陆安(海丰)民间传说中便是:牛郎织女婚后只管卿卿我我,把牧牛、织布的事都抛荒了,天帝知道后很愤怒,“即刻下了一道圣旨,命乌鸦前去传言,此后两人须各居河之一边,每七天,才准过河相会一次。乌鸦是顶拙于口才的东西。它这时得了御旨,便急急飞向两人同居的地方去了。它把好好的,每七天相会一次的话,误说成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即此以后,他们便永远每年只有一次的见面了。”

资料图
这里的故事细节很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这很可能就是七夕传说的一处关键:牛郎织女每年只有七夕才能相见是因为使者误传口信引起的,而误传者是乌鸦,作为对其误传的惩罚,它们每年七夕必须搭桥让牛郎织女相会。
误传口信的使者
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七夕是起源最模糊不清的一个。虽然有人推测《诗经·小雅·大东》里提到的牵牛、织女星与七夕有关,但该诗只说织女一日之间“七襄”(郑玄解释为一日之间自东向西经七个星次),且“牵”字不见于甲骨文、金文,可见这传说至少是较为后起的,因此也有人认为这与七夕传承没有关系。无论如何,如今对七夕传说的文献记载,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两汉,例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但该诗只是将牵牛、织女星拟人化了,歌咏他们“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相望而不能相见,却未提及鹊桥,甚至都未提及两人仅在每年七夕相会。
东汉崔寔(约103-约170)所著《四民月令》中首次确凿无疑记载了“七月七日”这一日期,表明这一天在东汉已成为固定节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详细记载了乡村四时风俗生活面貌,却完全没提及这天和牛郎织女有关,只说这天应按习俗制作除虫解毒的药丸,并按习俗曝晒经书、衣裳。直到稍晚一些的应劭《风俗通义》中,才明确出现了现在所熟悉的七夕故事:“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
资料图
为什么是七月七日?由于现在缺乏东汉以前的文献记载,如果孤立地看七夕的来历,这一点很难解释。不过,正如民俗学者刘晓峰在《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所言,中国传统节日“人日、上巳、寒食、七夕、重九、下元之间这种既有直接对应又有互涵对应的复杂关系,表明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是结构性的,非线性的”,而“构成中国古代思维模式原型之一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古代岁时节日的内部结构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很明显,奇数重叠的日期正月初一、三月三(上巳)、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七夕)、九月九(重阳)都是节日,而偶数日则没有相应的节日,因为按中国的数术原理,数字本身就是神秘性的,这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便使人相信相应的日期在整年的结构中均寓意天地的节律。因此,元旦意味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上巳则是由死而生、大地复苏之日,需要祓除不祥、祭祀祖神并繁衍后代;端午是阴阳交替之际,阳气上升,毒虫活跃,故须除毒辟疫;相应可以推断:七夕是阴气开始上升的日子,故而适宜女性。
在中国的数术文化中,“七”是一个神秘的玄数。虽然这是天地四时人的开始,但民俗中“七”常被视为凶数,这可能是因为“七”为一个周期,因而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散尽,在台湾、日本的民俗中,“七”也都被视为不吉之数。在道教中,每年的一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为“三会日”,三官考核人间功过,三魂攒送生人善恶,又谓之三魂会日,宜焚香忏过;其中七月七日名庆生中会,此日中元赦罪,地官同天水二官考校罪福。这种观念可能在先秦即已出现,按《礼记·月令》的记载,七月为孟秋之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按照数术原理,七作为凶数意味着隔断,这些可能就是传说中天帝在此时考校牛郎织女、对他们处以隔离之罚的原因。
最早记载天帝惩处的是南朝宗懔著《荆楚岁时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在此之前的东汉已经出现鹊桥的元素,因此合理的推断是:天帝的这一责令是由“信使”传达的。
这和《圣经·创世纪》中那个著名的神话相似:上帝告知亚当和夏娃不可偷吃伊甸园的禁果,但狡猾的蛇却引诱他们吃了,上帝震怒之下,将他们逐出伊甸园。英国人类学家James Frazer在《人类的堕落》一文中,旁征博引后指出,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是:“蛇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向人类传送关于永生的佳音,但是这奸诈的东西错传了信息,使这信息有利于它们而有害于我们。”这种“误传口信的使者”元素广泛见于世界各地,动物形象也从蛇、蛙到野兔等种种不一,但获胜的都是动物,它们为了自己获得永生而故意误传了信息,蛇由此年年蜕皮,在原始人看来这就像每年不断获得新生。
在七夕的传说中,信使不管是喜鹊、乌鸦、鹌鹑还是百鸟,无一例外都是鸟;在最早提到牵牛、织女星的《诗经·小雅·大东》中,“大东”本身就是远离镐京的东方诸国,而在东夷传统中一向以鸟作为天帝的信使。关于鸟传错信息的事,不仅见于广东民间传说,北宋词人晏几道《鹧鸪天》也有“当日佳期鹊误传,至今犹作断肠仙”一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为信使的鸟完全就像是一个奉天帝之令传信的下级官僚,它们纯粹只是犯了小错误,但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得私利而有意曲解信息。尽管如此,对它们的处罚却极为严厉:所谓“鹊首无故皆髡”,髡刑是盛行于先秦至东汉的重刑,在《周礼》中是死刑罪减一等的刑法,看起来只是剃掉头发,但“对当时的人而言,头发的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尽管洪淑苓在《牛郎织女研究》中搜集各种传说变体后发现,“搭桥的原因又有自愿与被罚之分别”,但“被罚”恐怕更合乎传说诞生年代的社会语境。在传统中国社会,这样因小过失而受帝王重罚的事极多,如《西游记》中沙僧原是玉帝的卷帘大将,只因失手打碎琉璃盏,就被贬出天界。
在七夕传说中,这个冒失的信使一向以来都被广泛认为是喜鹊,但其实,如按上古人的观念,更有可能成为天帝信使的应是乌鸦。
资料图
乌鸦还是喜鹊?这是个问题
在上古中国人的心目中,乌鸦的地位极高。汉字中对鸟的命名要么从“鸟”(长尾鸟)、要么从“隹”(短尾鸟),但唯独“烏”字属火部,单独造字,可见其特殊。在古史记载中,太阳中有三足乌,西王母的使者“青鸟”也“如乌”,直至中唐之前,乌鸦一直被视为预兆吉祥的神鸟。所谓“爱屋及乌”,其实也是因为乌鸦本是吉兆。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故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传说,三国时东吴年号“赤乌”也是因此而设。传说汉代曾有许多乌鸦栖息在御史府柏树上,因而御史府又被称为“乌府”、“乌台”,北宋所谓“乌台诗案”便是因这一典故。
将乌鸦奉为神鸟,乃是古代整个欧亚两洲北部的普遍观念。在古代亚洲英雄史诗中,乌鸦“是萨满的魔鸟,帮助他们的精灵和同伴。萨满偶尔把自己变成乌鸦。凡能操纵乌鸦的人,都懂得魔术”。这意味着,乌鸦其实是上天沟通的媒介。在北亚的科里亚克人神话中,乌鸦则被称为世间第一人,也是他们的始祖。日本《古事记》中将乌鸦说成是上天赐予天神御子(神武天皇)的动物。北欧神话中的大神奥丁有两只乌鸦,分别叫Hugin(思想)和Munin(记忆),它们每天环绕世界飞行,向奥丁报告一切,因此奥丁才能无所不知。在古代日耳曼人看来,“乌鸦是一种无所不知的鸟,它们是智慧的化身,能够洞悉这个世界的一切,并且了解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是一种神圣、尚武并且无所不知的飞禽。”
相比之下,鹊的形象原本颇为普通。西汉桓宽《盐铁论》卷七崇礼:“中国所鲜,外国贱之;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意思是昆山玉石极多,竟拿来投掷乌鹊,后世遂以“抵鹊”喻指大材小用。在一些文化中,甚至它颇具负面意涵。如《突厥语大词典》中说:“鸟类中最坏的是喜鹊,植物中最坏的是野蔷薇。”在欧洲,《蒙塔尤》中描述13世纪法国南部人的心理:“猫头鹰和喜鹊这两种凶狠而阴森的飞禽,与能飞能爬的龙一样,让人忧虑和厌恶。”在1475年绘于普瓦蒂埃的《忏悔诗篇》中,嫉妒罪的画像上,鹊被描述为饶舌爱抱怨的鸟类。在当时的西方文化中,喜鹊的形象是“多嘴多舌、爱偷东西,象征谎言与虚伪”,因为“在中世纪中期,身上带有黑白两色的动物都是不大受人喜爱的”。
在西方,乌鸦形象的逐渐降低,是从基督教时代开始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Michel Pastoureau在《色彩列传:黑色》中推断的,“到了封建时代,黑色的正面意义几乎荡然无存,而负面意义则占据了它全部的象征义域”,这对乌鸦这样一种全黑的鸟类显然是不利的;而且正由于之前的异教传统崇敬乌鸦,它才更为教会所贬斥。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乌鸦形象的逐步降低是随着它逐步被儒家剥去其神秘力量开始的。汉代独尊儒术,以孝义立国,乌鸦被称为“慈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义:“乌,孝鸟也。”另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所谓“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是儒家用以教化人们恪守“孝”、“礼”的一贯说法。这乍看仍推崇乌鸦,但无疑是将乌鸦的形象道德化、世俗化、祛魅化了,正如现代人所说的“勤劳的小蜜蜂”只是一个道德形象,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神圣的。在那之后,乌鸦在儒家文化中的“慈乌”形象一直保留,只有在道教中仍保留着对乌鸦神力的崇敬,相传真武大帝上武当山修炼时,有黑虎开山,乌鸦引路,故他得道后封乌鸦为“神兵”,日后善男信女朝拜武当时也将乌鸦视为“灵鸦”。
资料图
这样,大体从晚唐时代起,乌鸦和喜鹊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中唐诗人白居易《慈乌夜啼诗》中,还按照一贯的儒家道德观,将乌鸦歌咏为“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晚唐诗人张籍(约766-约830)在《乌夜啼引》中还记载:“李勉《琴说》曰:《乌夜啼》者,何晏之女所造也。初,晏系狱,有二乌止于舍上。女曰:乌有喜声,父必免。遂撰此操。”虽然这里提到的何晏是三国曹魏时人,但至少表明人们还记得乌鸦是喜兆,然而在稍晚的段成式(803-863)《酉阳杂俎》中,就出现了不同的记载:“乌鸣地上无好音。人临行,乌鸣而前行,多喜,此旧占所不载。”意指:人们只知道乌鸦叫不吉利,但其实临行时乌鸦在前面叫往往有吉兆,旧占却多不记载。这表明当时民间已普遍忘了乌鸦兆喜的说法。不过,不论吉兆凶兆,都还是延续了传递上天神秘旨意的意味不像麻雀,无论它怎样,没人觉得它预兆什么吉凶。
自此,喜鹊逐渐取代乌鸦成为吉祥喜庆的象征。旧本题师旷撰、晋张华注的《禽经》,其实成书年代很可能是在宋代以后,一是因为该书在汉唐诸志及宋代《崇文总目》中均不载,二是书中还出现了“灵鹊兆喜,鹊噪则喜生”的说法,这应是晚唐以后才流行的观念。在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的世俗化,乌鸦原先作为神鸟的那种神性逐渐被社会淡忘,反倒可能注意到它喜食腐肉等特点。
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会去细化区分鸦、鹊的不同象征意义。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畏吾儿人起源传说时说到,其首领受真主赐予“三只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zāgh),他在哪儿有事要办,乌鸦就飞到那儿去侦察,把消息带回”,何高济译注:“zāgh,这个波斯词义不清,今天指鹊和鴥。”这一词义变迁恰可说明,古人常把乌鸦和喜鹊混在一起,两种鸟都以黑色为主,都很聒噪,成语“鸦雀无声”其实应作“鸦鹊无声”,意指“连乌鸦和喜鹊这两种最吵的鸟都没声音了”,否则颇不合构词理据。无独有偶,英语里的“喜鹊”一词magpie在美式英语口语中就指“爱饶舌的人”,前半mag的词源在俚语里指女性浪费时间喋喋不休(“idle chattering”);而后半的pie源自印欧语词根*(s)peik-,指“啄木鸟,喜鹊”,梵语pikah则指“印度杜鹃”,拉丁语picus也指“啄木鸟”。也就是说,古人所指的鸟名是根据其某些特征命名了“一类”鸟而未必是“一种”鸟,到后来于是变成不同的特指。
中国古人因为很重视乌鸦,基本上还是能区分这两类鸟的,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有乌与鹊斗”,《淮南子·说林训》则说到“舍茂林而集干枯,不弋鹊而弋乌,难与有图”,这当然表明这两类鸟有所不同。问题在于:古人对鸟类的称呼并不精确,鸦科在中国共有13属29种(包括乌鸦和喜鹊),但古人一般都是泛称。“乌”本指全黑的大乌鸦,“鸦”字则不见于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中,直至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成书的《广雅》一书中才收录,其解释是:“纯黑反哺者,谓之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鸦乌。古有《鸦经》占吉凶,南人喜鹊恶鸦,北人反之,师旷以白项者为不祥。”这里说到的“鸦乌”的特征,倒更像是喜鹊,只有鹊才会在腹下出现纯白色(另如分布在印度的白腹树鹊);而北方人不喜欢的“白项”者,虽被列为鹊类,但它的特征却更像是鸦科中分布在中国东部的白颈鸦或达乌里寒鸦。
在古代诗文的习惯,“乌鹊”经常并称。三国时曹操的名诗“乌鹊南飞”,千百年来多有争议,究竟是指乌鸦还是喜鹊,抑或兼指两者;钱歌川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中嘲讽汉学家Herbert Giles将这句诗中的“乌鹊”译为“乌鸦”(raven),但这么译其实情有可原,在曹操的时代,“鸦”字本身都未必已通行,故并称“乌鹊”。宋苏轼《绝句三首》:“天风吹雨入阑干,乌鹊无声夜向阑。”此处所谓“乌鹊无声”大概犹言“鸦鹊无声”。在南宋人陈元靓辑录的《岁时广记》里,征引了许多关于鹊桥的诗文,虽然其中多称“乌鹊”或“鹊”,但他归纳的标题却是“填河乌”。
资料图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这一类鸟的区分本就模糊那种区分更多是外观和文化意义上,而非现代鸟类学意义上的精确界定,就像作为西王母使者和侍从的“青鸟”无法完全对应于现实中的某种鸟类。它们均可成为天神的信使,也都适合在七夕出现,因为两者都在夜间出没;只不过在远古,纯黑的乌鸦看着比黑白驳杂不纯的喜鹊更具通灵的神力。至少在七夕的鹊桥传说成形的东汉时代,北方的神鸟还主要是乌鸦。然而随着对这种神力的敬畏逐渐消失,人们更在意的是鸣声的动人、外观色彩的悦目,晚唐之后中国文化重心向南的转移,则更进一步将南方人那种对喜鹊的文化偏爱带到了七夕的节俗中去。但之所以是喜鹊而非别的什么鸟取代了乌鸦,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这两类鸟原本就具有的相似性。
这一文化转变后来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影响:世居东北的女真人,原本和许多东北亚民族一样崇敬乌鸦,但到清朝建立时,其后裔满族却变得崇拜“神鹊”了。元代纂修的《金史》卷一记载完颜阿骨打的祖父乌古乃被人称作“乌鸦”,他毫不介意,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女真文化中,乌鸦未必含有贬义。在同卷中记载有一个女真人的名字就叫“活罗”(乌鸦),这恰似康熙时顾命大臣苏克萨哈(Saksaha)的名字是满语“鹊”一样,“活罗”对应于通古斯语的turaki(“乌鸦”)或朝鲜语的talk(“鸡”),朝鲜古代的新罗王国因崇拜鸡而被称作“鸡林”。在朝鲜人心目中的鸡,与女真人心目中的乌鸦可能都是太阳鸟。
满族虽然后来也仍然崇敬乌鸦,在晚清时的老北京,“掌管太庙的官员们过去常常为乌鸦供香,觉得它们是神鸟”;但开创满清王朝的爱新觉罗家族向来以神鹊(enduri saksaha)为祖,传说是它衔来朱果,让天女佛库伦吃下后生下了始祖布库里雍顺。从周边文化来看,这一对神鹊的崇拜颇不寻常,因为北亚普遍崇拜的都是乌鸦,唯一合理解释就是:满清贵族在晚明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意识到乌鸦在汉人心目中带有的负面含义,因而将这一作为上天使者的鸟从乌鸦改成了“神鹊”。
(本文原题《从乌鸦到喜鹊》,并有注释,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