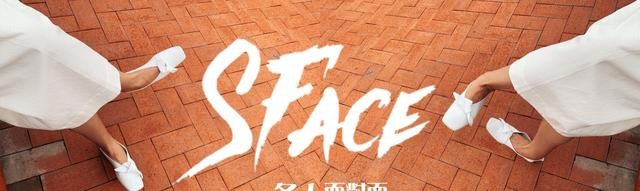
对话 · 陆川
以下为采访摘要
陆川跨界做舞剧
舞剧《天工开物》,是陆川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而成。明末书生宋应星,年少中举,春风得意。不料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宋应星参加6次会试,全部名落孙山。绝望之中,他的目光投向传统上无人问津的科学技术,终于写成中国技术史的旷世巨著《天工开物》。宋应星在书中写道:“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在人生的最后,宋应星经历了战火侵袭,家破人亡,改朝换代,最后郁郁而终。
△舞剧《天工开物》
舞剧《天工开物》预演的这一天,清晨时分,陆川出发了。他将驱车上百公里,去宋应星的墓地祭拜。
陆川:宋应星的墓特别凄凉,就像一个乱草岗。你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青山含黛。几百年前宋应星可能就是站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希望自己通过科举考试,进京做一个精英阶层,读书人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留在历史里。或者他就留在自己的家乡,在这片土地上,他能够为这个民族做什么?我觉得只有站在他的墓前,看到他当时生活和生存的环境,才能跟他的心境有些沟通。我相信是他走过的地方。看过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写作的人,搞创作的人,他会被命运抓住着手去写一些东西。
艾楚怡:但一开始大家好像是选的陶渊明来创作。
陆川:对,当时疫情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内心很压抑,想做陶渊明就是想做出世,做逃避。倒也契合当时的心情,哪儿也不让走动,最好就是采菊东篱下。但是后来我无意听到别人讲当地其他几个牛人,然后看了宋应星墓。回去之后做宋应星的想法就钻出来了,而且是抑制不住的。
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痛苦和纠结。作为一个书生,在功名路上得不到认可,他转而投身到更田野的写作。在那个时代,在当时的制度、礼教、伦常观念中,做出这样的抉择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宋应星一个人,在明朝大厦倾覆之前,卡着点儿把整个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全部记录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逆行者。在芸芸众生中,在那么多学术大咖和知识分子中间,他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所以直觉就想做他。
△舞剧《天工开物》
陆川:尽管在历史长河中宋应星消失了300年,《明史》没有记载他,《四库全书》没有收录他的著作。但他的著作飘洋过海,影响了亚洲各个国家,提升了他们的手工业水平。然后传到欧洲,达尔文、李约瑟看到这书都惊了。我之前开玩笑说,《天工开物》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地向全球开源我们的技术。今天我们说要开源,要分享,马斯克将他们的电动机技术分享给全球电机公司CEO,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电动车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技术最终是造福人类的。我觉得在古代江西,真正影响世界的第一把交椅就是宋应星。
△舞剧《天工开物》
艾楚怡:您觉得自己和宋应星惺惺相惜吗?
陆川:我一直没敢说这话,但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总能在他的书中读出弦外之音。明朝是禁海的,颁布了禁海令,谁也不许出海。但老宋写舟船,鼓励大家学习、出洋。说实话,明朝我们一个国家的GDP可能就占了全球一大半。但是我们禁海了,很多政策让我们裹足不前,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们逐渐落后,这不是从清朝才开始的。
宋应星其实一直走在体制里,但在书里他有自己的态度。他最后放弃考试时其实已经中举了,而且已经当上了县的教育局局长,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他选择写书,进行田野调查,问道于那些工匠,把细节一一记录下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这样的人。我现在最大困扰就是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他们一拿起手机就陷进去了。但是在我看来,爱好科技,爱观察生活,去发现生活秘密的风气其实很稀薄,都是在直播带货。AI飞速发展,可大家还沉浸在自我满足中,我很焦虑。我希望孩子们多关注科技和创新,像宋应星一样不拘一格地用自己的态度去拥抱真理。我觉得科技是有真理的,而且是造福所有人类的。
△舞剧《天工开物》编剧、总导演陆川工作照
陆川:如果这部戏没做好,那是我学艺不精,是我能力的问题。但选择宋应星和他的书作为题材,我觉得是对的,是有意义的。
陆川四处打工填补上亿电影资金缺口
陆川在新疆出生,在北京长大。父亲和姑姑都是作家。陆川在南京的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专业研究生。
艾楚怡:我们把您研究生的论文刨出来了,还记得题目是什么吗?
陆川:《体制中的作者》。
艾楚怡:研究的是?
陆川:科波拉。
艾楚怡:他算是体制中的作者吗?
陆川:是,他绝对是。宋应星也是体制中的作者,一个大体制中自由创作的人。
现在回头看,陆川的硕士毕业论文《体制中的作者》,既是在描绘好莱坞体制当中的大导演科波拉,也是在描绘自己的未来。
陆川在论文中写道:“在体制中生存,是每一个作者的首要条件,先生存,而后发展。执意极端个人化创作的作者,往往会陷入体制内生存危机。”评论者总结了陆川的观点,也就是既尊重体制的要求,同时又尊重自己内心的追求。
艾楚怡:您算是体制中的作者吗?
陆川: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都在体制里,但我是不是一个作者,我觉得我还需要用作品去证明。我希望自己是个作者,我希望能做出自由的东西来。
论文通过,陆川顺利毕业,而且如愿以偿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
陆川:那时候考电影学院,唯一的理想就是进入电影厂,必须进。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神级单位,不给钱都行,我自己养活自己,只要是在编导演就觉得挺好。但是我一进电影厂就傻了,记得第一次去报到时老领导就跟我说,“你看墙上挂着的,是我们厂的导演,72个,你是第73个。我们厂最近不太好,一年只能拍3到4部电影,得七十多个导演轮完了才能轮到你。”我一算这得轮到哪年啊。我分到厂里以后三年没有戏拍,但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不是自己没戏拍,而是同学们都开始拍戏了。不过我一直在写剧本,写了很多,《寻枪》只是其中的一个。
△电影《寻枪》
陆川:《寻枪》的剧本给了很多制片公司。后来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到姜文经纪人张蕾姐,她帮我约了姜文。我们在一个酒店大堂见面,聊了四个多小时。后来姜文特别认真地拿了一张纸写,我愿意拍陆川的《寻枪》,签好字后让我把纸条拿给韩三平看。周一一大早,那是我第一次进韩总办公室,我说韩总,您看一下这个。韩总是四川人,有袍哥的气质,他说这(肯定)是你自己写的,我说我哪敢自己写,然后他说,你出去。秘书把门关上以后我就听他打电话说,“姜文,你是给陆川写了个条吗?”然后又把我放进去,说你小子,可以。
其实韩爷一直喜欢《寻枪》的剧本,但2000年初整个中国电影行业都没钱。即使韩三平和姜文都觉得要拍这个戏,规定好了所有职位,韩三平是总制片人,姜文是监制,我是导演,格局搭好了,我们还找了6个月的钱。直到华谊兄弟的王中军入局,由他出资,电影才开始拍。你就想当时中国体制内的电影困难到什么程度,真的没有钱。
陆川:我们是通过电影与时代交流,每部电影出来后才能知道自己是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我不想做跟着跑,跟着哄,参与各种大合唱的创作者。我觉得那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擅长。我已经看透自己了,确实做不到,所以我会千方百计地在各个地方埋下自己想说的东西,埋一些梗。
艾楚怡:一些自己的小心机。
陆川:对。
艾楚怡:我看到一个评价,说陆川总是那么不欢快地走在商业化的道路上,总是不经意地左顾右盼,顾影自怜,你认同吗?
陆川: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顾影自怜,但是左顾右盼是有的,我知道我不彻底,确实不彻底。
艾楚怡:到现在也是这样吗?
陆川:还是不彻底。
2018年开拍的电影《749局》,刚刚开机就遭遇危机。资金匮乏,在硬撑到拍摄结束之后,还需要巨额资金,进行电影的后期制作。
陆川:血盆大口的一个大窟窿。
艾楚怡:一个小目标(1亿)的窟窿?
陆川:更多,1.5个小目标(1.5亿),但是这种窟窿怎么是我们扛得起的?当时我就想,先扛着,先让它做下去。所以我们就不问前路,每天低头做。我把整个任务分解开,我一次肯定融不到这么多。但这个阶段做的事可能需要20万,我不至于连20万都挣不到吧。所以就今天挣点钱,然后拍几个镜头或者完成某一部分内容。
艾楚怡:想过放弃吗?
陆川:这几年很多电影找过来,也会想要不就先去拍个别的,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我都想好了不行就什么都不拍了,必须要把《749局》做完。
传统的电影创作道路被堵住了,就自己再开创出一条路来。为了弥补自己经营能力的欠缺,陆川去商学院学习MBA课程。这些年,陆川拼命赚钱,广告、网剧、舞台剧、亚运会……
陆川:最后靠我自己和两次融资,算是把这个项目顶下来了。
△电影《749局》
这些年 ,陆川从一个产量不高的电影艺术家,被迫成为了一个高产的多面手,一个“小微企业”的负责人。
陆川:人得活在当下。其实这几年我过得很丰富,很扎实,并不寂寞。我相信宋应星写书那几年也是这样的,你看他写得多生动,细节多丰富。
艾楚怡:您觉得自己现在更像企业家,还是和以前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导演?
陆川:我们就是一个小微企业,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得挺正规的。至于企业家这个身份,我一直在给我的搭档们洗脑,你们要成为企业家,你们要有企业精神,你们要有成为企业家的担当……说实话,我还是在排练现场,在创作中,在剪辑房,才是真正的自己,才真的开心,你让我加多长时间班都行。但你要让我开俩公司的会,我可能就想摔杯子,暴躁,烦。
制作人:张燕
编导:王劼
编辑: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