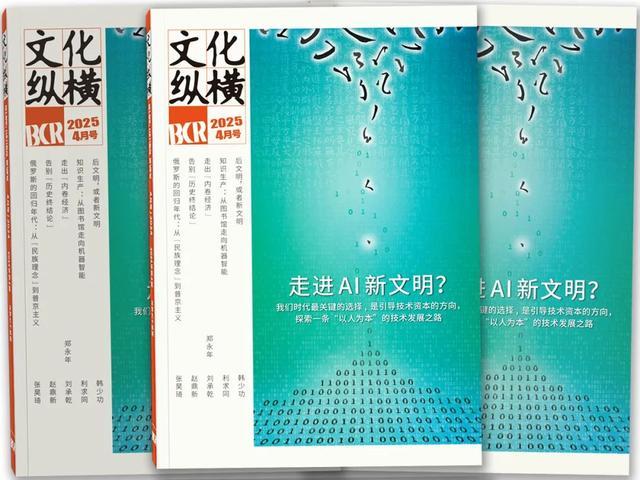
美国国内制约川普关税政策的力量
“对等关税”是美国总统行政权发挥到极致的一次尝试,短期内能对之构成有效制衡的,恐怕只有三权中的其他两权。
国会方面,民主党人本周开始行动起来,由纽约州众议员Gregory Meeks牵头提出一项终止川普关税“国家紧急状态”的否决决议案,并打算通过快速程序绕过委员会和领导层,强行提交到众议院投票表决。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公开呼吁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一起推翻川普的关税措施,维护国会决定贸易政策的宪法权力。
共和党人也有点被关税引发的经济动荡吓到,担心这会影响2026年中期选举。Ted Cruz已经公开表达不满。川普宣布关税第二天,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Chuck Grassley联合民主党参议员Maria Cantwell共同提出《2025年贸易审查法案》,打算重新确立国会对总统征收关税的监督权。根据该法案,总统新实施关税须获得国会批准,否则就会在60天后失效。总统还需在关税生效48小时内向国会通报,提供关税措施的理由以及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评估。在众议院,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Don Bacon打算提出一项平行法案,主旨也是把总统关税权重新收回国会。
但总的看,共和党对公开和川普唱反调还是很谨慎。Grassley在X上强调《2025贸易审查法案》不是冲着川普关税去的,而是因为一直都觉得征收关税的权力本就应是国会的。Mike Johnson和John Thune两个共和党大佬硬着头皮支持川普,Johnson说应该给川普必要的施政自由度,让子弹先飞一会。Thune对关税心里不爽,但在公开场合还是顶川普。
历史上,美国的关税政策一直是国会的权力范围。国会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部重大立法就是关税法案。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1789年7月4日将之签署成法(这或许是川普“独立解放日”这个梗的另一种解释?)
由于关税问题涉及税收水平、政府规模、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阶级经济分化等,其中交织着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博弈。
18、19世纪,国会作为立法机关牢牢掌控关税政策,总统基本上是配合执行或在特殊情况下动用否决权。随着20世纪美国全球地位上升和经济结构变化,出于提高决策效率和应对外交谈判的需要,国会逐步将关税权下放,总统在贸易政策中的自主度大大提高。从1934年《对等贸易协定法》开始,美国总统几乎接管了关税谈判的方向盘,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调整关税、签署贸易协定成为常态。国会不再事无巨细地制定关税税则,而是通过框架立法、设定授权期限和目标来保持影响力。当然,每当总统被认为滥用了关税授权、偏离了立法机关的意志,国会也会尝试夺回关税政策的控制权。
1792年,时任财长汉密尔顿发布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建议征收新关税,但当时还是议员的麦迪逊觉得汉密尔顿以财长身份主导立法议程,是对宪政架构的挑衅和对国会“钱袋子”权力的侵夺。两个开国元勋为这个闹掰,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对政党对立:几年内,汉密尔顿成为联邦党的理论领袖与政治架构师,而麦迪逊则和杰斐逊并肩成为民主共和党的创始人。
独立后至19世纪早期,关税迅速成为联邦收入的主要来源。1812年战争后,美国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关税保护本国工业。1816年,国会通过首部明显具有保护色彩的关税法,提高工业品进口税率,标志着关税政策从纯筹资转向兼顾产业保护。但是这也引发了南北方的矛盾:北方工业州支持高关税以保护本土制造业,抵御欧洲商品的竞争,南方农业州则因高关税推高了进口商品价格且影响把南方的棉花等农产品卖到欧洲而强烈不满。
1828年,国会在亚当斯政府末期通过了《1828年关税法》,大幅提高关税税率(对多数进口工业品征收高达约50%的关税),南方认为该法偏袒北方工业、损害南方利益,气愤地将其称为“可憎关税”(Tariff of Abominations)。杰克逊当了总统之后,南方的不满持续发酵,最终导致“废除条例危机”(ification Crisis):南卡罗来纳州通过“废除条例”,主张各州有权废除联邦立法,并宣称关税法案违宪,拒不执行。坚定支持联邦统一和中央权威的杰克逊向国会申请动用联邦军队对南卡征税、平叛。虽然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关税暂时解决了危机,但也成为1860年南方正式脱离联邦、引发内战的一个导火索。
川普的偶像麦金利在1890年(当时是共和党众议员、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提出“麦金利关税法案”,把美国的关税提高到平均50%的历史高位,并授权总统和外国谈判互惠贸易协定:如果外国降低对美关税,总统可以削减特定商品的关税作为回报。然而,高关税引发的物价上涨招致公众不满,更被民主党的激烈抨击为“保护富人特权”,直接导致共和党在众议院失去93个席位,酿成了美国历史上总统所在执政党中期选举第二大败绩。1892年,民主党主打关税议题,重新夺回白宫,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重新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连续任期总统”(22任+24任)。
1922年,共和党掌控的国会通过《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除提高关税外,还授权总统根据美国关税委员会的调查建议,在不经国会新立法情况下自行将特定关税税率上下调整最多50%(即所谓“弹性关税”机制)。虽然这一授权范围有限,但开创了国会将部分关税决策灵活性转授给总统的先例。
胡佛任内,保护主义者主导的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高位,平均税率接近60%。其实胡佛本人对这么极端的关税壁垒是心存疑虑的,但因为担心和党内国会领袖决裂,不顾上千名经济学家联合请愿和自己经济顾问的反对,签署了该法案。
斯穆特-霍利法案推动美国贸易政策出现历史性转向,也直接引发了国会和总统关税权力的再分配。法案实施后,共和党在1930年中期选举中失去了52个席位。1932年,富兰克林以472张选举人票对59张大胜胡佛(历史上最悬殊之一),民主党也在国会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参议院增加12席获得多数,众议院增加97席形成绝对优势)。当然,大萧条是共和党溃败的主要原因,但舆论也普遍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加剧了经济崩溃,成为民主党攻击的主要靶子。
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后,国会次年通过《对等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在不经国会逐案批准的情况下,与他国协商互降关税协定,并可据此下调美国关税税率最多达50%,以换取对方国家关税对等降低。协定生效不需要参议院2/3多数批准(避开了条约缔约程序),只需总统签署行政协定即可实施,而国会若想推翻总统谈成的减税条款,则须另行通过法案并达到足以推翻veto的多数。
斯穆特-霍利关税实施两年后。国会觉得关税加剧了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一度曾由众议院税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利尔提出一项新法案,旨在撤销该法案赋予总统确定关税税率的权力,将其收归国会。很多进步派共和党人倒向民主党,推动该法案一举通过。时任总统胡佛否决了科利尔法案,国会随后发起了推翻否决的动议,但因在两院没拿到足够票数而宣告失败。
Grassley和Cantewell提的《贸易审查法案》,和科利尔法案很像,本质上都是要让国会限制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但该法案所获势能却和科利尔法案不可同日而语。目前,白宫已经放话会否决该法案,理由是其将 “严重限制” 总统的关税权力,以及制定外交政策、保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从目前的情况评估,《贸易审查法案》不太可能在众议院或参议院通过,更不用说推翻川普可能的否决。当前川普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很强,相比关税,恐怕共和党议员们更担心得罪川普带来的政治后果。
司法分支介入总统关税权力分配,历史上早有先例。1892年Field v. Clark 案中,最高法院审查了麦金利关税法中授予总统的互惠关税权是否违反宪法授权原则。当时该法指示总统若认定某些国家对美征收“不公正的高关税”,即可单方面对来自该国的特定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原告主张国会将立法权不当授予总统。
最高法院在此案中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认定总统此举 “只是在执行国会的政策…并非在创造法律,他只是立法机关的代理人,依据国会预先设定的条件宣布其意志何时生效”。该判例确认了国会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授权总统执行关税调整,而不被视为违宪越权,为日后总统在关税领域获得“受限的自主裁量”提供了司法背书。
在1928年的J.W. Hampton, Jr. & Co. v. United States案中,美国进口商J.W. Hampton 公司起诉福特总统依《福特尼-麦克坎伯关税法》调整关税侵犯了国会在《宪法》第1条第8款中独享的“征税与规制贸易”权力,属于违宪授权(unconstitutional delegation of legislative power)。时任最高法法院首席大法官塔夫脱(美国第27任总统、也是日后唯一出任首席大法官的前总统)代表法院撰写一致意见,强调“国会可以将裁量权授予总统或行政机关,前提是国会本身提供了一个‘明确原则’(intelligible principle)来指导授权对象的行为。”本案中总统调整关税的行为不是将立法权不当下放,而是合宪授权总统在限定条件下执行立法意图。该案确立了“明确原则”标准,为现代行政国家的合宪性授权打下了基础。
对这次川普的关税政策,司法分支的制衡作用很可能会比较突出,主要是川普使用的法律依据不是很牢靠。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国会制定关税和监管国际商业活动的权力。也就是说,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源自国会的授权。
历史上,美国总统通过贸易法征收关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赋予美国贸易代表广泛权力,调查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有权在调查基础上征收关税。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也给了总统对特定关键产品(如钢铁)征收关税的权力,只要商务部能通过调查认定这些产品的进口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些都可以为川普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
但问题在于,使用贸易法需要经过标准的调查程序,通常需要不少时间。例如,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征收首批关税花了11个月。此外,贸易法要求关税必须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产品,面向全球的“普遍关税”或“对等关税”在这里有点找不到依据。
于是,川普这次使用了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来作为征收关税的法律基础。
我们对IEEPA不陌生,因为这是川普和拜登两朝多个对华制裁措施的母法,比如ICTS规则、限制美中数据跨境流动法规、反向投资审查规则等。
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IEEPA,本来是为了限制总统在《与敌国贸易法》下封锁敌国资产、监管金融交易以及管理和许可进出口的战时紧急权力,最主要的是要求总统行使这些权力前要先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且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声明以继续维持紧急状态。
IEEPA的出台,和国会、政府围绕关税权的博弈息息相关。1971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强推“新经济政策”,在未获国会事先授权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关税,希望迫使贸易伙伴重新调整汇率(美元贬值)并保护美国工业竞争力,减轻美国严重的贸易逆差和黄金外流压力。
尼克松援引的是1917年《与敌国贸易法》,用总统行政令实施。当时,这在法律上勉强站得住脚,因为《与敌国贸易法》这部战时法律的部分权力也可以扩展到和平时期的经济紧急情况。但尼克松此举把国会排除在这个重大的贸易决策之外,还是引起国会强烈不满,促使其着手堵住这类行政越权的制度漏洞。1974至1977年间,国会先后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要求总统今后如以紧急状态为由干预经济和贸易,必须正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定期接受国会审查。
从IEEPA的立法历史能看出来,国会原本是希望总统能谨慎使用IEEPA。根据附随该法案的众议院报告,“紧急情况本质上是罕见且短暂的,不应与正常、持续存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但有权者总倾向于把权力用到极致。此后的美国总统在该法实际实施中显著降低了宣布“紧急状态”的门槛,使之成为一个施加经济制裁、干预国际商业活动的利器。据统计,美国财政部30多个制裁项目直接源于IEEPA的授权,17000个外国个人、公司和政府实体被IEEPA实施资产冻结。
但使用IEEPA作为法律依据来征收关税,川普是破天荒第一个。
IEEPA给了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的多项权力,允许行政部门 “调查、监管或禁止” 涉及任何外国利益的外汇、信贷或支付转账交易,以及货币的进出口或补贴行为,还授权总统监管涉及外国或外国公民财产的交易。这也是为什么IEEPA长期被用于实施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但从法律文本里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它给了总统“征收关税”或“征税”的权力。相反,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明确规定在国会出台的1974年《贸易法》等其他贸易相关法律里。美国历届总统出台关税措施,援引的都是这些贸易法。
即使是围绕IEEPA的解释有可以争论的地方,基于IEEPA的关税措施也很难过得了最高法院“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测试。根据“重大问题原则”,当行政机构试图基于模糊的法律授权,作出在政治或经济上影响深远的决定时,法院不会默认其解释为合法。相反,法院会要求国会必须就此类问题给予清晰、明确的授权。
无论是10%的“普遍关税”还是更高的“对等关税”,无疑都属于“重大问题”,需要国会明确的立法授权,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想当然得把IEEPA拿出来做挡箭牌。
今天,美国贸易代表Jamieson Greer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接受关于本届政府贸易议程的听证,民主党进步派领袖Bernie Sanders就围绕这个问题一通发难。在Sanders看来,川普援引IEEPA的“国家紧急状态”征收关税,是“夸大其词”和“谎话连篇”,等于“赋予总统几乎无限的权力去对任何国家宣布紧急状态并实施关税,这是威权主义,不是民主国家应有的做法”。Sanders问Greer:“你真的以为川普宣布个“紧急状态”就能完全绕开国会,重构整个全球贸易体系吗?”Greer的回应显得很苍白,只是不断重复说总统依据IEEPA有权在国家紧急状态下采取措施,这项权力正是国会给他的。
美国国内已经有反对关税政策的力量看到了这个明显的法律缺陷。最近,一个叫“新公民自由联盟”(New Civil Liberties Alliance,NCLA)的NGO代表一家经营办公用品的美国公司Simplified,在佛州地方法院起诉了川普的关税政策。
该诉讼针对的不是这次“对等关税”,而是川普2月1号和3月3号基于芬太尼理由、同样以IEEPA为基础针对中国的关税行政令。Simplified在美国卖日程规划本等办公文具产品,供应链主要是中国商家,因为加关税的行政令承受了很大利润损失。这个NCLA则是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宪法学者Philip Hamburger创办、由一批自由主义倾向的宪法学者和律师组成,政治光谱偏自由意志主义或保守派立场,致力于挑战“行政国家” 。最近该NGO最著名的工作成果是在 Loper Bright v. Raimondo一案提交法庭之友意见,成功推翻了 “雪佛龙尊重原则”(Chevron Deference Doctrine)。
NCLA在诉状里主打的法律论点就是IEEPA作为征税关税的依据不合适,该法根本没有授权总统能去征收关税,因此两个关税行政令都属于行政越权。而且关税虽然是以阻止芬太尼进入美国作为理由,好像有那么点紧急状态的意思,但这根本不是个贸易问题,川普及其团队的多次表态也都说明关税的真实目的不是芬太尼,而是降低美国贸易逆差并增加政府收入,所以不存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也就没有根据IEEPA征税的“紧急权力”。
NCLA还进一步论证说:如果假设IEEPA能被解释为允许征收关税,那就只能说明IEEPA违宪了。因为《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征税权在国会,如果IEEPA把征税权给了总统,就违反了“明确原则”(intelligible principle)和“非授权原则”(nondelegation doctrine)。
基于上述理由,以及关税已经给原告Simplified造成不可逆的损失,NCLA要求法院做出一项宣告性判决,宣布川普针对中国的关税行政令是非法且违宪的。
这两天,美国国内又传出美国商会等多个商业团体正在考虑对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提起诉讼,并且也打算打IEEPA这个点。这几天美国商会在权衡,但越来越多的会员企业敦促商会起诉。这些公司怕得罪川普,不愿意自己起诉,但是希望代表他们利益的商会能去起诉。美国商会虽然不愿意跟川普正面硬刚,但包袱比起单个公司少了很多,以前也曾经起诉过川普第一任期的移民政策。
在立法和司法两权的制约下,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变成一场抢时间的游戏,拖得越久、国内的怨气积累越多,政治和法律上的反噬恐怕随之而来。当国会里的那些反对力量难以压制、商界的法律挑战继续得势,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收拾了。
文章仅做学术探讨和市场研究交流使用,相关判断不代表任何公司或机构立场,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