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宣布将在今年9月11日之前,全面撤出2500名驻阿美军。他说,“(入侵阿富汗)从来不是一个应该延续几代人的事业,我们遭到了攻击,我们曾带着明确的目标开战,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了。是时候结束永无止境的战争。” 与拜登的声明同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会同步撤出约7000名北约联军士兵。
这个撤军决定和中国有关,拜登说,“我们必须追踪和瓦解‘9·11’以来,远远超出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网络和行动。我们必须支撑美国的竞争力,以面对日益增强的、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
初看起来,这有一点不合逻辑。因为阿富汗正是中国的陆地邻国之一,而且又恰好与中国新疆这个西方战略家们眼中的“软肋”接壤,同时还是中国“一带一路”整体布局的重要枢纽之一,基于与中国“激烈竞争”的考虑,本应牢牢占住这个“桥头堡”才对,为什么反倒要撤出呢?而且是在苦苦经营了20年,花费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金钱,付出了伤亡合计2万美国人的代价之后?而且是在没有取得显著的军事胜利甚至连现实的威胁都尚未清除的情况下?
是的,正如拜登所言,到他这里前后四任美国总统都说过要撤军,他不能再把这个决定传给第五位了。
那么,阿富汗对于美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入侵决定也勃焉,撤军宣布也忽焉,背后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战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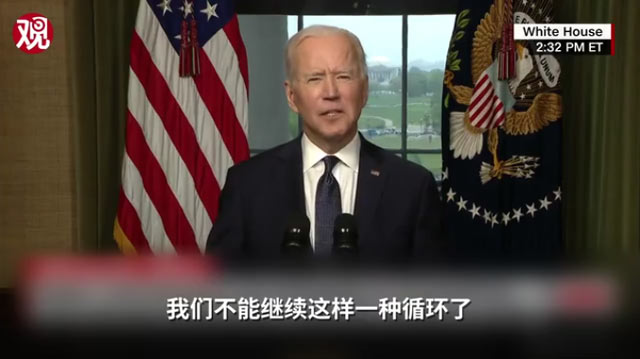
拜登宣布撤离阿富汗,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地缘之事
美军入侵阿富汗,是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关于布什家族与阿富汗,有三个流传的故事:
1991年,白宫官员曾向当时的老布什总统报告喀布尔附近又出现了新的冲突,而老布什的反应是非常惊讶,“阿富汗还在打仗?”他问到。因为在他头脑中,阿富汗不过就是美苏地缘政治大博弈的一个前沿地区,既然苏联撤出了,国家也面临解体了,阿富汗的冲突也应该结束了。
他并不把阿富汗当作一个有其自身历史进程的国家,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时期的阿富汗正是美国此后几十年在该地区面临的一系列大麻烦的开始。苏阿战争的后期,流亡到巴基斯坦、伊朗等地的阿富汗人已有数百万人,这些难民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里,食物和水由联合国提供,四分之三的难民年纪不满15岁,被贫苦、卑微、绝望、仇恨紧紧包围着,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宗教学校。宗教学校由右翼伊斯兰神职人员建立,推广追求“纯净的伊斯兰”的瓦哈比教义。整整一代人将在这种极端环境中成长起来,其政治势力代表,就是日后震惊世界的塔利班。
9年后的2000年,克林顿任期即将结束,小布什竞选总统,提到阿富汗议题时,小布什依然与其父一样,头脑中没有什么概念。被问到对塔利班的看法,布什还以为塔利班是个摇滚乐队。他的外交政策专家赖斯也对塔利班不屑一顾,甚至完全搞反了情况,错将其称为伊朗的走卒。当时的小布什团队正陶醉在新保守主义新的全球视野中,想要在一切地区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私人资本纵横世界开辟道路,所以不想对个别威胁大惊小怪。“我厌倦了打苍蝇。”布什总统对赖斯说。
这一次当然又是大错特错了,“9.11”事件之后,美国步大英帝国和前苏联的后尘,派兵入侵了阿富汗。而这时的阿富汗早已是各路“圣战”武装军阀们的天下,曾经代表了这个国家全部现代化努力的喀布尔已经几乎被炮火夷为平地。从此以后,美国就被一步步拖进了这个深不见底的泥潭,无论是表面上的军事胜利,还是以“马歇尔计划”为模板的“阿富汗战后重建”,实际上都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功。当然不可能成功。小布什满心以为阿富汗的“马歇尔计划”也能让美国一举两得,既帮助了阿富汗恢复元气,又让自己通过投资回报大发横财,可以说,这个错误并不比当年苏联想要将阿富汗彻底改造成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错误来得小。
连续的错误,最终结果就是这个美国历史上历时最久、但今天却“当着敌人的面撤退”了的战争。
结局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都是因为阿富汗仅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进入到了帝国思维中,然后就被当作一个地缘政治的要害之地试图进行占领和征服而导致的错误。当年的大英帝国和当年的苏联,无不是犯下同一个错误。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Great Game(大博弈),以及20世纪中后期苏联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冷战”,实际上共享了同一个地缘政治信条——谁控制了中亚这个“中央欧亚地区”,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而无论是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的“枢纽地带”威胁论,还是荷兰裔美国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威胁论,必须控制阿富汗这一点,都被当作了不言自明的道理。
在这样的帝国思维当中,头等重要的,是让军队驻扎在阿富汗地区,至于阿富汗这个国家本国的利益如何、阿富汗人民的诉求是什么,都是次要的问题。英国当年与阿富汗的三次战争,即使给当地带去了西方化和现代化,推动了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甚至刺激了该国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地区强国的雄心,但是最终结果仍然是摧毁了这个国家。
19世纪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有言:“阿富汗就是一杯亚洲的鸡尾酒,它的战略地理位置决定了帝国、地区性大国和众多邻国都要来搅和一把。”
塔利班“驻联合国大使”哈希米则一针见血:“由于我们地处亚洲的咽喉要地,所以我们承受着苦难,18世纪如此,19世纪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我们没有攻击英国人,也未曾攻击俄国人,但他们都侵略了阿富汗,给我们带来了灾难。”
今天拜登总统公开承认“阿富汗所面临的挑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实际上,100年前被迫与阿富汗签订和约并承认阿富汗独立的英国,和1989年在未巩固战果、未顾及脸面、未保留后手的匆忙之中就将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的苏联,也都是这么承认的。
最初为了垂涎欲滴的地缘利益乘兴而来,最后丢了军队、丢了金钱、丢了脸面败兴而去,近200年里3个称霸世界的大帝国,竟然无一不是如此。
那么,在这个面积只有西藏的一半、人口只相当于一个重庆市的多山贫瘠地区,到底是什么东西强大到可以让近现代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也被迫承认在这里“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呢?
文明之事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牢牢地盘踞在阿富汗广阔的乡村地区。前苏联在撤军前最后几年采取了将部分乡村变成无人区的残酷政策,意图断绝游击队的后方依靠,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导致犹如古老童话般的“乡村共和国”传统社会彻底崩溃,但即使这样,这股力量也没有被打垮。它的更为凶猛顽强的变身甚至从遍布世界各地的难民群体当中诞生了出来。
但同样也可以肯定,这股力量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搭不上什么关系,唯一合适的概念是“部落主义”,因为真正的组织力量来自于个人对部落的忠诚和对部落首领的服从。
阿富汗从未真正成为过一个民族国家。虽然早在英国人入侵之前,阿富汗就诞生过一位帝国首领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将该地区包括白沙瓦在内的五大城市统一了起来,此人今天被很多阿富汗人尊为“国父”;而且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位大力推进现代化的国王希尔·阿里(Sher Ali),让这个国家有了第一个邮政系统、第一份报纸、第一支常备军和第一批兵工厂,甚至有了议会的雏形。但不幸的是,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会被外部帝国的地缘政治行动所打断。
艾哈迈德·沙阿画像
可怜的希尔·阿里国王最后日子是个国破家亡的悲剧,他一边收到了英国迪斯累利政府通过利顿勋爵发给他的威胁信函“在俄国军队到来之前,我们会向你的国家投入一支军队”,一边却在喀布尔城里见到了径自渡过阿姆河不请自来并声称是来“交朋友”的俄国“外交代表团”,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有了足够借口的英国人已派出了数万人的军队,和俄国人一样也不请自来了。
帝国的入侵引起了普遍的反抗,即使傀儡国王向入侵者妥协签订和约,人民仍然自行反抗。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西方入侵在世界各地重复过无数次的“刺激-反应”模式,在阿富汗却从来没有让全体人民通过这种模式而团结起来。恰恰相反,针对外部入侵进行的武装抵抗总是以部落为单位各自为战、分散实施。不仅在各主要民族之间,包括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俾路支人、努里斯坦人、布拉灰人、哈扎拉人和艾马克人等,少有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时候,即使在占人口多数的普什图人内部也是分裂大于团结。普什图社会有个古谚说:“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对付我的兄弟。”在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中,部落是在共同抗敌时能够形成的最大的可以勉强维持内部团结的组织。
然而另一方面,与人们通常以为的情况也恰好相反,正是这种部落化的武装反抗,给外国入侵者造成了比团结一致的全国抗战更大的麻烦。苏军入侵时期,有多达80多个抵抗组织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展开活动,代表了阿富汗境内多达几百个甚至数千个部落化武装团体。这些抵抗组织大小不同、主张各异,最大的共同之处是“捍卫伊斯兰”这面大旗,于是有了“穆贾希丁”这个统称。面对遍布全境、神出鬼没、分不清谁是战士谁是平民的“穆贾希丁”武装团体,苏军的每一次出击都只是很小的战斗,只解决很小的一部分问题,从来不会有大的战役,更不会有“全歼”、“彻底清除”这种军事效果。
美国入侵之后的阿富汗情况更甚,长达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战争已经让整个国家成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丛林社会。苏联占领时期,美国为了让阿富汗成为套在苏联脖子上的绞索,采取了扶持“圣战”武装、大量提供先进武器的政策,使得这个国家在苏军撤离后成了一个军火堆积场,未开封的“毒刺”导弹就有上千枚,机关枪全国人民平均每人一挺。长期成为世界最大武器输入国之一,结果是阿富汗军阀混战的残酷血腥程度也与日俱增,恢复和平、重建经济的前景遥不可及。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看,阿富汗这个国家不仅没有一个连续的国家建构进程,相反却越来越向前现代社会后退,甚至退到了文明早期的蛮荒状态。一位西方学者曾评价阿富汗人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原始的民族,他断言“阿富汗人就像狼蛛,他们会吃掉幼崽”。毫无疑问,在一个人人都像“狼蛛”的社会是无法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
但是,从反抗帝国入侵和异族统治这个角度看,阿富汗这个国家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奇迹。近200年来,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国家在阿富汗先后尝试过最强大的“军事解决方案”,但统统遭遇失败。而导致其失败的力量,恰恰不是团结一致的共同抗战,而是一种内战猛于抗战的部落化分散游击战。
第一次英阿战争,图片来源:wiki
自杀式的杀敌,自杀式的自保,结果却成功了。可以说,在确保生存的意义上,阿富汗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生存策略和生存能力,堪称世界第一。
不能不承认,这也是文明的一种体现,一种最初级的体现。人类文明自古以来,从一成不变、生生灭灭的原始状态中脱颖而出,首要问题不是别的,就是生存问题。只有那些在野蛮人浪潮一般的入侵中和在大自然的一次次毁灭中成功生存下来的社会,才有文明发展可言,否则就是文明夭折、重回野蛮。
阿富汗人一次次面对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最强大的军事打击,他们并不是在面对文明,而是在面对野蛮,一种必欲置整个国家于死地的最大的野蛮。阿富汗总人口不到3000万,流亡到外国的难民一度多达600万,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成为背井离乡的难民,而没有离开的家乡的人也是在无休无止的战火中苟活的难民。但全国人民皆为难民这个现实,归根结底,并不是他们的错。
依靠着最原始的、最无奈的当然也是最野蛮的部落化、极端化武装斗争,这3000万阿富汗人以难民的形式生存下来了,而且正在迎来再一次将世界最强大国家彻底赶出家园的最后胜利。
当然,塔利班的野蛮行径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塔利班又是从野蛮的外国入侵中生存下来的成功策略的结果。无法判断对错,只能说,这是人类文明本身的悖论。
这意味着什么?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阿富汗这样一个两极对立的现实——地缘之事归帝国,文明之事归部落,对于美国和中国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美国,它当下的撤军决定,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在这20年里它第3次以帝国身份占领并控制这个地缘要冲地区的企图也同样失败了。200年来的历史经验昭然若揭,美国的撤出也就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类似的企图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性。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在苏联占领阿富汗的9年期间,美国恰恰是作为苏联入侵这一帝国企图的反面将手插入到了当地部落文明当中,通过不断增加的援助凝聚起了阿富汗传统的部落化抵抗运动。这也就意味着,围绕阿富汗政治的外部帝国和本地部落这两极,美国都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也都获得了重要的经验教训。那么,这就预示了未来的一个可能性:当另一个非美国的大国第4次企图以帝国身份控制这一地区时,美国会很轻易地重复历史,作为抵抗运动的外部支持者而介入进来。
如此来看美国的这次撤军,也就另有了一层含义:美国并不是要完全撤出,它只是要让自己换个角色,更好地保持存在并操控该地区。
再说中国。首先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又是与新疆这一特殊地区毗邻的国家。无论是反恐、遏制“双泛”极端思潮、打击“三股势力”、维护新疆的和平稳定,还是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富汗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国家。
2013年中阿发表了《中阿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中阿引渡条约》和《中阿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合作文件。2017年首次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2018年三方共同签署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这些都是在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基础上发展的双边关系,其前提是,双边关系的双方都是正常的主权国家,既不涉及凌驾于阿富汗国家主权之上的帝国势力,也不涉及分割了阿富汗国家主权很大部分的部落势力。因此,这些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定的关系,对于中国与阿富汗实质性关系的发展只能起到一些很有限的作用。
但是这里有一个对于中国相对有利的因素,即中国可以将阿富汗问题置于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关系框架中进行处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国与国关系是一个久经考验、非常巩固的关系,而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又有着部落社会层面上历史形成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阿双边官方关系过于薄弱的不足。
2014年,中方公开阐述了对阿政策目标,“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发展、友善的阿富汗,愿为帮助阿实现顺利过渡、推进和解发挥建设性作用。” 虽然从目前形势来看,其中包含的关键词——团结、稳定、发展、友善、顺利过渡、和解,无一不是距离现实极其遥远的渺茫前景,但只要将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边关系稳定住并处理好,也并非不能逐步地朝向这个目标稳步推进。
从这个角度再看美国撤军这一行动,可以认为,由于该行动造成了整个地区战略形势的重大改变,对中国在该地区各种目标的实现也会造成重大影响,一些方面也许有利,另一些方面也许更加不利。
但毕竟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无论转向何方,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中国,都必须要无畏地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