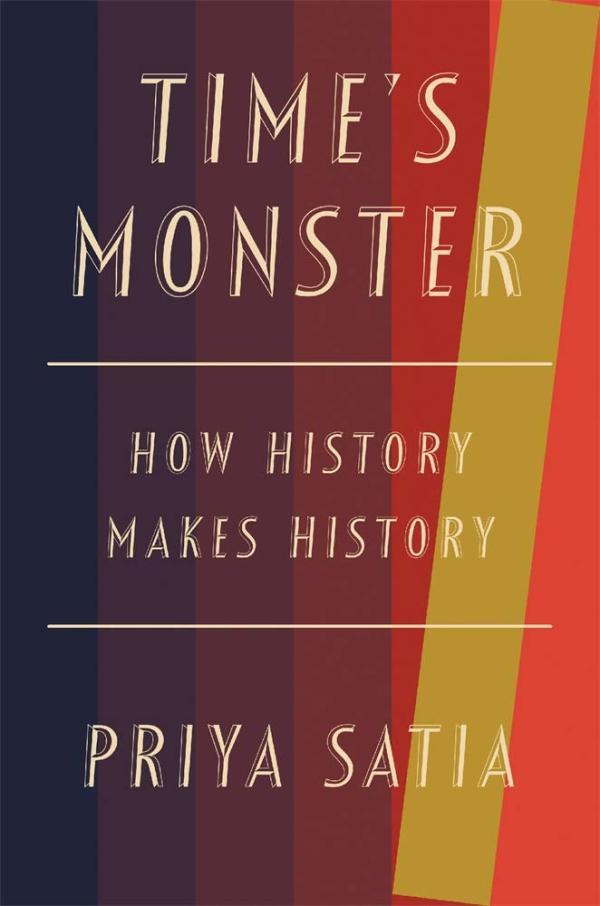
, by Priya Satia,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20, 363 pp
, by Mahmood Mamdani,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20, 401 pp
, by Adom Getache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020, 271 pp作为一名政治学而非历史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的主要关注点是帝国的遗产如何继续塑造我们现在的世界。他之前的大部分著作都在分析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殖民主义对现代非洲政治的影响。他的新书《既非迁居者又非原住民》动人而优雅,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重申并扩展了这些论点,目的是了解困扰许多后殖民社会的极端暴力的来源。马姆达尼将其根源追溯到西方发明的民族国家本身——一个多数民族或宗教“族群”的政体,外来少数民族只是被容忍共存其中。他在书中论及,殖民权力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将定居者的优越民族与他们周围的落后“土著”区分开来。他指出英国人试图“文明化”的第一个海外族群是爱尔兰人,而对原住民的大规模种族清洗,强占土地,建立迁居者的种植园,都曾在英伦诸岛和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各地发生。后殖民时代的内战和种族灭绝之病,与“文明”国家长期以来在其国内所作所为的历史直接相关。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马姆达尼从西方开始。正如他所指出的,美国在建立时并非一个移民国家,而是由迁居而来的殖民者建立的,殖民者刻意灭绝领土上的原住民,偷走他们的土地,以种族概念定义他们,使他们处于低下的法律地位,将他们限制在被随意划定的“部落”领土上,并用与欧洲列强在其殖民地所做的完全相同的方式为这一切辩护。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实践上,美国印第安人及其保留地,都永远陷于英帝国统治下强加给“原住”人民的那种从属地位。(马姆达尼避开了“美国原住民”这个词,因为它伪造了他们与这个迁居者国家的真实关系——把他们伪装为一个政治社群的原始居民,而事实上这个社群从未把他们视为平等的成员。)
雷金纳德·库普兰德(左)和巴勒斯坦问题皇家委员会的另外几位成员1936年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启程前往巴勒斯坦。马姆达尼认为,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为如何处理基于国家的极端暴力铸造了一个有害的模板。纽伦堡法庭并未承认纳粹的种族灭绝是一项政治意义极为深刻的计划,而是以胜利者虚伪的正义感,仅仅将其视为个人战争罪行的累积。与此同时,盟国自己继续在欧洲和殖民地实行民族分裂和驱逐,从而在多民族与种族混居的土地上建立同质化的民族国家。1940年代末他们系统性地将数千万德国人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驱逐出去,并以类似的民族主义理由支持以色列建国。丘吉尔在1944年对下议院说,欧洲的“人口解离”将是一项艰巨但又必不可少的任务:从今以后,“将不再有因为人口混杂而造成无尽的麻烦……将进行一次大扫除”。清洗和净化,一直是种族和宗教方面的迫害与流血事件的首选委婉语。
如今,无论是在南斯拉夫、卢旺达还是苏丹,对极端暴力的标准反制,都是将重点放在恢复法治和追究个人侵犯人权的罪行上。正如马姆达尼所指出的,这种受纽伦堡启发的模式在它自己的时代受到广泛批评,但在冷战结束后又复活了,它不仅永久保留了被强加在种族、民族和宗教身份上的有害的政治化标签,而且在内战的情况下也是徒劳的。其无视历史的手法只是重新树立了基于身份的分裂局面,而忽视了其政治原因——尤其是本应保障正义的国家的民族属性。为了说明以罪行为中心的处理手法对后殖民冲突的局限性,《既非迁居者又非原住民》探讨了苏丹以及巴以之间的历史。在前者,在殖民统治中被政治化、领土化、内化的种族身份,继续主导着解殖后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暴力斗争。在后者,法律本质上的殖民特征,以及针对民族的态度这两点持续存在,使非犹太人公民与居民在法律、领土和政治上的次等从属地位更加僵化。
与此相反,该书举出了南非从种族主义的核心地带到真正的后殖民国家的鼓舞人心的轨迹。这一转变并非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而实现——马姆达尼认为该委员会持有“不正常”的纽伦堡式立场,将重点放在个人罪责上——而是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经历了一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殖民时代的民族身份并未被强化,而是逐渐被非政治化。通过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消弭迁居者和“原住民”之间的诸多法律和政治区别,并相应地改革其宪法和法律,南非人已经能够开始重新想象他们的共同社区,不是作为受害者、肇事者、旁观者或单独的民族,而是作为一个幸存者整体。马姆达尼认为,这是克服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的一个充满希望的模式。(他虽然没有提到,但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大概也符合他的政治解殖模式。)
《既非迁居者又非原住民》倾向于进行大胆但有选择地抽象概括,由此带来的一个局限性是,其论点暗示后殖民政治一直被包括种族、部落和民族国家的殖民时期意识形态所支配。然而,这种方法本身却强化了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目的论。在书中几乎没有出现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战后欧洲防止民族主义暴力重新抬头的努力中起着核心作用,而且对许多新独立的原殖民地领导人也同样重要。埃里克·威廉姆斯在1959年敦促即将独立的加勒比地区人民,他们“在这个万隆、泛非、阿拉伯联盟、英联邦、泛美、联合国、欧洲共同市场的时代”首先应该寻求塑造区域和全球组织,而不是过去那种已显疲态的民族国家体制。他的灵感不是殖民主义的,而是世界性的,主体上并非民族的,而是超民族的。
这部分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身首先是一个国际系统。在其存在的漫长的几个世纪中,它带来了一整套法律、经济和政治的全球秩序,其中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一部分是基于种族等级制度的发明。无论具体控制机制如何,殖民地及其原住人口的最终目的,始终是为了维持殖民者的母国和更广泛的帝国的权力和地位。而当西方大国合作建立新的国际法体系时,他们只会延续这种不平等。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联盟的伟大倡导者伍德罗·威尔逊,经常被描述为受平等主义,以及本质上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概念的动机驱使。但正如阿多姆·格塔丘在她敏锐而精辟的第一本著作《帝国之后的世界塑造》中所论述的那样,这与事实几乎相反。
在威尔逊眼中,维护“白人在这个行星上的至上地位”是战后的终极目标。正如非裔美国人不配拥有国家公民身份一样,对于世界各地的被殖民人口和其它少数民族来说,自治也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个发展阶段,而他们天生就不适合这个阶段,或者充其量是准备不足。1917年后,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盟友将“自决”提出为一项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原则,号召殖民地人民摆脱束缚。为了阻止这一挑战,威尔逊和他的合作者,非洲裔政治家扬·斯穆特挪用了这一术语,但将其重塑为一类种族主义的理想,为帝国统治正名,认为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永久特征。
国际联盟的目标和机制明确地以大英帝国为蓝本。它对国家的定义是分等级的,并以不同的发展概念为基础。一个新的“托管地”体系,即战胜国瓜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前领土,使帝国对落后的“原住”人口的监护原则得以延续(当地统治者的默许足以表明他们的自决权)。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虽然在名义上是联盟的正式成员,但它们的政府被视为低人一等,并一再受到种族主义和虚伪的“人道主义”干预——这为意大利在1935年秋季入侵并吞并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帝国列强对其殖民化的认可奠定了基础。
即使欧洲正式名义上的各个帝国在1945年后逐渐解体,帝国主义化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统治体系的霸权并没有结束,也无意就此结束。就英国人而言,这就是从帝国到“联邦”的过渡,哪怕这是被反殖民主义的抵抗所迫使的。(这就是为什么丘吉尔拒绝承认任何形式的战后“印度自治”,哪怕那是不可避免的。利奥·阿梅里在1943年的日记中坦言:“我试图建议,不能仅靠抵制来面对东方的现代民族主义,通过在形式上让步,我们可以通过条约及其他方式保持大部分的实质内容,但他就是拒绝继续讨论。”)
《帝国之后的世界塑造》展示了大西洋两岸英语地带的黑人反殖民主义者在解殖年代初期几十年中如何应对这一现实。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真正的自决,仅仅把人民从经济和政治的外来统治中解放出来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国际秩序进行彻底的重建。非殖民化这个项目必须同时关注塑造世界和塑造国家。
这本书主要聚焦于一个由七人组成,之间关系松散的小组:富有开创性的美国社会活动家W.E.B. 杜波依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帝国主义批评家之一);非洲政治家纳姆迪·阿齐基韦、夸梅·恩克鲁玛和朱利叶斯·尼雷尔;以及加勒比海各国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埃里克·威廉姆斯、乔治·帕德莫尔和迈克尔·曼雷。正如格塔丘所强调的,他们的愿景是一个更广泛的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各个国家与民族团结反对帝国主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的核心,其他许多跨国运动在战后的非殖民化世界中蓬勃发展。泛非主义、法语国际主义、不结盟运动。但是,她的研究对象的思想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强调几个世纪以来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奴隶制和强迫劳动是如何在建立现代国际秩序中发挥其根本作用: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的等级化与种族化的束缚。
这个团体中较为年长的成员,例如威廉姆斯,曾因193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遭遇而变得激进,他们认为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现状的延续,令人沮丧。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者阿齐基韦不满地指出,这个新组织的宪章对自决权只作了口头承诺。“殖民主义和对黑人的经济奴役将得到维持。”杜波依斯对此也表示赞同:“我们已经征服了德国,但并不包括他们的思想。我们仍然相信白人至上,把黑人约束在自己的处境中,而当我们提到帝国对殖民地七亿五千万人的控制时,就编造关于民主的谎言。”
格塔丘在书中三个节奏轻快但内容丰富的中心章节里,分别描述了一个反殖民主义的世界塑造案例,这些案例都试图克服上述的统治结构。第一项是战后的一场漫长而最终获得成功的运动,将自决权从一个模糊的原则转变为一项坚定的法律权利,并将联合国大会转变为一个推进非殖民化的平台。尽管1960年时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南非表态抵制,但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规定,“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尽管它对“外国”统治的规定似乎为迁居者的殖民主义开脱,但这仍然是一个法律分水岭。格塔丘在这里,以及在整本书中的分析出色地揭示了那些法律和政治变革,尽管通常被解释为原有西方理想观念的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延伸,但实际上是如何通过非西方人的创新(和历史上的偶然)成果,在面临巨大反对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非殖民化从来都不是由强者随意赠与的:它总是要由其下属来争取。
改变国际法只是一个开始。但正如本书的另外两个案例研究所表明的,大西洋两岸的黑人反殖民主义者为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所做的努力实际上并不成功。在加勒比海列岛和非洲,1950和196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领导人都创建了区域联盟,以增强其新民族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并使其逐步摆脱恩克鲁玛所描述的“新殖民主义”陷阱,即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控制,却“保留并扩大其对前殖民地的经济控制”。而他们更加雄心勃勃,但也最终流产的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推动。在所有这些改革中,这项运动将赋权给联合国大会,要求公平地重新平衡世界财富和贸易条款,使之向全球不发达国家倾斜,几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无情地剥削着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
格塔丘对这些计划的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局限性以及最终失败的原因都有清醒的认识,尽管她本可以对苏联和中国如何促进反殖民运动,以及冷战对这些运动的影响有更多的阐述。但她的成就不仅仅是阐明了那一幕结束于1970年代中期的后殖民时代的雄心壮志。这本书重申了反殖民运动在开始时所代表的一个重要维度,如今它仍然令人向往: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国际法律、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如这每一本令人印象深刻、意义重要的著作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要设想一个更好的未来,必须从正确看待过去开始。
(本文原文刊登于2021年7月1日《纽约书评》,由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