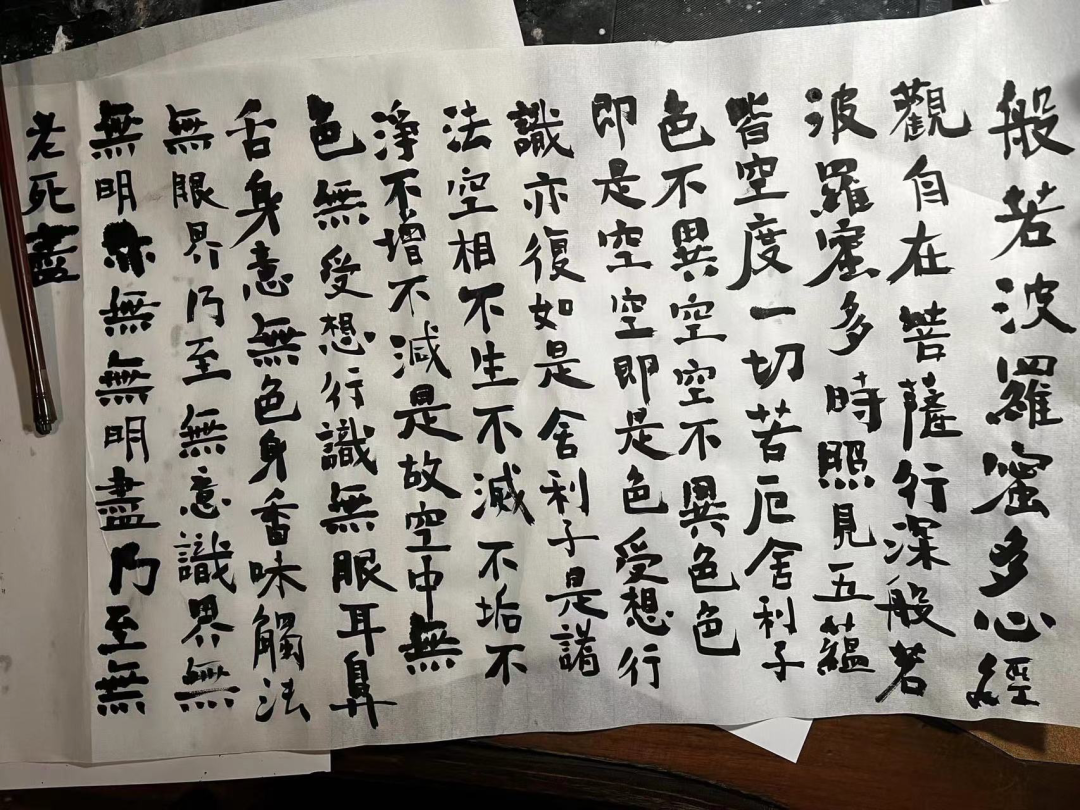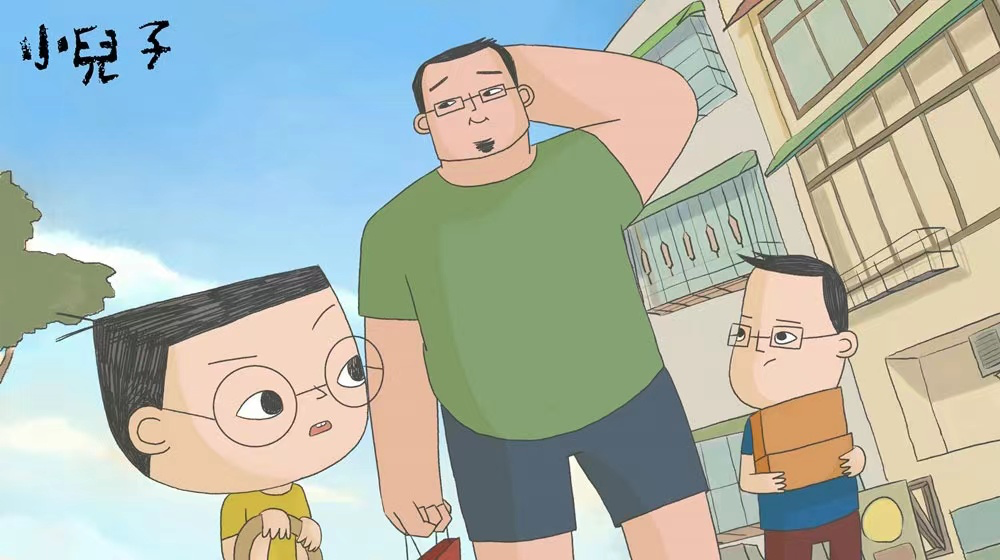采访骆以军是不容易的。一是“时差“,他的在线时间常是凌晨三四点,如小动物般出动,发两个可爱表情包了事。二是他太“跳”,酷爱给人看星盘、讲寿山石,再严肃的对话也被笑声和玄学淹没。三是他“人傻了”。傻是一种温和的自嘲,间带一些现实的锐利——病。
骆以军身体不好,或者说,极差。从牙齿到心脏,从皮肉到神经,乃至他原本超凡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没有一处完好无损。如果我不认识他,会觉得始作俑者是年龄和体质,但不是,只是作家群体多有的、被各类显性的美好——作品、奖项、圈子——遮蔽了的东西:职业病。年少成名的小说家,有一套自我的产出标准,为了完成它,超乎常人想象地嗜烟、咖啡,兑现从伟大文学艺术中习得的自毁倾向。蛮写会早衰,他从二十几岁就知道,并提前准备好。
与过度使用身体不同,他好好地保护了那份多数人都会渐渐失去的少年心性。这是为何年轻的读者会喜欢他,唤他可爱。他对当下年轻人的敏感和困惑也确如亲临,却又绝不带几句轻飘飘的评价,而是跟着想,怎么办呢,太艰难了。这和那个用自己的糗事讲笑话的骆以军,判若两人。我不由得想,是什么让他从悠悠的时光中撑下来呢?在苦和乐之间,是否有那么一种方式,是骆以军式的叙事,是“这世界,我除了作作鬼脸,扯两句屁话,就一无所有了。”
西天取经
骆以军始终记得那碗臊子面。为了吃掉它,他曾跟在一位顶级女杀手身后,横穿火车铁轨,进入有外星军团驻守的高科技基地,完成秘密任务。这是他讲述的版本。另一个版本是,2019年冬天,作家骆以军受梁文道邀请,到北京录制“看理想”音频节目,期间在编辑带领下游玩、探店,吃遍了北方的面食。
口腹之欲,最终喂养了他身体里的一头巨兽。是夜,月亮升起,饕餮出没,骇然从台北旧公寓的冰箱里翻出四十支冰棒、一包萨其马和果冻,全数吞下。“我后来想,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去北京吃的面太好吃了?”说到这,他哈哈大笑,“像脸盆那么大碗,我全部吃光,还外带回去一次。”
贪吃是玩笑话,夜间“清理”冰箱则是他梦游时的无意识行为。由于常年忧郁、失眠、作息不规律,骆以军靠服用大量安眠药过活,药效显著,浑然不知大脑宕机后自己做了什么。这药还让他发胖、变傻,说话丢三落四。今年55岁的小说家,度过了如骑兵、运动员般勇猛写作的当打之年,身体残破如古稀老人。
但这并不是最糟的时候。几年前,骆以军患上心肌梗塞,每周往台大医院跑几次,检查、开药,还差点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加上他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打胰岛素,几番折腾下来,身心俱疲,“那时候以为自己就要像波拉尼奥、雷蒙德·卡佛他们一样,50岁就嗝屁了。”
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是他的大学老师、诗人杨泽。这位怪咖,年轻时意气风发,与木心在杰克逊高地阔论文学,后来到中国文化大学教书,同阶段在职的还有小说家张大春。骆以军读书时,想不到后来有跟着他行走江湖的缘分。这些年,两人逛遍台北街头大大小小的菜市场,找从《儒林外史》里穿越来的人:卖玉石的、卖佛像的、卖茶叶的,还有“给人延命的”。
杨泽,诗人,本名杨宪卿,生于1954年,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毕业,曾于布朗大学任教。已出版作品有《蔷蔽学派的诞生》《仿佛在君父的城邦》,译作有《纪德评传》《窄门》等。
其中一位师傅,好像练过少林功夫,为他们踩背、腿,“通经活络”。还有一位老者,养蜜蜂,据说让它们叮一叮,可以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民间称蜂针疗法。每个星期天,骆以军都会去叮蜜蜂,一开始一针,后来增到二十针,“痛到不行”,“但大家都不喊痛,我也不敢喊”。
不出意外,这套疗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妻尤为焦虑,一方面觉得不靠谱,另一方面是怕他感染新冠,真丢了命。“我脑子、骨子里也根本不信,”骆以军说,“但杨泽算是我的恩人。我人生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老大哥,相信某套系统,用来骂我,想把我从很糟糕的状况里救出来。”
最夸张时,他看到杨泽身上叮了一百针,却镇定如佛陀打坐,大惊。这才忍不住问,“老师,我跟你来了一年多,期间见你带不同的人来过,为什么最后只剩下我跟着你?”师徒关系不像神话故事。在骆以军的世界里,唐僧没有遇见孙悟空,身边只有猪八戒,而他们一起走到了最后。
虽自嘲“八戒”,但骆以军身上有一股憨人和乐天派少有的狠劲儿。他选择报答恩情的方式,与他的写作如出一辙——以身体发肤为代价。他不追究方法是否科学,只要它们有益于重建生活的秩序。在杨泽的带领下,他的嗜好从咖啡变成老茶,从宅家变成接近自然,这已经是本想在三十多岁“殉道”、为了家庭打算再撑一撑的小说家,心态上最大的变化。
骆以军手抄的《心经》
“爹味”与少年气
骆以军是个急性子。他坚信写作的黄金期只有十年、二十年,所以从大学转到文学系开始,人生就上了发条,正式进入倒计时。在这层意义上,身体机能的衰竭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不如视还拥有的一切为礼物。如今,他调整了自己的写作节奏,每天只写两三个小时,“写得超烂”,“要不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我应该在写完《匡超人》以后就不写了。”
那么,剩下的时间在干什么?在书房佯装写作,实则偷偷上网,刷youtube。他最喜欢的节目叫“脑洞乌托邦”,讲世界各地发生的离奇凶杀案,他看后连连称奇,然后被小孩痛骂。骆以军有两个儿子。小时候他们是《小儿子》里的“两呆儿”,长大后变成了父亲的管理者,反过来劝这位不务正业的小说家多读书、少上网,少相信来路不明的信息。采访时,骆以军在家喋喋,大儿子在天台遛狗。他对孩子们的评价是,“他们都很不错,但是可能将来也都不一定有钱。”
没有人会不喜欢《小儿子》里的故事。它们集结于骆以军的脸书,记录了他和家人的生活碎片,实际上是无尽的笑料。在家里,他们会一起读书,但没有人读骆以军的书。享受亲子时光的作家有些尴尬。每当他开始讲人生哲理,儿子们就作鸟兽散。妻子甚至公开调侃他,“爹味很重”。
改编自骆以军《小儿子》的动画
骆以军的妻子郑颖是大学老师。两个人在学生时代像琼瑶剧里的男女主一样相遇、相恋。1996年,他们结婚,蜜月期在大陆度过。《故事便利店》里,骆以军讲了自己如何带着美丽的新娘,辗转南京、南昌、上海、北京,最后在香港摩天大楼上肠病发作,从97层的楼梯间往下狂奔、差点被警察逮捕的乌龙。
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关乎一个创作者要花多长时间学会当别人的丈夫、父亲。早年,他与妻子路遇车祸,当事人还是学生,两人帮忙送他去医院,还垫付了钱。但天生凶相的作家总让人紧张,还好有妻同行,一路上半调侃、半安慰——“别看这个伯伯很凶,其实他比你还害怕”。还有一次,他开车载着小儿子,儿子手上落了鸟屎,愣是被他带去用那只手抽了一张彩票……这样的骆以军当然是可爱的,但也注定是脆弱的、晚熟的。由于这一生都在吃“不够社会化”的苦,他的教育方式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对儿子们重复——不要歧视,不要霸凌,不要羞辱别人。
骆以军一家四口早年合影
两次落榜、一次转系和无数的“废柴”时光,都没有把骆以军变成世俗者。他从未后悔因走上写小说的路而成了穷鬼,但内心的隐痛会突然发作。夜里,他梦见一向慈爱的母亲掏出一张存折,说,你看看这些年我光花在你一人身上有多少钱?“写作非常耗能量,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困扰,”骆以军这样形容自己的选择,“它不是一个能养家的、安定的事业,它是一个职业。”
骆以军是骆家第一个从事创作的人。从二十几岁小说获奖开始,他就得到了身边人很多的爱与支持。他父亲是安徽人,多年后娶了台湾太太,四十几岁有了他。老人不太理解文艺青年的世界,却乐于报以“就算你不是我儿子,只是我恰遇见一这么执着搞创作的后生,我骆某人也要支持你”的态度。这或许是骆以军用近乎“慢性自杀”的方式写作的原因之一:他急于证明自己。
自我证明的同时,骆以军创造了一套自己的叙事方式。在受“文化部”管辖、崇尚IP为王的台湾出版界,纯文学市场狭小,即使是通俗小说,也卖不了多少本。为了好好卖书,上台宣传不冷场,他会提前准备些有趣的小包袱,现场抖一抖。如今,这项本领已经被他练到登峰造极,以至于他在寺庙里讲那些“屁笑话”,方丈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生活中的骆以军比台上更擅长讲笑话。具体如何发挥,要看周遭的环境。“比如三四个人在场,我会感觉到谁强谁弱,谁跟谁在相互伤害,那我就会想让大家都开心。”于他而言,比身不老更重要的是心不变坏,只要没有虚无,没有剥削年轻人,没有失去柔和的瓣膜,他就还好好保护着三十岁以前的自己,那个人生中最骁勇的时刻。
最好的时光
骆以军的九零年代,有一种卡通和武侠片混合的质感。那时,年轻人的世界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巢穴,“每间不到两坪大”,有《千与千寻》里汤婆婆似的房东。其中一间塞满脏衣服、旧报纸、狗毛,中间夹着一个逃了课的胖少年,在被书和纸稿垒得高高的桌前,奋笔抄写《百年孤独》。晚上十二点,他搁笔,向床头的地藏王菩萨叩拜,然后入梦,日复一日。
青年骆以军(右)与友人
这个地方叫阳明山,以温泉闻名,空气中蒸腾着许多虔诚、闪灵灵的梦想。骆以军回忆,三毛自杀那天,有十几个哥们打公共电话通知他,汤婆婆唤一声,他就轰隆隆地往外跑。此地的文学青年多半是抽象的脸,但也不失留下姓名的:袁哲生、邱妙津、黄国峻……骆以军与三人共享的是同一段青春。有时是哲生下榻,他们在灯影绰绰里聊社会新闻;有时是妙津在宿舍与人围坐,辩论文学;有时是国峻,小说家黄春明的次子,很乖,很沉默,“他的路数和同龄人很不一样”。
同龄人的名校光环,一度让“废柴”出身的骆以军自卑,但好的氛围让他可以不为此困扰太久。那是台湾“解严”的头十年,所有摩拳擦掌的新人都可以像参加《中国好声音》一样竞技、争取奖项,他们平等地拥有一条开阔的上升路径。读研究生时,骆以军凭一篇《手枪王》走红,紧接着就有出版社找上门来。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合作机会,比如给一个看起来像没睡醒的人写歌词。他写了两首,拿到一万五台币(人民币3300元左右),觉得对方“很大方”,那是后来火遍全国的歌手伍佰。
再后来发生的一切,愈发像镜像世界般光怪、扭曲,失去纯真的颜色。一年之间,黄国峻、袁哲生接连离世,引发社会震动,人们将此与邱妙津海外留学时的自戕联系起来,视为某种时代的症结。马华作家黄锦树将他们按写作风格归为一类,叫“内向世代”。有段时间,骆以军成为“内向世代”中一个反向的代表,被关心或过度关心,有人甚至直接问他,“下一个会不会是你啊”?
从左至右:邱妙津(1969-1995)、黄国峻(1971-2003)、袁哲生(1966-2004)
彼时的他,的确有些抑郁的倾向,但从未有过极端的想法。摆在他面前的是另一种层面的痛苦。在文学界闯出名气后,出于养家和找到伯乐的期冀,他进入一家出版社工作。结果没多久就后悔了,“感觉他们把几个管线接在我头上,吸取我的脑浆”。最崩溃时,他跑到一家串烧店,问老板制作成本,盘算着是否该开启一门自己的生意,“不如养那个时间,可以写点纯粹的东西”。
作品打入市场,意味着他需要融入业界和圈子。最荣光的时候,朱天心给他题字,王德威为他的新书作序,事业仿佛走向了巅峰。他不容置疑地感到恩惠。于是,菜鸟开始跟着前辈出席各种私人聚会,直面内心对社交的恐惧,发挥自我调侃的功力。他还在杨泽参与创作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新宝岛曼波》里扮演过一个对着美女流口水的人,如今提到仍觉得羞耻,说那只是为了帮忙,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还有一个流传的故事是,唐诺有时在骆以军家附近的咖啡馆写作,遇到他携儿子走过,唤他名字,他不理,只有喊“大师、大师”,他才有反应。骆以军苦笑,说自己早已习惯在特定场合扮演小丑,每当被调侃“大师”,就反说“我是大便”,以至于条件反射,听见那两个字就回头了。
提到前辈和后辈,骆以军流露出罕见的低沉和严肃。他从一个被视为极致哀愁、沉浸于自我世界的流派里走出来,一路走到现在,已经比那些凝固住的生命大了几十岁。他有很多话想代他们说给所有恨不得与世界决裂的创作者。他告诉过胡迁,“你有这种才情,答应我不要自杀”;他也写文章纪念林奕含,拷问“年轻人如何学习这种穿过那伸进你内里之手,仍相信爱与自由”。
但人世之艰难,非常人能抵御。他有幸参与过最好的时光,也亲眼见证网络和市场如何牵引文学代际的变化:过去,大家都很虔诚,为了写出了不起的作品匍匐前进;后来者更用功,抱负更远大,但还愿意接受正规的写作训练;再往后,他几乎看不见不急功近利的人,都在讨论发言权和人脉。“从我这一代到你们这一代,好像只变得更痛苦,被解构、撕裂、粉碎。”
故事的褶皱
贫穷、绵薄是台湾小说家的底色。唐诺、朱天心讲过自家空间不足二十平,容不下书房,于是去咖啡屋写作的故事。骆以军笔下也有好几任房东、一辆除了喇叭哪都响的二手车,以及永和老家的旧宅。他母亲八十大寿时,外地来的亲属进门直接哭了,还凑了钱,想要帮他们改造、翻新。
儿时骆以军与家人
骆以军是“外省人”,跟着上一辈的苦难长大。骆父参过军,逃过难,住过眷村,与当年的一百二十万军民共同组成了那片土地上“无根”的族群。那里有一条特殊的文艺创作的潜流,代表作是白先勇《台北人》和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对于骆以军而言,历史的牵绊更加个体、私密,是一个同父异母、生活在南京的哥哥。
大哥比他大二十几岁,刚出生就与父亲失联,跟着母亲和曾祖长大。两人没见过几面。一次他在南京先锋书店演说,大哥从报纸上看到消息,郑重地带着家人、自种的农产品直接坐到了台下。在骆以军的回忆里,那个场面并不是十足温馨、感人的。他当天讲的是父亲去世,自己因家中男丁不足找来几个好哥们帮忙抬棺材的故事,而这个父亲于对方,是那样遥远和陌生。
关于大哥的记忆,注定是不完整的。中学时,它是一个半导体,从远方传来未曾谋面的亲人的声音;成年后,它是传统的礼节,是他带着新婚妻子向一屋子姓“骆”和“以”字辈的人下跪、认祖,所有人哭成一团;再后来,记忆变成了一种道不明的感觉,是白发老头站在他面前,开口喊他“小弟”,他才能迟钝地辨认出那条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家族遗传的剑眉,仅此而已。
父亲、兄长的身世,是他自我认识的起点。而书写是根植于原生之地的创造,与土地的疏离和经验匮乏,影响的是作家对于情感的处理机制。后来他写《西夏旅馆》,用杀妻、弑父和亡国灭族打开身世探寻的“第三只眼”。他也调动爱身边之人的能力,写下《遣悲怀》、《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西方小说大爆炸和古典文学教育碰撞出的火花,将他推上一浪又一浪巨人的肩膀,也使读者对其写作的印象,多是华丽的词藻、充斥着暴力与死亡的意象,和无边的想象力。
2020年以后,大历史汹涌而来,他开始写《大疫》(曾定名《爱在瘟疫蔓延时》)。但他对成作并不满意。“我认识的人太少了”,骆以军说,把他们流放至孤岛般的世界,非他所长。他也深知自我的局限,因而特别关注社会新闻。采访时,他提起一个当街被殴打的女人,他的故事里也多次出现真实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坠楼事件,还有儿子带母亲遗体搭地铁事件催生的“大众运输法”……
《大疫》,骆以军,镜文学,2022年8月
一切的标本都是波拉尼奥。骆以军对这位“最爱”有说不完的话:上个世纪,他处在怎样的生存境地,如何把底层生活的苦楚和残酷记录下来,这在当下和自己所在的岛屿实现,几乎不可能。因此,网上一切的惊悚、离奇、荒诞,有时比现实更像现实。不过,有些地方天然具备复杂性,为写作提供养分。“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写故事是比赚钱更幸福的事,他肯花时间,用生命的二十年各处走走、记录,那写出来可能就是波拉尼奥。”
游历、观察、记录,是骆以军认为有灵魂的写作方式。这同时是当下创作领域一种较为流行的体例,叫非虚构。童年时,骆以军还不是人们眼中写作的苗子,身边经常围绕着哭诉恋爱失败的哥们,他家里养过后来混迹于街头“黑帮”的小狗,他脑海里如烟花般绚烂的梦境,他超强的记忆力……一切都仿佛为他后来说故事作牵引。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身上缺失的历史和时代厚度、生存经验的宽度,是为在体内凝聚成活水的泉源,随时准备着现代主义故事的大爆发?
“但‘说故事’的我和‘写小说’的我,不是同一个人。”骆以军笑。如果说写小说容易耗损生命值,那么讲故事就是亵神的,“很可能是不小心,你就拨开了神或是魔鬼的翅膀”。听起来有点玄,实则是呼唤人类对一种“发明”的敬畏,是让听故事的人相信,每一个为之发笑、啼哭的时刻,天空中都划过看不见的神迹,你永远都在被看见、被陪伴、被安慰。
对话骆以军:
我们的文明所缺乏的品德
由于骆以军身体抱恙,
以下部分为他给记者的邮件笔答回复
凤凰网读书:《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首次在大陆出版,其中收录了您的处女作《红字团》、成名作《降生十二星座》,书中末篇是写于2005年的自序。如今您已处于下一个人生阶段了,如果再写“序”的话,会想说些什么?
骆以军:会想说什么?应该是感激神灵在这个时刻,会以那为“昔日”的时间刻度。回想一下后来的这十来年,我很开心写了《西夏旅馆》《女儿》《匡超人》这几个长篇,很开心自己的心没有变坏。我生了几场大病,以为会阳寿止于五十出头,但又遇贵人,侥幸从死境拉了回来。但确实已该“知天命”,车子引擎已爆缸而修过,不复有从前的“全线骑兵冲出”的力量了。
《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骆以军,九州出版社 | 后浪,2021年12月
凤凰网读书:王德威说您的作品里有“人渣世界观”,有什么想为那些主人公们“辩护”的吗?或者如果按他的说法,所谓的“人渣”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
骆以军:很像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吧?就是像说“这世界,我除了作作鬼脸,扯两句屁话,就一无所有了”。人世真的很难!!!超乎我每个年纪所领会的难,这有我自己的“人世之衰”与“他感”的外沿、流浪。从我几年前读了波拉尼奥《2666》《荒野侦探》之后,就要抵抗那巨大的构图洞察力:这一切在几百年前,我们所有人努力活着,但都只能是被扭坏塌陷的“人渣”。那些承受过各式超乎想像之痛苦,却无声、或被遗忘、或以丑陋蠢笨之形态示人,但也些温暖的灵魂(譬如鲁迅),传下了那种炭笔素描方法。
凤凰网读书:您在《故事便利店》里提到“这个时代不会有木心这样的人了”,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否是台湾新生代作家的某种集体焦虑?
骆以军:应该不会焦虑,夏虫无法语冰。台湾现在可能没有人把木心当作失落的什么。不只台湾吧,我想现下这个世界新局,很难“再现”木心、张爱玲、沈从文,这些不论冷或热、温润或荒凉,但知道天地多高,有深邃教养的作家。他们那一代人,没有网路、手机,很像犹太教静默教义,把庞大的文明放在自己脑中,真正活在丧乱的、周边的人全都疯狂的时代,又心灵纯淨,爱最美的艺术、文学,简直就像是最挑嘴的、只吃清泉里游鱼的鹤。我们活在用眼耳鼻舌做生意的世界,没办法的,只能把馊水、米糠混在一起通通吃下。这说来话长了。
《故事便利店》,骆以军,河南文艺出版社 | 理想国,2021年12月
凤凰网读书:您如何看待文学世界由“向外扩展”到“向内探索”的大趋势?在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看来,这一代作家缺乏的并非“经验”,而是一种“精神”。
骆以军:(未作答)
凤凰网读书:和大陆相比,台湾文学和出版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包括市场环境、文学机构的建设、大众阅读氛围等等,您可以随意说说。之前我和一位您的读者聊天,我们都很好奇台湾有没有作家协会,新作家和作品主要通过什么渠道出来?
骆以军:应该是蛮惨的。十多年来网路对纸本书的灭绝,现又加上疫情。台湾能一直有年轻创作者,应该说是一件很珍贵的事。台湾没有作协,从我这辈往下,专业写小说基本是非常艰苦、困顿的事。老实说,我根本不能想象,某个角落里、某些和我年轻时一样两眼烧着梦幻光辉的年轻创作者,他们是怎么有一顿没一顿地存活下来的。台湾的市场太小了,如大江(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很多年前说过的,世界(或说日本)的典范人物早已不是大小说家,而是动画片导演或顶尖运动员。事实上这本就是像《金刚经》里描述的已美到没有缝隙的资本主义世界,台湾的出版市场竟不合物理学定律,长出许多颠沛穷困仍认真写小说的年轻人,其实很珍贵。
凤凰网读书:五年级作家的意义上,在岛屿写作的意义上,或者世界文学坐标系中,您如何看待以及面对自己也许不会成为“符号”、成为“经典”的命运?我想这能投射到很多人身上,例如我注定不会成为这个时代出色的记者,这可能也并不是“我的时代”,而我要如何接受这个东西。
骆以军:我曾在脸书写过,“当某个下午,我在某个咖啡屋的角落小桌,写下了一段,我自己觉得马尔克斯、大江或卡夫卡也不过如此的段落,周围没有人知道,但这事已是它的奖赏本身了”。那个饱满、激爽、幸福的时刻。
凤凰网读书:您与社会活动、公共议题似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在台湾是一种常见的写作者状态吗?在大陆其实比较割裂,纯文学被认为“高冷”,基本不回应现实,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可能也会被批评。
骆以军:“小说”或说“二十世纪那些伟大小说”,其实都要颇长的时光去学习体会,譬如我对卡夫卡的摸索、笨拙的领会,是这几年有缘在童伟格的书写难度中我因此多打开的小说矿洞。或是三十多岁时,黄锦树开给我的奈波尔,或是后来读的大江那几本长篇,或我很晚才细细品读的门罗或卡佛,那都不是我最初习艺十年曾碰到的,难度颇高的内向宇宙。或宋明炜推荐我的《洪堡的礼物》,其实一定有一些“大词”,譬如高贵的可能、厚重油漆后面的无言的旷野……这在我的摸索学习之途,没有停止过深感那个构图的难,建筑的难,可以演奏一首钢琴奏鸣曲的难。
也许它持续没有停歇地在回应现实,但如我所说过,我们的窗望出去的风景,有毕加索、有塔可夫斯基、有卡夫卡、有芥川、有波拉尼奥,太多太多了,掩面哭泣的女人、某颗齐白石的篆刻印章,里头有东西早被动过手脚、被摘掉平衡半规管、不可能完整如青叶瀑布的原初了。纯文学常常并非“高冷”,而是搜寻、描绘这个时代的人类之苦痛,要运算的算式真的要耗太大的能与时间。很像这两年我们如此有感的病毒与疫苗的追与逃逸。
凤凰网读书:您讲过自己在出版社当编辑的经历,后来不想干了,说不如去卖串烧,还真的考察过一家叫小猫熊串烧的地方。现在如何看那时候的“不社会化”?或者放大了说,如何处理工作和创作之间的冲突?如今,我目光所及的很多年轻写作者还在用工作养爱好,有的为媒体撰稿,有的工作和文学完全无关。
骆以军:这都很艰难,我是很后来才读到常玉,真是衰到让连我这么衰的人都流泪。我现在还是“不社会化”啊。这真的是非常辛苦、折磨那年轻人天赋灵光的二三十年。但好不容易极少数侥幸能以自己年轻、意志,成为“文坛”中的一部分,却如《儒林外史》里,用空洞的情感和话语,当成生意或当官,也搞一些无聊的斗争啦、是非啦。这真的就不如最开始时去卖串烧,然后养那个时间可以写点纯粹的东西。
常玉(1900-1966),近现代画家,与徐悲鸿、林风眠熟稔,颇具个性,不读美术学院,拒绝商业创作,因而一生窘迫、默默无闻,后因家中煤气泄露中毒离世。
凤凰网读书:您年轻时一直在抄书,为了克服“阅读障碍”,就此想向您讨教一些有用的阅读与写作方法论。因为现在不仅是“年轻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文学时代,还已经是三分钟讲完一部电影、一条视频讲解一本书的快时代了,好好读书、读好书和读懂书变得难上加难。
骆以军:我不知道,也许十年前我还能对这件事说说嘴。如今我的感觉像,我是否是一个生活在北极、靠补猎海豹为食的北极熊,恰好“天注定”活到了一个交迭的新时代,冰块全融了,和所有生物一起掉进大海,必须适应此后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新世界?我只是恰好生在一个“人们都说贝多芬、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珍稀的”的时代的最尾端?我在youtube上看到大英博物馆的分集介绍,迷到不行;我看陈丹青的《局部》,迷到不行;我从一个叫“马可说电影”的节目里看了成濑巳喜男、沟口健二的电影介绍;我看“老高与小茉”,知道了各种有意思的遗传、古人类、宇宙源起、地球末日知识;我也看一些讲世界上不可思议的凶杀案或失踪案的节目。这些讲者对这些知识的理解确实都远超我。所以我是得到了这个时代的好处的。
《局部》(2020)
但确实,花上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持续地读川端康成、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是多么幸福、奢侈的事,而它们真的无法被“三分钟说故事”取代。你想你必须是一个多奢侈的人,每天最少有三四个小时,没有其他事来烦心,像品一杯最昂贵的威士忌,像享用一篇门罗的短篇、一本昆德拉的小说一样,感受那完全将你包裹起来的句子的灵性。比起像《千与千寻》里变成猪、狂吃馊水的爸妈一样,被强迫吃那么多垃圾故事,这真的也很麻烦,像全部的人都疯魔出动,到古玩摊捡漏,却发现价格让人乍舌,或像某个在云南边城的女孩,日复一日地要和不同的缅甸小哥砍价,把一颗开价五十万的翡翠原石砍到七八万成交。这里头神奇的或戏剧性的部分,其实非常单调,除了价格,无法给人提供什么领悟。但已少有人静得下心,好好地感受一个下午,感受一只优美的汝窑或定窑或曜变天目,它那沉静、深邃的美。
凤凰网读书:您认识林奕含、胡迁,也在文章里提到年轻一代与前辈的关系,本质上有权力的不对等。但年轻人自我不够强大,对此不敏锐,甚至容易合理化它,像有个流行词叫PUA,当大家都喜欢听社会地位高的人讲道理,爱喝“大师鸡汤”,该怎么“穿过那伸进你内里之手”?
骆以军:我喜欢许寿裳在推他的亡友鲁迅时,说的那样两个字: 诚与爱。他们可能在一百年前就痛心疾首,我们这个文明,缺乏这两样品德。这真的是非常艰难的提问,甚至在我的想象中,它可能是最接近小说里那团光晕或黑影的内结构,否则我们不会觉得《红楼梦》那么伟大,《金瓶梅》那么神。但我们有幸从二十世纪的小说入门,它一定只是个观测和思辨的入口,这只是因为我们学习演奏的这个复杂乐器叫“小说”。
有更多的人们在他们领受爱与荣光的同时,未必需要去离析,“这也许只是某种关系网络,是短时间看不出的买卖”,或真的是古典的“知遇之恩”?这之间如你所联想,“异性”之间的吸引,如果放进一定的时光中,更能保护特殊才能的专注运作?或许,我们不自知地从二十世纪累积至今的电影、广告、时髦昂贵美丽的衣香鬓影中,提萃了某种欲望,才会“可怜身是梦中人”,觉得彼此“相濡以沫”?这个缠扰,直到我成年很久很久以后,仍然让我有不舒服的感觉。
不只是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文明里的成年人,在某些理想的投影中,都是不强大的。那些在依傍、群党、服从、世故中的玲珑巧变,也许是让更聪明的人更能取得安全感的“海床岩礁”。你看《三体》,地球人对于远高于自己的外星文明,最乖异的发明竟是“面壁者”,也就是这个文明最高的艺术,竟就是骗术。这个“小行星带”,我自己在这个年纪的感慨,是“用小说这个心灵技艺,或许无法穿越它的范域限制”。因为学习、感受的整个过程,都是同时被搅碎混搅其中,“爱”、“忠诚”、“宽恕”、“柔慈”,这对我们来说,那么难以言喻、神摇意夺的一切。你看,我这样反复翻看,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想你们势必比我的时代更艰难,因为那必须把自己放置其中,跟着无边际旋转的单位碎片,更细小,更纷杂,更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但我想古来“大师”,并非“社会地位高的讲道理者”,而是真的有某种光亮、力量、神性、创造的人。我是这么想的。我年轻时是被梵·高激起“要当个创作者”的念想,然后在途中遇见了不同的人,我在其中学习摸索了那么长的时光(已早超过梵高自杀之年龄),现今看他的画仍是那么激动、感动。这样说的话,像不像我是一颗粒线体?因为我们能感受、享有的“美的维度”,早已超越这个个体原本在生物学设计,能达到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