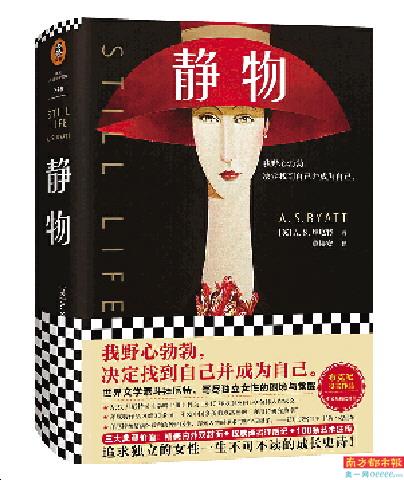
《静物》,(英)A.S.拜厄特著,黄协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版,88.00元。
□ 谷立立
放眼当今西方文坛,大概很难找到像拜厄特这样的女作家了。她的小说常常被评论界贴上“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标签。但如果按照19世纪盛行的女性主义写作标准来评判她的写作,恰恰又是不妥当的。《静物》是拜厄特“成长四部曲”的第二部,哪怕她早早地把“成长”的主题(且是女性的成长)摆上了台面,我们仍然不能指望这样一位出身名校,集作家、学者、诗人于一身的精英人士会像她的前辈乔治·艾略特那样,循规蹈矩地创作一部严格遵循英伦传统的小说。
《静物》的开篇,有一个发生在皇家艺术学院的会面。1980年,62岁的剧作家亚历山大偶遇曾经暗恋他的女子弗雷德丽卡。在看了一整排凡·高的画作之后,他郑重其事地邀请弗雷德丽卡,去看一幅马德莱德·伯纳德创作于1888年的静物画。画面上有两只梨、一束鲜花,放在鲜红的盘子上,四周是黑暗的背景。这本是一幅简单的静物画。弗雷德丽卡偏偏要“脑洞大开”,读出了太多女性命运的隐喻:花果是马德莱娜身体的象征;四周的黑暗既是她刻意设置的背景,又是她将要面临的生活,以及由这种生活引发出的深层的疏离。
不过,谁都不知道马德莱娜究竟有过什么经历,而弗雷德丽卡的人生却是显而易见的。她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如拜厄特所说,这是一段“非常平静甚至被遗忘的时光”:十年前的世界大战已经尘埃落定,十年后的激进时代还没有正式开始。整个世界就像一幅静物画,“只有现实问题,没有思想问题”。而弗雷德丽卡一家呢,则与当时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抱着朴实的心态,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彼时,她刚刚考入剑桥大学,一心只盼望着逃离无趣的父母,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她的姐姐斯蒂芬妮则恰恰相反,明明可以跻身学术圈,偏偏要嫁为人妇,回归家庭。
这样的开篇看起来很简单,但要真正读懂《静物》却并不容易。拜厄特自称,她想要“那些会消失不见的东西”。于是就有了所有注定会“消失不见的东西”:文学、哲学、艺术、博物、心理分析……这里不难看到拜厄特的热情。或者说,她不是要捕捉世界的精妙,而是要把整个世界一滴不漏地搬进小说。因此,无论是描写一间卧室的陈设,还是将神像的脸蛋形容为“瓷娃娃”,或者记录一场为受伤孩子举办的晚会,甚至观察、讨论蚂蚁的群居生活,都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相反,它们都是拜厄特挚爱的物事,从不同侧面映衬出人物的命运。
于是,阅读《静物》就像走入了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家的花园”。园子里长满了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鸟儿从头顶上飞过,虫子在草丛中穿梭。如果我们停下脚步细细倾听,更不难发现远方那片由拉辛、狄更斯、莫里哀、亨利·詹姆斯、庞德、毕加索等名家组成的文艺丛林。毫无疑问,这是拜厄特的名人堂。只是,简单地记录名人名言,从来不是她写作的目的。相反,她比普鲁斯特走得更远。她是严苛的文学教授,也是百科全书的编撰者;她记得每一朵花的颜色,知道每一棵树的名字,更要将树木的生长与人物的成长,放在一起加以类比。在《一棵单木成林的树》一章中,弗雷德丽卡的弟弟马库斯发现了一棵树。它枝叶繁茂,“细桠生出绿叶,主枝分出细杈,躯干又生出主枝”,如螺旋般分叉开裂,盘旋而上,虬结不平的枝干“呈现出充满几何美感的规律性”。
不过,有着“几何美感”的哪里只是一棵树,更包括斯蒂芬妮和弗雷德丽卡。姐妹俩就像从同一棵大树生出的两根枝桠,看似纠结成团,却又彼此独立,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因此,为了烘托两人的命运,拜厄特写得细碎而具体。在她这里,“静物”具有多重含意。表面上,它是西方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7世纪以来,不同流派的画家都把花卉、蔬果、书籍、食品、餐具当成永恒的临摹对象,留下了大量经典画作。然而,“静物”也可以是一种生存状态:鲜艳的红色代表精神、肉体的伤害,深沉的黑色是“死亡”的象征。以斯蒂芬妮为例。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分娩后,她生下儿子威廉,将他视为瓶中的花朵,“花茎是淡绿色的球体,叶子坚挺,像从花瓶里冒出来的尖刺”。而她自己呢?她哪里有什么自己,不过是新生儿的“妈妈”,是围绕着初生花枝的“淡色的影子”。
与困居家中、不问世事的姐姐不同,弗雷德丽卡的人生反倒是顺风顺水的。她与诗人、剧作家交往,观摩剧团演出,参加诗歌分享,“进一步深入思考了人类认知和风格建立的细节与道德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并不代表她有着多么前卫的观念。骨子里,弗雷德丽卡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维多利亚气质,习惯性地把女性当成男性的附属。甚至,“她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婚姻的女人是不完整的,每个美好故事的结局都是婚姻”。于是,就像奥斯汀笔下那些19世纪的女子一样,她满心期望通过社交,找到她的理想丈夫。
事实上,每个美好故事的结局并非都是婚姻。就像静物画。这是色彩的艺术,也是光影的艺术。以凡·高为例,他的画作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浓艳的色彩,更在于无处不在的光。因为光是“审视事物秩序的深邃目光,在这种目光下,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但弗洛伊德又告诉我们,光并不美妙。它就像生命的哲学,预示着每个人共有的归宿。凡·高越是像夸父一样追逐灿烂的日光,越是无法掩饰他内心的脆弱。回到小说,当斯蒂芬妮意识到她“不被重视、已经麻木的自我终于苏醒”,她才发觉自己早已习惯了独处,习惯了沉默。同样,当弗雷德丽卡绞尽脑汁与不同男人周旋,她终于明白他们不过是她年轻生命里的“一个参照点”,既不能改变自己,更不能拯救他人。那么,这是女性的囚禁,还是女性的自由?或者说,是女性觉醒的开始。因为不管是归隐家中照料婴儿的斯蒂芬妮,还是汲汲于寻找灵魂伴侣的弗雷德丽卡,说到底都是一幅沉默不语的“静物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