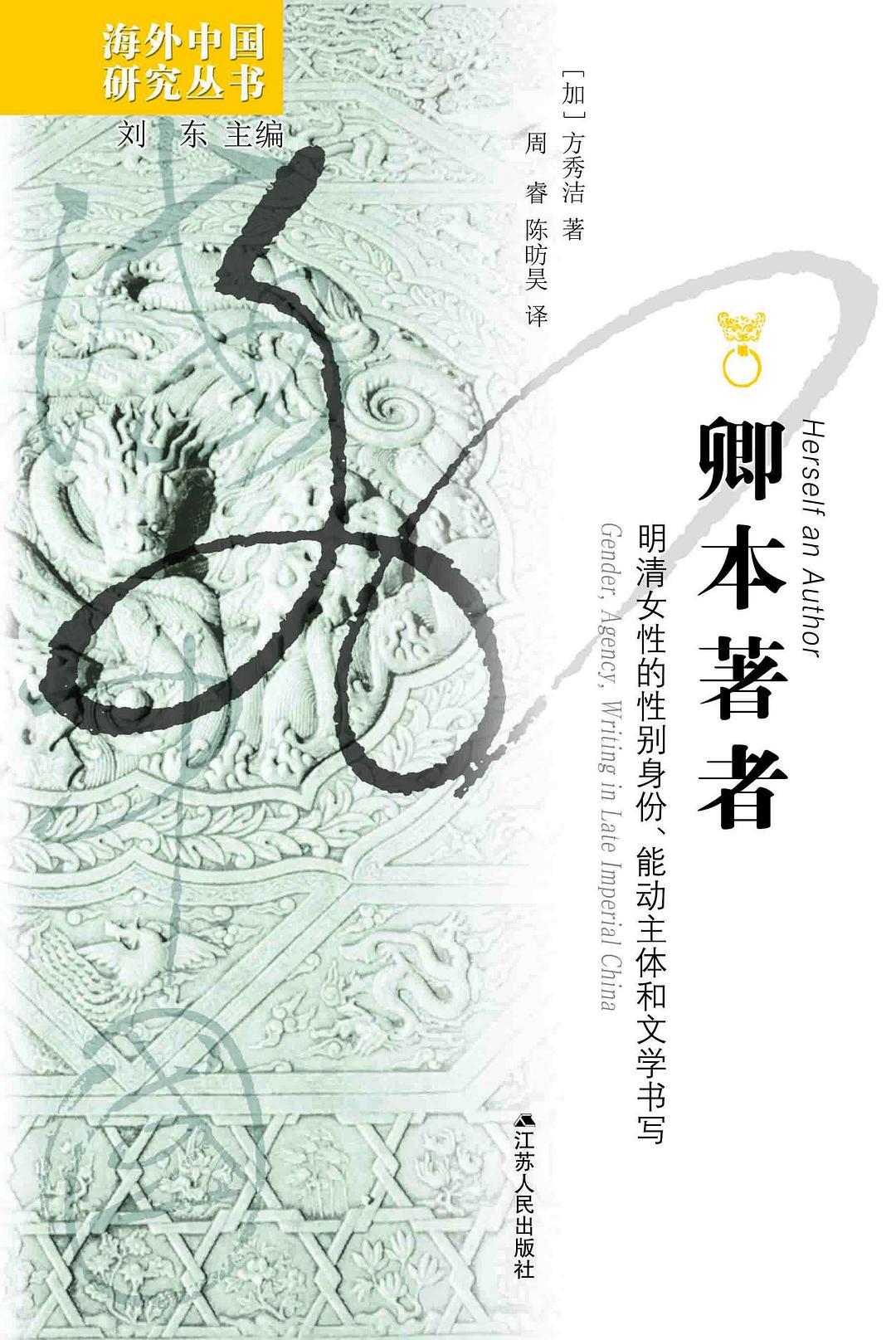
《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加]方秀洁著,周睿、陈昉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264页,68.00元
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帝制史中,关于女性文学文化的写作往往被视作非正统材料,在历史中尘封。尽管一些精英阶层的女性凭借出类拔萃的文学造诣跻身典范,但也仅是浩瀚的文学长河中几处零星的闪光点。边缘化与从属性,足以概括长期以来女性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中的角色性质与讨论范畴。长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多囿于文学史梳理和专题研究两种思路,难免陷入简单认识“她们”的窠臼,而未有讲述“她们”的自觉。诚然,对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梳理是必要基础,不过,阐释文本的方法与路径才是学术研究的关键。如何在社会、地域、性别、历史等多维度视野下处理文本,构建新的研究支点,方秀洁《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为女性文学研究呈现了一个绝佳的范例。本书的英文原版(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十五年之后终于翻译成中文,今日读来仍是胜义纷呈。
方法与史料
过去的几十年,随着明清闺秀诗文别集被大量发掘,这些重见天日的珍贵材料为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底本。此外,伴随着上世纪以来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文学研究逐渐深入到性别与历史、地域、社会等多维度的跨学科探索。其中,海外学者发声较早,至今为止已累积了不少实绩。作为汉学家的中坚力量,方秀洁教授长期致力于古代女性研究,其著作《卿本著者》立足于“性别身份”“能动主体”“文学书写”三个概念,探讨讲述“她们”的方法。女性作为能动主体是如何在传统规训下进行文学实践的?她们如何在写作中表现出性别独特性?诗歌对于女性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卿本著者》无意通过构建经典的两性对立解答这些问题,正如书中所言:“经典本身更多是让人以管窥天而非骋怀游目。”(Canons can blind us rather than broaden our vision.)由此,本书在反传统意识形态的视野下,立足于社会与时代背景,以回归历史语境的态度解读文献材料,在传统叙事外另辟蹊径,既在宏观上勾勒出了明清女性群像的总体面貌,又细致描摹出闺秀才媛们各具特色的生命力与文学创作,真实地呈现出十七世纪早期至十九世纪中叶明清女性的文学实践与自我表现。
《卿本著者》英文版
女性写作常因现实境况受阻或中断,她们的手稿、出版作品的流传范围小,保存不多,珍本更是难觅。方教授花费十余年的时间奔波于中美图书馆、古籍库中搜寻史料,于2005年主持建立了“明清妇女著作”数字化项目,网站运作至今已汇集了四百余部女性作品,不少珍贵文本得以重见天日。
《卿本著者》中的大量坚实文献亦得益于此,全书主要分为四个章节,选取不同的研究对象与主题展开论述:第一章以江西闺秀甘立媃作为个体研究对象,根据其自传诗集《咏雪楼稿》的布局——《绣余草》《馈余草》《未亡草》《就养草》四卷,按照其刻意区别的四种身份——少女、妻子、寡妇、母亲分别解读,通过阐释个体在生命不同阶段的能动性创作,呈现女性以诗歌记载意识与构建自我的过程。第二章讨论妾妇的文学实践,从语言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古代纳妾现象及“侧室”等词义的阐释入手,揭示女性身份称谓与中国空间结构文化暗合现象。作者进一步选取了汪启淑的《撷芳集》“姬侍”卷、沈彩的《春雨楼集》等为特定文本阐释妾妇文学的辑录与创作,揭示这类群体通过文学表达自我及改变社会从属地位的过程。第三章考察女性行旅与记游文学,选取了邢慈静的《追述黔途略》与王凤娴的《东归记事》两部游记散文,以及李因的诗集《竹笑轩诗稿》为研究文本,考证了明清女性在特定地域与变动空间中的文学实践。第四章研究女性文学批评与社群构建,以分析女性在书信与诗歌中的文学交流为楔子,进一步阐述四部女性诗选评注本:沈宜修的《伊人思》、季娴的《闺秀集》、沈善宝的《名媛诗话》、王端淑的《名媛诗纬》,通过分析诗集的编撰、序言、条例等文本,探讨女性诗学批评的构建过程。
除了呈现选本自身的文献价值外,《卿本著者》在阐述文本时所体现的文献钩稽之功亦不可忽视。无论是自传诗集、行旅写作,还是诗歌批评、选集,作者始终秉持追根溯源的态度,以明晰每个主题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此外,对所选底本并不囿于纯文学研究,而是从梳理誊抄、编排、刊刻的整个编撰过程入手,辅以地方志、人物传记、史书记载等材料交叉考证,从语言、社会、历史等方面多角度观照明清女性的文学实践,体现出极为宏阔的学术视野。
讲述“她们”
(一)妻与妾
《卿本著者》用近一半的篇幅分别探究了妻子的自传诗集与妾妇的文学创作。本书并未将二者作直接对比,而是各为一章独立分析。但通过对妻与妾在创作中的自我表达与权威构建,女性阶级中不同身份的异同不言自明。正妻有法律和仪式赋予的地位,出身较优渥,拥有一定独立的经济资源,这些现实因素使得她们在写作、出版等行动上享有更大自由度。并且,从书中对甘立媃、邢慈静、王凤娴、沈宜修等人的阐释可见,正室作为家族“嫡母”,“子女”始终是她们诗作书信中的重要主题之一。相比而言,亲权被削弱的妾妇们在写作上则很少涉及子女。值得一提的是,正室的地位也促使她们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在遭遇事变时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甘立媃早年失去数位嫡亲,出嫁不久后丈夫又离世,她独自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长达几十年,“万苦与千艰,尝尽转安适”;邢慈静的丈夫客死他乡后,她毅然带着两个儿子将丈夫的灵柩从贵阳送还故乡山东,“不手厝家寝,死且不瞑”;沈宜修在编撰闺秀总集期间痛丧二女,因而收录了不少母亲悼亡儿女的哀作……正室严格地履行作为妻子、母亲的职责,极其在意世俗的规训,类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书中列举的女性自我书写中更是比比皆是。
对于妾妇而言,这样的传统道德思想束缚则小得多:大胆书写闺情的沈彩,借诗歌直抒对身体、感官、才能的热爱;柳如是、顾媚、董白、李因等人,完成从名妓到妾的转变后,“侧室”反而成为她们远离浮世、继续进行艺术创作的庇护所。她们与丈夫共同创作,参与校勘、选集的工作,一些妾妇因为文学成就获得社会认可,将后者转化为文化资本并建立起学术权威,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转变。不过,该群体同样面临着困境:侧室通常因为卑微的出生(家主从贫困家庭或妓院购买)而被视为一种商品。在《卿本著者》中,我们可以看到小青、袁倩、李淑仪等女性在不幸的婚姻中遭遇正室排挤、丈夫冷落,甚至沦落到被放逐的凄凉境地,这种社会从属地位使得理想婚姻成为了决定她们命运的关键。
在这两章妻与妾的叙述中,我们既见到背负着深重道德使命的妻子如何在自传的编排与书写中完成自我构建,亦见到妾妇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边缘化的境遇下,如何通过文本创作反抗、建立权威。这些女性通过文学创始冲破传统的藩篱,实现了将能动性与主体性从文本到现实的过渡。
(二)变动空间
中国的记游文学以魏晋六朝的山水行旅诗为发端,再到唐代的游记散文、北宋的行旅日记,发展演变由来已久。而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下,出游是男性的特权,除了归宁、宗教等特殊原因,女性外出机会极少。直到晚明以后,社会风气更加开放包容,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越来越多的男性友人支持女性出游,种种因素促使女性越出闺门的迹象渐增。鉴于此,《卿本著者》关注到了其中一种特定的形式——行旅,这一主题的选取依然建立于对女性能动性的探讨上:长期的传统思想规训,加之习惯以男性文学来构建自我表达,女性的创作总是缺少完整的性别特质。而闺门之外的行旅,使得女性身处于无序而不稳定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中。陌生的遭遇、新奇的见闻,无疑赋予了女性表达自我与拓展写作主题更多的可能性。
本书选取了几种不同的出游类型:扶柩还里、行旅抒情、宦游羁旅,以此呈现女性在变动空间中不同的书写与记录形式。一方面,以邢慈静与王凤娴的游记散文作为特定文本。和诗歌的精炼与形式化相比,散文无疑是更能记录细节与挥洒情感的体裁。此外,二人截然不同的现实处境使得创作风格、主题亦各有特色,沉重的归家之路与新奇的自然审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本章探讨了深谙“闺门内外”双重世界的女性,以妾妇李因为个例,她因为复杂的人生经历颇具见识,从而形成超然深邃的诗歌风格。在随夫宦游的路途中,李因和男性同伴们通过诗歌形式娱乐、切磋,在漫长的旅程中创造了一个有序的创作空间,这是女性以写作建立权威的又一新形式。
(三)女性诗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史悠久,但基本是在男性文人群体为主导的理论框架下构建而成,直到明中后期,女性文学批评才开始发轫。伴随着印刷业发展甚隆、教育普及渐盛,女性逐渐从冗繁家务中暂时抽身发展文学。受心学、性灵说等思想的影响,自由自发的理论成为了女性文学讨论的重点。在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下,女性对于文学参与的渴望已经不止于创作,而是进一步试图成为更加权威的批评家,她们结合已有的诗学理论推陈出新,从而构建出女性诗学的独特范式。
从简单的文学交流到设立明确的批评标准,女性在逐步构建诗歌批评理论的过程中,具体参与了哪些工作?她们在收录诗歌时所采用的批评原则及其意义是什么?与男性编选女性诗歌有何不同?为了厘清这些问题,《卿本著者》首先探索了女性讨论诗歌创作理论的个案:以沈彩与汪亮、袁枚随园女弟子为例,考察了她们以书信与论诗为媒介,作为彼此读者和批评者的交流过程,以此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文人参与到诗话、诗歌批评撰写的工作中。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比较了男女编者的差异:从时间维度看,男性收录的诗歌范围甚广,从远古跨越至当代;女性则更倾向选择同一时代的女性诗歌。其次,男性编者通常会有部分“固定名单”,以示对过往经典诗集的尊重;女性编者的收录则透露出更加鲜活的生命力与情感:沈宜修在编《伊人思》期间失去了两位女儿,诗集有意选取了多位母亲丧女的悼亡之作。季娴编撰《闺秀集》的收录标准无论身份而专注诗歌风格,延续了《撷芳集》收录妓女诗的传统。王端淑与沈善宝为首的女性编者,为尽可能地保存女性诗作更是不遗余力,秉持“诗以人存”“意在存其断句零章”等理念,耗时多年接力完成了《名媛诗纬》与《名媛诗话》两部集大成之作。
女性诗选评注本在倾注对诗歌的热爱和为女性存名的志向之外,还要求编者克服心理与社会的障碍。通过《卿本著者》对序言、选辑过程以及凡例的分析可见,女性编者总是反复声明文学活动只是履行家事妇职之后的兴趣,郑重地解释自己介于文学审美与伦理取向之间的辑录原则,承担并处理传统道德礼教带来的焦虑。当然,这些努力也为之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诗存志,留名于世
在长期占据官方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女性总是被置于社会与家庭等级中的从属地位。究竟是什么驱动明清女性自愿承担违背礼教的风险,执着于在文学实践中表达与构建自我?或许从《卿本著者》中许多女性对待传统思想的非寻常之态可以窥见答案的蛛丝马迹:甘立媃晚年积极参与儿子管辖地区的政治治理与社会交际,在当地树立了一定的名望;沈彩借由诗意暗讽“缠足”这种人为色情的丑陋:“无谓甚!竟屈玉弓长”;季娴批评男性编者的纰漏,直言儒家传统宣扬妇道无文,哀叹女性文人“不传者多矣”;邢慈静创作《追述黔途略》并不只是作为简单的日记,更是意在记载路程之艰与谨慎的辩白,以“俾后世子孙,知余之苦”。此外,不少女性引用《诗经》“言志抒情”的传统以证明女性也拥有表达自身情感与思想的自由。无论自传诗集、游记写作,抑或诗评注本,这些文字是如此鲜活,以诗存志、留名于世的渴望,是她们执着于创作与辑录最根本的动机。
然而,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形下,女性的“立言”与“立德”似乎无法并行,比如女性诗集的出版。作为一种公开展示的形式,出版与女性保守谦逊、妇道无文的传统教义相悖,因此她们通常要在序言中耗费相当篇幅为此作解释。也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明清之际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焚书现象,许多保存下来的女性手稿或选集标题中都带有“焚余”等字眼。《卿本著者》中有两个相关事例:为胡佩兰作传的男性文人吴钧认为这种命名其实是“羞其诗之少”而编造的借口;而王凤娴托稿于弟弟时,哀叹道“妇道无文,我且付之祖龙”,献吉曰:“不然。”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读:“王凤娴之言是应作字面意义直解,还是当作转义修辞解读?”诸如王凤娴的众多才媛们,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记录与表述,她们真的愿意烧掉自己的创作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企图获得亲友同情的计谋?或者,如吴钧所言,真相另有隐情?其中值得推敲的地方尚多,耐人寻味。
在变幻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境遇中,实现文学理想、留下作品的女性只是少数,有些甚至在男性同伴的支持下才得以保存。但正如《卿本著者》所言:“她”的主动是“他”行动的原动力(her initiative is the impetus for his action)。女性热爱创作而笔耕不辍,不辞辛劳地选辑,竭力保存更多的诗歌,这些举动无疑具有强烈的才名意识。明清女性沉迷于文学的魔力,超越了单纯审美愉悦的情感,本质来源于她们在接受传统思想中所形成的共识:立言以不朽。
“明清妇女著作”网站(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php)
白璧微瑕
是书篇幅不大,仅有四章,但征引资料极为丰富,并有作者较多的前期研究成果和主持创建的“明清妇女著作”网站为基础,所论极有见地,引人入胜。故不避繁复,详论其优长如上。由于论述涉及面较广且作者长期处于英文写作环境,书中也偶有未当之处。如第53到54页,论甘立媃的庐山诗对苏轼名篇的呼应后说,“苏轼曾于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1080-1085)造访庐山”,显然失察。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起复,量移汝州,由江淮徂洛,道经庐山,盘桓数日,作《题西林壁》。苏轼在黄州安置时,实为受监视居住,不可能离开黄州去造访庐山。又如,第三十页论甘立媃三言体《述怀诗》时称“三言诗体应是对童蒙读本《三字经》的模仿”,恐亦未当。按,赵翼《陔馀丛考·三言诗》:“三言诗,《金玉诗话》谓起于高贵乡公。然汉《安世房中歌》‘丰草葽’及‘雷震震’二章,《郊祀歌》之‘练时日’‘太乙贶’‘天马徕’等章,已创其体,则不始于魏末矣。刘勰又引《喜起歌》为三言之首,而谓诗之有三、五言,多成于西汉,盖《国风》:‘山有榛’‘隰有苓’,《周颂》:‘绥万邦’‘屡丰年’之类。古诗中原有此句法,特汉初以之为全篇,遂成此三言之一体耳。”可见,汉魏时已有三言体诗,且汉赋中亦有大量相连的三字句,经鲍照以至宋人接续创作,三言体诗所在多有。书中称甘立媃所作是对《三字经》的模仿,实未允当。
此书的两位译者为更好地呈现该书的价值,在翻译过程中核查了书中论及的中文文献,并不时以“译者注”的方式来纠正原书中的小失误或补充介绍有关资料,这对原作者来说实为幸事。但百密一疏,译者也偶有未能顾及之处。如第38页脚注二称:“明清妇女著作”网站收录十九首语带“归宁”的诗作,这实是方教授当年撰文时的数据,今检该网站,可得六十二条记录;第147页脚注一“《竹笑轩诗稿》”应为“《竹笑轩诗钞》”,为浙江图书馆藏钞本,应加译者注改正说明,以与第108页的译者注相呼应。由于译者已有多部译著出版,此书的文字总体来说雅洁可读,偶有误字,特为拈出,可在将来再印时纠正。如第11页第十一行“吟雪楼稿”应为“咏雪楼稿”;第169页第十三行“鼎格”应为“鼎革”。此皆白璧微瑕,无伤大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