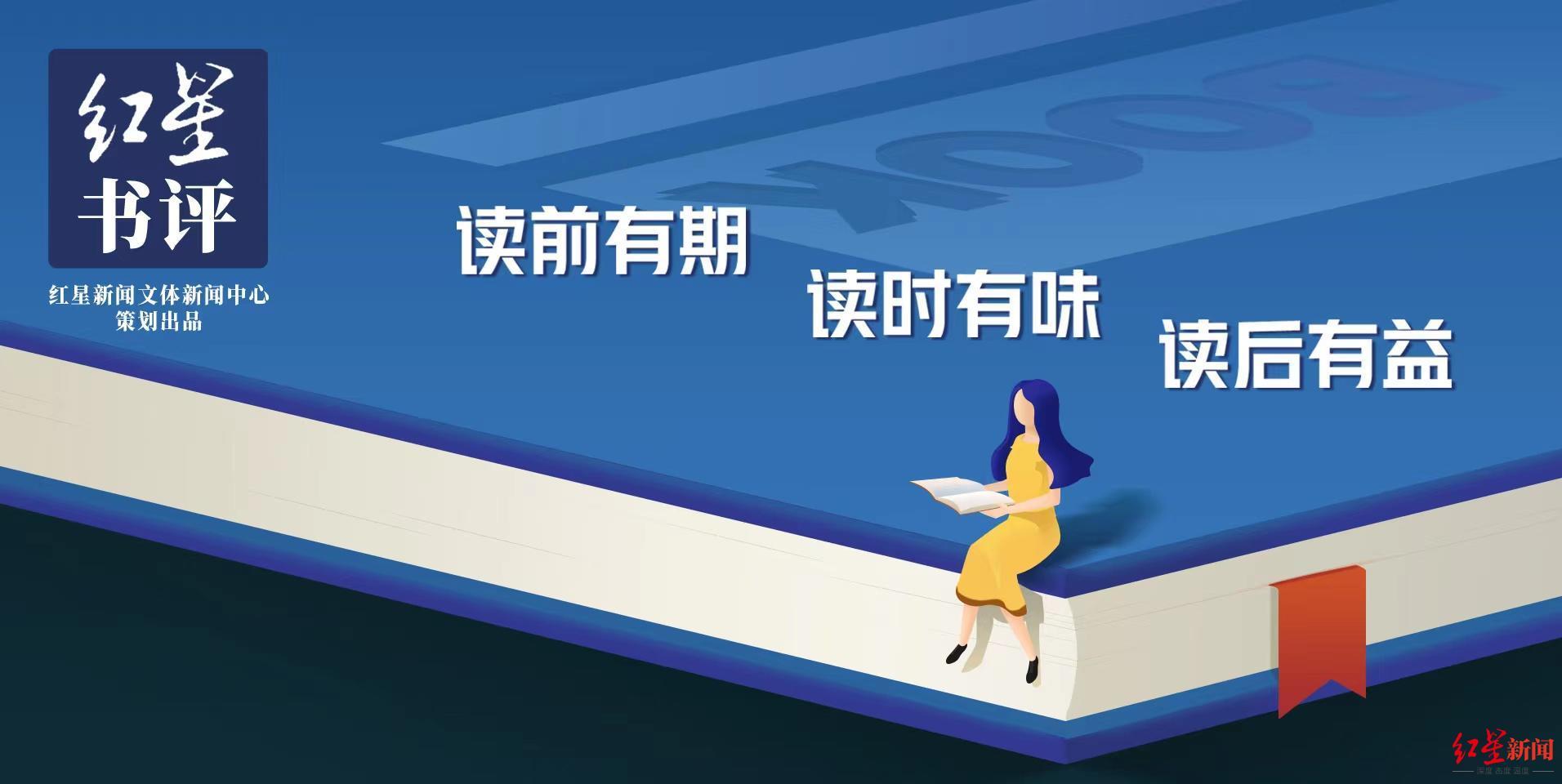
甲子必不悔,六十始不惑
读陈小平诗集《甲子不悔》
谭光辉
陈小平诗集《甲子不悔》即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甲子就是六十岁。孔子云,六十而耳顺。进入耳顺之年,好话坏话都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也能采纳,相当于可以给人生做总结了。郑玄注云:“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意思是说,进入耳顺之年,别人说的话,不论是言内之意,还是话外之音,都听得懂了,人生步入大智时代。无论是听得进意见也罢,还是听得懂话也罢,人一旦到了六十,定然进入一个新阶段。到了六十而“不悔”,说明前半生过得惬意,后半生还要继续。世间各种评说,既听得懂,也听得进,但我仍然是我,百年亦如一日。
陈小平的前半生,主题鲜明:诗、烟、茶、酒、朋友、女人、小儿子、大自然。惟此八君,他才愿付出真情。除此之外的生活看似快意,却难遣内心的孤寂。孤寂的缝隙,正是诗心涌出之机。真情附托的对象,化为诗歌的主题。
小平笔下的大自然,因取譬远而显得魔幻。他对自然之物,有一种从梦中进行观察的角度,彰显出“人生如梦”的世界观。“二月的枝头,发出瘆人的狞笑”(《二月纪事》),“芦苇是冬天的人质”(《初春》),“种子在聆听来自不同春天的陌生”(《三月》),“女贞子神态自若/在光天化日之下与路人调情”(《四月印象》),“我看见一条鱼游向树梢”(《七月》),“风在楼道的拐角处不停地撕咬”(《大雪》)……这些意象的奇妙连接,比拟手法无节制的使用,勾画出诗人活跃的思维路线图和骚动不安的灵魂。因为诗人对现实生活有失落感和不满足感,所以他想在诗歌的世界中去寻找别样的幸福,为此不辞艰辛。“寻找幸福的人翻山越岭”(《小溪》),正是他在诗歌世界中孤独寻找的影子。
小平笔下的小儿子,是他生命中的浪花,幸福的寄托。“在初霁的早晨听见儿子朗诵/是七月最美好的时光”(《七月》);“一天中最幸福和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接上小学的幺儿回家”(《日记》)。他愿意为小儿子花费大把的时间,“我要返儿子的房间/整天陪着他,排练他”(《稚子说》);小儿子也给他带来思考与启发,“在我与儿子近在咫尺的/过去和未来里/某样东西正在被涂抹”(《醒来》)。五十岁后喜得儿子,儿子便成了他生命甜蜜的延续,温柔的再生,让他能够继续呆在童年中与儿子一起做梦,一起幼稚。
小平笔下的朋友,亦如他生活中的朋友。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朋友是十分珍惜的、慷慨的、重视的。他希望每一个朋友都是一首诗,一段记忆,一个生命部件。他对朋友,是敞亮的、率性的、真诚的。“多年前我与朋友一起喝酒,猜拳/谈论女人。他们散去,没有留下地址”(《三月》)。年轻时候的朋友,一个一个逐渐老去,在回味友情的时候,仍会有所收获:“像黄牛徘徊在残雪与小草之间/看似波澜不惊,却在反刍岁月与真理”。朋友带来的感情是多元而复杂的,重要的不是年轻时的快意,而是年老后的回忆。李商隐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说的是五十岁时的感觉,陈小平谈的是六十岁时的体悟,二者不谋而合,道出了沧桑的感觉、人生的哲理。诗人相信朋友们的真诚和持久,人生道路再长,他们也无处不在:“动车蜿延而行/让我看见了飞速掠过的岁月/我的朋友,他们在道旁/耐心地等待我的到达”(《旅途》)。
诗是陈小平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幸而“一树白花带回了春天/诗歌的流亡终止”(《初春》),诗歌不再流亡,诗人因而得救。虽然诗人号称“我是一个尊重孤独的人”(《七月》),但是他实际上更害怕孤独。尊重孤独,是因为没有孤独就写不出诗句。为了寻找孤独,诗人可以通宵不眠:“一位诗人为大雪节气写诗/通宵不眠/丢弃了一地纸屑”(《大雪》)。为了寻找孤独,诗人喜欢独自坐在江边,或者独倚窗前:“时值中年,我仍然喜欢独坐礁石,眺望未来”(《这个下午》);“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独倚窗前”(《看云》)。为了寻找孤独,诗人瞄向了远方:“迎面而来的群山,阻挡过我的视线/它们无法如盆地一样/囚禁我的孤独”(《旅途》)。虽如此说,诗人实际上是害怕孤独的。“我并不害怕孤独地度过余生/我只担心爱情会让我感到孤独”(《说爱的时候》),这个矛盾的说法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前一句是表面的说道,后一句才是真实的想法,“孤独”并不可怕,“感到孤独”才可怕。诗人喜欢外在的孤独,害怕内心的孤独。寻找表面的、外在的孤独是为了写诗,而若内心真感到孤独则很要命。诗人摆脱孤独的办法是写诗,于是诗人陷入了永恒的悖论:为了不孤独而去寻找孤独。为了逃避内心的孤独而写诗,要写诗就要主动去寻找孤独,诗歌成为诗人“孤独”的中介,挥之不去的魔障,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上述诸点,是陈小平在《甲子不悔》这本诗集里着重表达的几个主题,对应了他在俗世生活中最看重的几个元素。但是,诗人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毕竟步入甲子,早已经历了“而立”“不惑”“知天命”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对生命必然有更深刻的观察和理解。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明白存在的意义”感到了“自我的无奈”和“人类、地球的渺小,思想的苍白”,他发现任何的限定、对本源的追问、语言的表达,都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意义的一切行动都是没有意义/定义生命便是自掘坟墓放弃尊严”(《存在与时间》)。从这个角度看,陈小平确实在甲子之年步入了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洞悉了人之为人的某种虚构性和虚无性。
有了这个意识之后,诗人进一步意识到,“我不能变得更加虚无了”,他希望“回到梦一样清澈明亮的天空”(《如果》),去重新寻找更多的意义和价值。他设想可以回到某种本真的状态,用生命和感觉去重新体验和建构这个世界:“我不再思考世界,只用吻品尝”(《摹仿》)。在诗人看来,语言构筑的世界也不真实:“我们从不听从语言的召唤/尽管它构筑了世界……/我们却不知道它的意义”,不如重新回到自然的状态之中去:“我们幻想草成为草,石成为石”(《悖论》)。诗人有此意识,是明确地感觉到了生活与生命中的某种荒诞,希望生活在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本己本真的状态之中,构建一个“诗意地栖居”之处所。然而,陈小平永远也不能确定如何才能找到和成为那个真实的自己。这个问题解决,或许只能求助于某种信仰,然而信仰也给不了我们答案,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问题。“我们可以选择,却无法逃避/我们向神山訇伏跪行时留下的疤痂/一挑明,便流血”(《观景》)。这是诗集的总结,也是诗人的无奈。
有了辩证性的思维之后,诗人看到了许多包裹在表面现象下更深刻的真实,他发现了“甜言蜜语的陷阱”,请求“不要以仁爱施暴”(《法则》)。他不要“廉价的奉迎和颂赞”,觉察到“礼貌和施舍”是“君临天下的压迫”,“温柔和霸气更像暴力”(《距离》)。他发现,“爱”这个“唯一崇高而圣洁的语词”可以“将我们深刻地刺伤”(《对立》),“忠于内心的结局”是“时光将一寸一寸地湮灭我们的骨骼”(《留言》)。诗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的欺骗、荒诞、虚无,告诫人们“也要相信宿命”,“现实如此残酷,像未曾晤面的前世”(《忠告》)。原来,“我们收集起词典里的所有誓言/戴上对方的头顶,现存它们已经破碎”,“模糊的景象总是被眼睛擦伤”,“我想将我的爱/留在那里,留在那些远逝的时光里”(《看见》)。到这里,问题似乎已经明晰。撕破知觉的表象,回到感觉的真实,抗拒实在的痛苦,走向沉默的反抗,我们看到了一个乐观豁达的诗人心灵深处那些不愿被轻易揭开的脆弱疤痕。
有了这一系列的认识,诗人开始深深地忏悔。他希望所有的故事“以开始的方式开始”“以结束的方式结束”(《模式》)。他希望重新返回自由的状态,渴望着命运重新安排,“除了自由,有什么可以自持?/又有什么不能放下?”(《酷暑》)为了自由,什么都可以放弃,甚至是生命。“我已学会与死神握手言和”“我不介意死亡”(《放弃》),“我们和空寂已达成和解”(《立秋》)。痛苦的诗人之痛已经达到了极致,“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许你听不到我的痛和忏悔/我却可以自在地站上每一棵树/如一只鸟在众鸟之上歌唱”(《歌唱》)。诗人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一粒稻粟诱捕的山雀,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发现“有时真相包藏祸心”,所以不靠近真相可能更好。发现这个真相之后,诗人觉得自己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以至忘掉了压力并喜悦地抽泣”(《山雀》)。
诗人似乎是在向我们讲述一段苦闷的经历,一个难以言表的痛楚,一瞬刻骨铭心的觉悟。他梦想着另外一次“偶然”,遇见一个能将自己“幻化成一只蝴蝶”的她,一个让“好时光就会翩然而来”的对面女孩(《天使》)。希望归希望,诗人总得回归现实,给自己的一生做总结,继续今后的生活。即使“我已数年生活在背弃与谎言之中”,但对世事仍然看得非常清楚。虽然“我也没有因为眼疾而视线模糊”,但还是要“学习对着月亮和星星歌唱/纯粹的欢乐和纯粹的苦痛”(《生日》)。这是因为,不论是欢乐还是痛苦,都是人生宝贵的经历,是命运的赐予,是母亲的馈赠。在母亲伟大的爱里面,诗人学会了宽恕、仁慈、谅解,“如你的善良一般的光辉/使我在仁慈和宽恕中,学习/直立行走,又在嘲讽和轻蔑中/感知到万物的结局”(《给母亲的信》)。如母亲在天国宽恕了再婚的父亲一样,诗人也觉得,世间其实没有什么不可宽恕的了。
所以,《甲子不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主题是宽恕。“释放”了,也就“释然”了。释然之后,可以把自己放置于高处和远处,把曾经的经历当作景观进行欣赏。虽然伤疤仍在,但要学会忏悔、珍惜、治愈。《观景》作为诗集的总结,深刻地表达了这一主题:“我们学会在日益遥远的地方宽恕”“现在珍惜从前的一切”。这大概就是一种比较彻底的超脱,一种与过去达成的谅解。过去那些“沿途的创伤”,要“小心翼翼地捡拾”起来,在一种虔诚的信仰中或许可以得到超度。他觉得,这些创伤,或许是宿命的安排,虽然看起来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而实际上是无法逃避的。在寻求忏悔、宽恕的过程中,又会留下新的疤痂,永无止境。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便会明白人生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一挑明,便流血”的事实。有了这个认识,人生的本质意义也就认识清楚了,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宽恕的了。到了甲子耳顺之年,回头观看自己的人生景观,还有什么可“悔”之事呢?
作者简介:谭光辉,男,四川南充人,1974年12月出生,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学、叙事学、情感。
编辑|段雪莹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