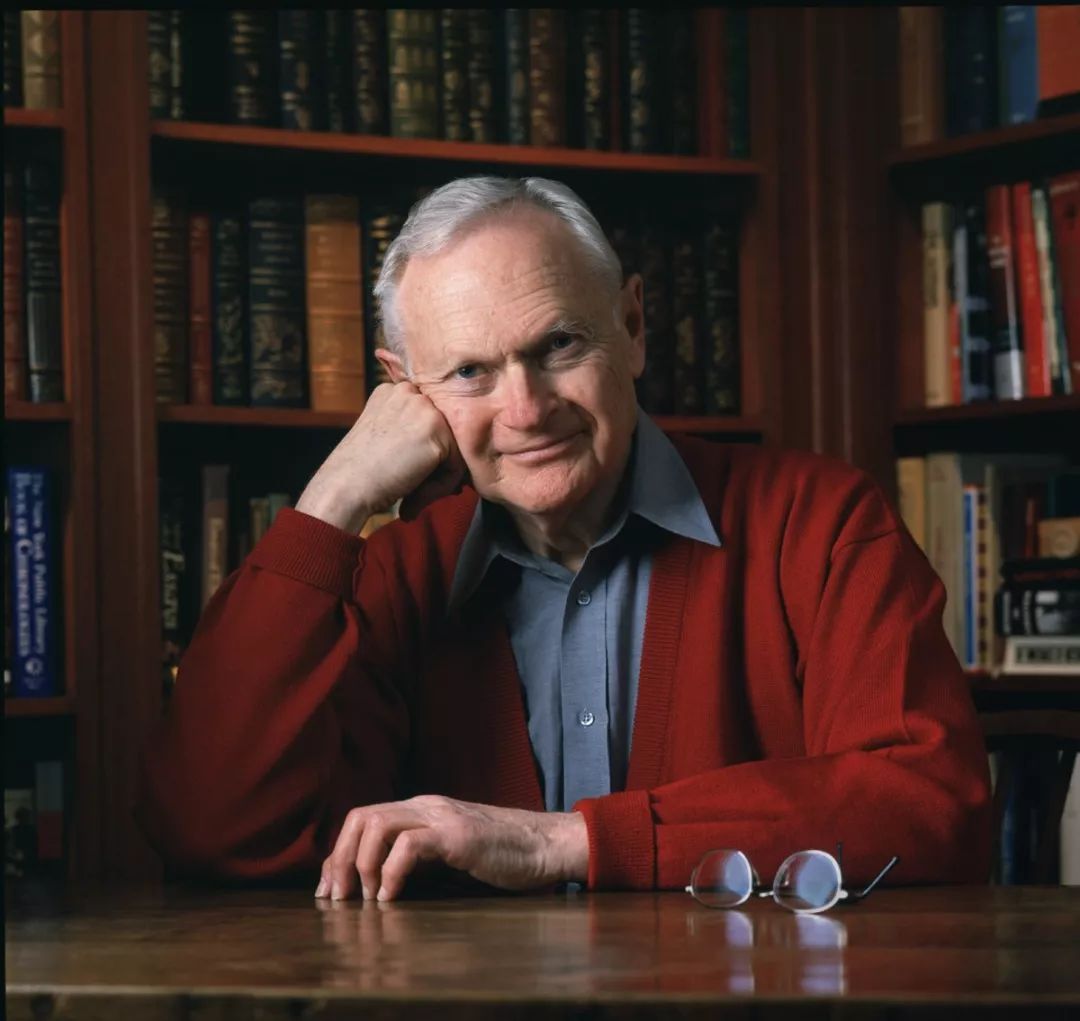当身体机器过了保修期……
死亡的向导
我关心微观世界甚于宏观世界;我对于一个男人如何活着的问题, 比一颗星球的毁灭要有兴趣得多;一个女人如何在世上生存,也比一颗彗星如何划过天空更能引起我的关注。如果有神灵存在的话,它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显现。我所沉迷的神秘是人的情境,而非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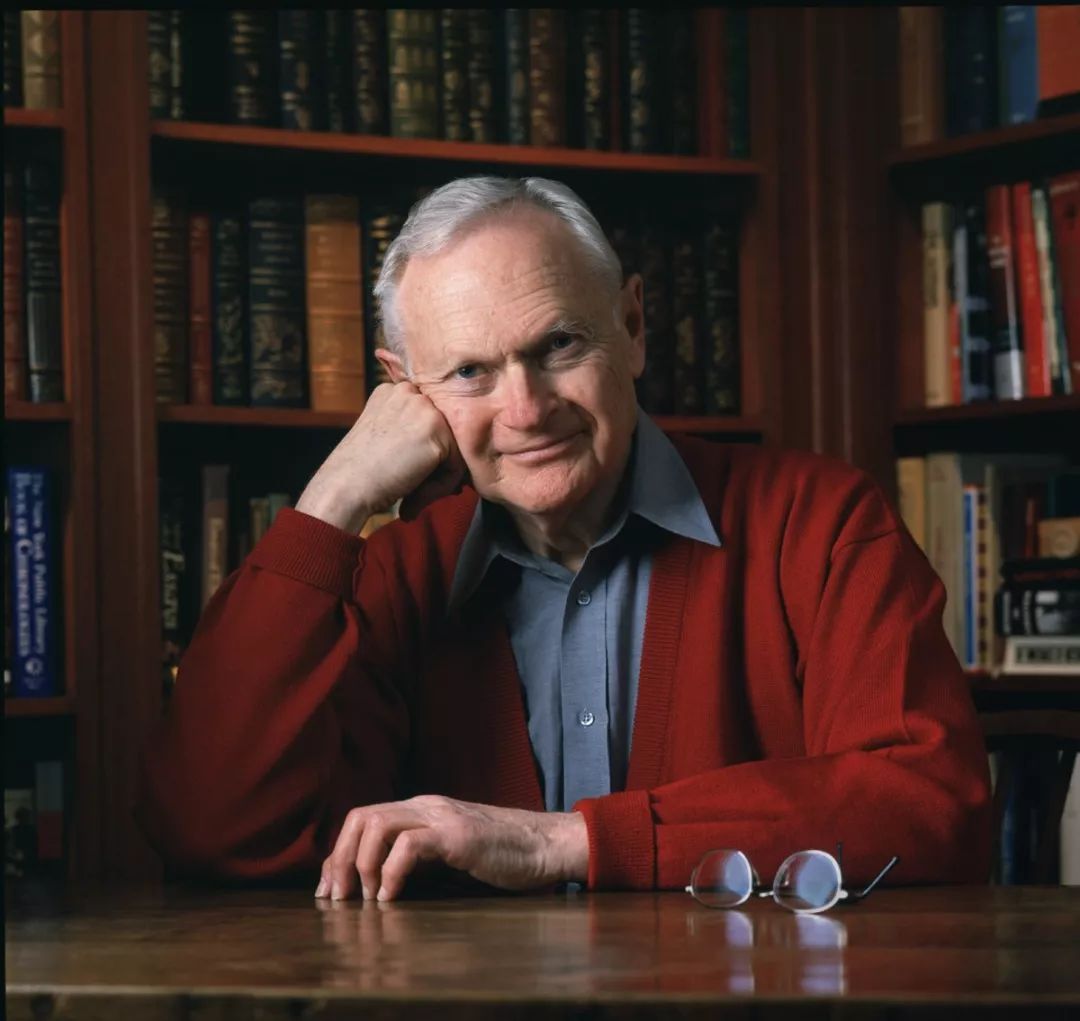
舍温·努兰
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
集毕生行医生涯的智慧,
用故事揭开死亡的神秘面纱,
临床抉择与经验累积。
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普利策奖。
了解人类情境成为我终生的志向。在我已迈入第七个10 年的生命中, 我有我的一份伤感,也有一份我的胜利。有时我觉得我应该有比这两者更多的东西,但这样的观念可能源于我们共同的倾向。也就是觉得我们自己的存在是共同经验的缩影— 一种比一般生命更广阔、感触更深的生命。
没有任何方法可预知这是否是我生命的最后一个10 年,或者还有更多的日子—健康良好并不能保证任何事。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也有我们共有的信念:我希望无痛苦地走。有许多人希望迅速地死亡,甚至是猝死;也有人希望死于为时短暂而没有痛苦的疾病,周围围绕着他所爱的人。我是后者,而且我推测大多数人都是后者。
很不幸地,我所希望的,并不是我所预见的。我看过太多死亡,所以无法忽略那压倒性的可能性,就是结果不如我所愿。像大部分人一样,我可能会罹患许多致命的疾病,遭受身体与情绪上的痛苦,而且我也会像大部分人一样,在最后几个月由于优柔寡断而更添痛苦—继续治疗或放弃;积极处理或是逆来顺受;争取更多时间,或是过一天是一天—当我们痛苦地面临那有能力杀害我们的疾病时,这是一面镜子的两面。我们选择在最后时日照出自己的哪一面,应当是心有定见的平静景象,但也未必如此。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我自己,同样也为了读它的人们。借由收集一些穿越过我们视界的死亡军队,我希望忆起我所见过的事,使每个人都熟悉它们。我们并不需要去观察全部的杀手,我们没有兴趣看遍每一个死亡骑兵。但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与你在这里读到的,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如果我们比较熟悉它们,或许这个骑士就不会那样令人害怕,而且或许那些必须做的决定,就比较不会在一知半解、焦虑,以及不正确的期盼下进行。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可能都有一种正确的死亡方法,而我们必须努力去发扬它,同时接受它可能不在我们的掌握中这个事实。大自然施予我们的最后疾病,将决定我们离世的环境,但只要可能的话, 我们应有选择离世方法的权利。里尔克写道:
喔,主啊!赐给我们每个人属于他自己的死亡。
死亡,引他离开人世,
在其间,他有爱、意义,与绝望。
这位诗人像祈祷者般讲述着,但像所有的祈祷者一样,即使上帝也不一定应答。对我们之中太多的人而言,死亡的方式无法被控制,而且也没有智慧或知识能改变它。在我们所爱的人,或是我们本身即将死亡时,值得了解即使在现代生物科学最精细、最善意的帮助之下,很多环境仍不允许人们做出选择。死得很惨的人并不是报应,而只是他们的杀手本性如此。
大部分人并非以他们选择的方式离世。在前几个世纪,人们相信“死亡的艺术”这样的概念。在那个时代,接触死亡的唯一态度,就是让它发生— 一旦有死亡的征兆出现,没有别的选择,死亡是最好的途径,何不在平静中安息。但即使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在死前仍会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顺从以及祈祷者与家属的安慰,会使最后的时光好过一些。
我们的时代没有死亡的艺术,只有救人性命的艺术,以及这门艺术的诸多两难困境。在半个世纪之前,另外一个伟大的艺术—医学的艺术,仍因其有能力处理死亡的过程而感到骄傲。但现在除了极少数的设施之外,医学艺术的这个部分几乎已完全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拯救成功时的显赫荣光,以及极常见的、不能救时的遗弃。
死亡属于垂死者和那些爱他的人们,虽然它可能被疾病的入侵蹂躏所玷辱,但不应允许被一些无益的善意作为进一步扰乱。治疗是否继续进行,会受到主张治疗的医生的影响。通常,训练最精良的专科医生, 也是最坚信生物医学有能力克服疾病挑战的忠实信徒。家人会把统计资料当成最后一线生机,但这看似客观的临床事实,常常反映出一种哲学, 即把死亡视为无情的敌人。对这样的哲学信徒而言,即使是暂时性的胜利,也值得荒废垂死者曾经耕耘的土地。
我说这些,并非责难那些高科技的医生。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而且我也分享过背水一战的激情,以及胜利时的高度满足。但在我的胜利中,有许多是付出了极高代价的。有时,这种胜利并不值得经受那样的痛苦,我也相信如果将我置于病人与家属的地位,我未必认为这样不顾一切的挣扎是值得尝试的。
当我罹患需要高度专精技术治疗的重症时,我将会寻找该部门的专家来诊治。但我不会期待他能了解我的价值观、我对我自己及所爱之人的期盼、我的精神层面,以及我对生命的哲学观。这不是他受训练的项目,不是他专精的部分,也不是促成他追求卓越的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我将不会让一个专科医生决定我该在何时撒手。我要选择我自己的方式,或至少把我的原则说清楚,万一我无法自己决定时,可由最了解我的人来决定。我疾病的状况可能无法允许我“好好地死亡”,或是我们寻找的那种有尊严的死亡;但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 我不会比我应该死的时候还晚离世,而这只是因为一个无意义的理由: 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高科技医生,并不知道我是谁。
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隐藏着对家庭医生制度复兴的祈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向导,他了解我们的程度,就像他知道我们该如何探触死亡一样。同样的疾病,有许多不同的路通往死亡,有许多抉择要做, 有许多站我们可选择休息、继续或是完全停止这个旅程—直到这旅程的最后几步,我们需要有所爱的人相伴,而且也需要有智慧来选择自己的路。影响我们决定的临床事实,必须来自一个熟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以往生活的医生,而非来自一个拥有专精生物医学技术的陌生人。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长期了解我们的医生朋友。讨论以何种方式改革我们的医疗体系时,只有认同上述事实,才能做出良好的决策。
而且,即使有最敏感、体恤的医生,真正的控制仍需要自己对疾病及死亡的了解。正如我看过太多人挣扎得太久,我也看过不少人太早放弃。而那时还有许多可做的,不只是保存生命,还可保存生命的乐趣。我们越了解致命疾病的相关知识,就越知道如何选择停止或继续奋斗的时间,而那些我们不愿见到的过迟或过早的死亡就会越少发生。对那些死者与爱他们的人而言,最实际的期盼乃是安静的离世之途。当一切结束时,让我们难过的应是丧失了所爱之人,而不是做了错误决定的罪恶感。
实际的期盼,也需要我们接受以下观念:一个人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必须被限制,才能让我们的种族持续生存下去。人类即使有上苍许多独特的厚爱,也只是像其他动植物一样,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大自然不会去分辨。我们死亡,世界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我辈能享受生命的奥秘,是因为数以兆计的生物,为我们准备了生存之路,并且死去—为我们死去。我们死了,别人才能活下去。单一个体的悲剧,变成大自然事物的平衡,以及生命绵延的胜利。
上述这些,使得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每个小时都益显珍贵;生命必须是有用而且知回馈的。如果借由我们的工作与娱乐、胜利与失败,对于我们每个人,不只是人类,而且对整个大自然的生存进化过程都有贡献, 那么我们在大自然所分配给的时间内建立的尊严,就会借由接受死亡的利他主义而长存。
那么,平静的死亡景象与平静的过世,又有多重要呢?对我们大部分的人而言,这是希望的象征,是必须奋斗的理想;但这或许可能接近, 也还是无法达到,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之外。
其余的人则必须满足于即将被赐予的死亡。经由对于常见疾病致命过程的了解,借由符合实际期盼的智慧,借由重新认识医生的限制而不向他们要求他们无法给予的,死亡应该能在致命疾病的允许之下,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
虽然死前的几小时通常是很平静的,而且多半先前有一段人事不知的时光,但这种平静通常需要付出可怕的代价—我们抵达死亡的过程。有人设法在过程中找到高贵的时刻,在此时他们能胜过那加诸其身的侮辱。但这样的间歇,并未减少他们短暂胜利之间的痛苦。生命本来就散布着痛苦时刻,有些人的生命里还是痛苦居多;但在人生过程中,痛苦的阶段会被平安的时刻与喜乐的时光所抚平。然而,在死亡的过程中却只有痛苦。短暂的休息与减弱总会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复发的折磨。平静与喜乐在解脱时才会来临。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死亡之际常有平静, 偶尔也有尊严,但死亡的过程却鲜有这些。
因此,如果传统的“有尊严的死亡”概念必须被修正,甚至抛弃的话,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冀求的离世的最后回忆之中,哪些希望该被留下?我们在死亡中企求的尊严,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求。死亡的艺术,就是生的艺术。活着时的诚实与仁慈,是我们如何死亡的真正方法。并非在生命的最后几周或几天,我们传达的信息就是以后将被回忆的,后人回忆的将是我们过去所活的几十年。活得有尊严的人,死得也有尊严。19 世纪美国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在给他的诗作《死亡随想》(Thanatopsis) 加上最后一段时,只有27 岁,但他已了解死亡,就像许多诗人一样:
所以活着的人,
当你被招募加入熙攘接踵的旅队,
移往神秘的国度,
在死亡安静的大厅中,
人人领取自己的房间;
勿像夜间采石场的奴隶一样不愿前行,
而应以不变的信念,坚毅而宽心地迈向坟墓。
放下卧榻的帷帘,
躺下来,做个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