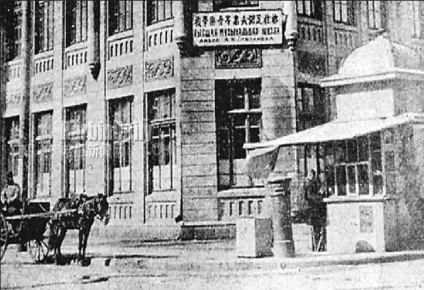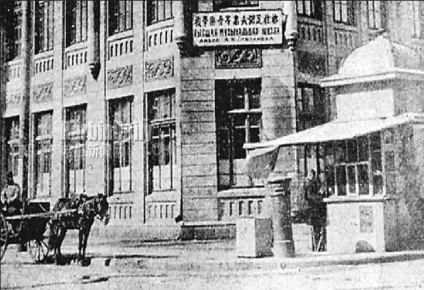
□冯前明
哈尔滨的百年老街中央大街,早年叫哈尔滨中国大街,1923年,欧式建筑参差耸立的哈尔滨中国大街上,一位英国绅士徜徉其间,目光定格在街角一栋出售香烟的小木屋上,这让他脑海里灵光一闪。1924年,吉黑邮务管理局设计制作了六角形小木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邮亭”,坐落在当时哈尔滨的5处繁华之地,分别是哈市道里区中国大街、南岗区果戈里大街、道里区地段街、哈尔滨火车站广场、南岗区大直街铁路俱乐部前。据老哈尔滨人回忆,“这种邮亭出售邮票、信封,并备有糨糊。邮亭旁边设有邮筒,寄信时贴上邮票、封上口,再投进邮筒就行了,很方便。”简单、实用、美观,这种邮亭迅速推广于全国,并传向世界。
这位英国绅士就是时任吉黑邮务管理局邮务长(局长)李齐。1921年李齐从上海调到哈尔滨,他在任内做的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主持接收了俄国在中东沿线开办的邮局。据他回忆,当时居留在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人大约有20万,其中,仅在哈尔滨一地居留的就有10万人。吉黑邮务管理局接收俄国“客邮”后,中华邮政同仁“恶补”俄文,很快能用俄文应对俄国用户,而且把中华邮政章程、邮资表、邮便签等全部都翻译成俄文。“不到三年,吉黑邮区变成仅次于上海,最繁荣、最赚钱的邮区。”
“客邮”是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擅自在中国开办的邮政机构。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美、日、德等国明目张胆地在我国领土上设立了自己的邮局。这些外国邮局实行本国邮政章程、粘贴本国邮票、盖印中国地名的外文邮戳,他们不仅收寄中国到外国的信件,也收寄中国国内互寄的邮件。这些“客邮”中领头的是英国,数量最多的是日本。日本当时在我国设置邮局59处、附属局所12处、代办所32处,野战邮局7处。日本设立这些邮政机构,既无条约根据,又未经中国承认,系侵犯中国邮政通信权的行为,屡遭中国方面反对。日本“客邮”不得不在1922年底前全部撤销。
据资料记载,1918年9月7日,日本人在日侨聚居的哈尔滨市道里区石头道街和南岗区新市街公然开设两家邮局。此外还在哈尔滨和满洲里两处设立了野战邮局。民国时期著名文化人、当年曾在吉黑邮务管理局工作过的陈纪莹回忆:上世纪20年代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的大街上,离中国绿色邮筒不远处,就有一个红色邮筒,上边写着“日本邮便”。他在邮局里看见天天有一个日本人到挂号房来交信,心想日本既然有邮局,为什么还把信件交给我们代寄?经他探明,才知道有好多寄中国各地的信件,虽然被日本邮局收下了,仍须交给中国的邮局代为转寄。
黑龙江邮政博物馆内悬挂着两帧外国人的照片,其中一位就是英国人李齐,还有一位是意大利人巴立地。这两位洋人先后担任过吉黑邮务管理局邮务长,他们也都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据《中国邮政简史》记载,在“九一八”大劫难后,主持东北邮务的巴立地,于1932年1月29日函告中华邮政总局,叙述日伪企图劫夺邮政的阴谋,并提出应变的建议。巴立地经总局授权办理撤退后,拟定了撤退计划。凡是可以移动的财产、邮票、档案、公物,尤其是邮政储金,都通过外国银行和外国领事馆,不声不响地运往关内。日本关东军逼迫中华邮政承认伪满,巴立地予以拒绝。
与此同时,在东北工作的3000名邮政员工深明大义,誓死不当亡国奴,响应“撤邮”号召,踊跃返回关内,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日军代表曾哀叹:“要是中国官吏都像邮局一样,我们将不能在此地立足了。”1944年,巴立地不幸陷于日寇的魔掌,被关押到山东潍坊日军集中营,经受了野蛮的暴行。
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近代中国受到世界上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帝国主义为如何“瓜分”中国而绞尽脑汁。旧邮政如同其他民族企业一样,始终是艰难地成长着,处于受制于外人和不发达的状态。但在中国广大人民中蕴藏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强大力量。巴立地等外籍员工为人类正义事业而奔走,在中国邮政的历史天平上留下分量。
世界上最早的“邮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