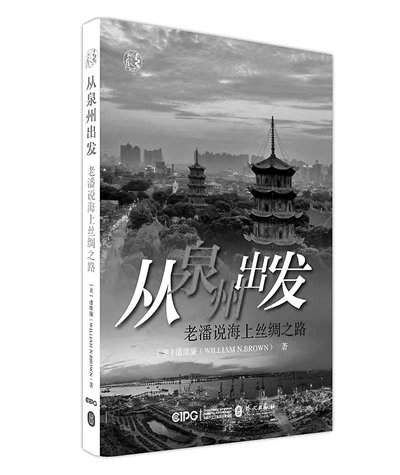
◎杨早(作家)
本来以为《从泉州出发——老潘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本纯歌颂泉州的洋人著作。没想到书里充满了这位将泉州称为“第三故乡”的美国学者的解构(俗称“吐槽”)。比如路牌上写着600米到少林寺,老潘自己一量是1.1公里,问方丈,方丈说和尚会功夫,飞过去就是600米;泉州人说“九日山无石不刻字”,老潘点头说“就像美国地铁涂鸦”;泉州人说“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能推动风动石”,他就想“我就是心灵纯洁的人”,结果推了半天,那块石头一动不动……
虽然是玩笑,但有趣里有一个道理:在词与物之间,本土与外地之间,玩笑与真实之间,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翻译。尤其泉州是一个如此复杂而多面的城市,而越是复杂与多面的事物,我们就越需要“翻译”。
很多外地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听泉州的朋友介绍泉州时,总有一种山阴道中应接不暇的感觉。光是世遗景点就有22处,其中随便哪个景点,开元寺,洛阳桥,清源山……都足以让一座城市辉映一时,这还只是“中西杂糅,华洋杂处”的“宋元泉州”,还有明清泉州的铺境制度,妈祖崇拜的民俗传承,晚明李贽的童心立说,弘一法师的重兴律宗,南音,木偶、德化瓷、安溪茶……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去吃牛肉锅和菜头酸,舌头总是最真切最直接的带路人。
很多人以为,只有文字和语言才需要翻译,就像拘罗那陀大师在延福寺译佛经那样。但其实,文化更需要翻译。像泉州这样的“多面文化体”,尤其需要不同的专家通人,进行各种层面的翻译。哪怕是吐槽与调侃,也是一种翻译——它们其实是站在基于说者自身世界里的常识常情常态之上,对“差异”的凸显与传扬。对泉州诸如“宗教博物馆”“诸神办事处”等等或庄或谐的归纳,就是不同样式的译名。“中西杂糅,华洋杂处”是好多外地人初访泉州的最鲜明印象,但往深里想,中西如何“糅”,华洋怎样“处”,这就不是一般以家乡为自豪的泉州人能说清楚的了。
即如我上月应邀参加泉州丰泽区举办的“海丝·蟳埔”民俗文化节为例。活动分两大块,头一日的祭海仪式是宋元传留的官方仪规,也是让外来人士大开眼界,但又一头雾水。祭文诵读用闽南语,“这是传统”,但是不是可以配个字幕组呢?还有那道士的作法、各国的来宾、仪式的规程、歌舞的人物,想必都有切实的考证与复原,只是何所从来,意指何物,我也好想知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隔阻在我与内行之间的,不只是方言与风俗的差异,更在于古今之变,江海之别,官民之异,中西之交。从一些细节,是能够看穿泉州文化的一些根柢的。
第二天到蟳埔村参加“妈祖天香巡境”又自不同。那种繁华、喧腾、奔放的民间节庆似乎是无须翻译的。人们管自游,管自舞,管自笑。鞭炮与面线的气息盈满整个渔村。美丽的簪花围如野花开遍天空与原野,网红主播如云,摄影达人如雨。谁说中国没有自己的狂欢节?你来蟳埔村看看哪!欢乐与美丽是不需要翻译的,投入就完了。巡香的短暂性增加了它的魅力,很多人看到朋友圈,只能梦想着明年的入画。
但是我仍然不满足。之前我在菜市场,确实见到了满头簪花的蟳埔婆婆贩卖渔货,我很想知道,如果说从前每日家簪花上市场,是为了更吸引顾客,现在是否还是同样的功用?日常的簪花与节庆的簪花又有什么不同?那位坐在路边淡定地呷着面线的老婆婆,她怎么看这年复一年日益热闹的人神共娱?
巡香将近尾声,我们站在妈祖庙前,看一位老人往两边的红纸上,用金粉书写捐献的信众名色。这些捐献明显没有经过EXCEL的统计排序,只是顺着写下来,壹万也是一行,貮佰也是一行。神明,文物,日常生活,如此和融的交织。我又体味到了一点自己认为的“泉州”。
潘维廉在讲到安溪文庙时,又开始了他独特的调侃。有一泉州英文版地图将“文庙”印成了Confusion Temple——正确写法显然是Confucius(孔夫子),但老潘说“我又不能百分百确定那是打字错误”。这真是全书最妙的一个笑话。Confusion意为“混淆、混乱;不确定,困惑”,泉州的哪一处,又不是重重叠叠,杂糅混处,Confusion的呢?我不禁有点埋怨长居泉州十四载的弘一法师了:您明明有天津背景、上海背景、东京背景、杭州背景,又“二十文章惊海内”,何以不能为我们这些后人,翻译翻译这谜语一样迷乱、群峦一样层叠的泉州呢?
想必法师只会和煦地沉默,舍利塔旁的石刻遗言又新描了红,你看不见吗?“悲、欣、交、集。”2023.3.13
供图/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