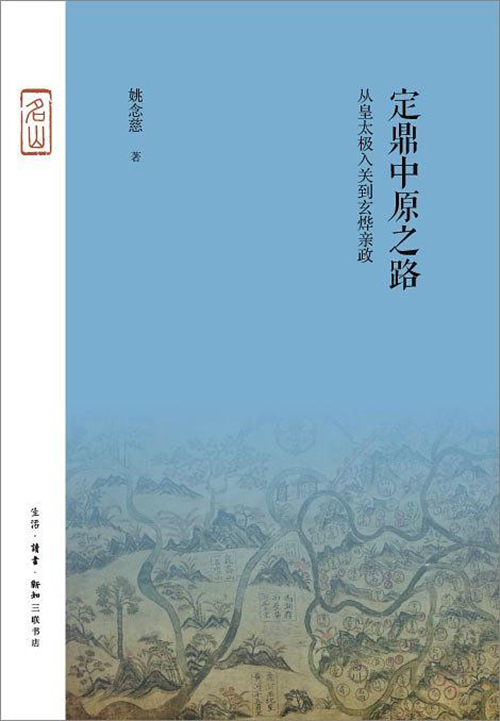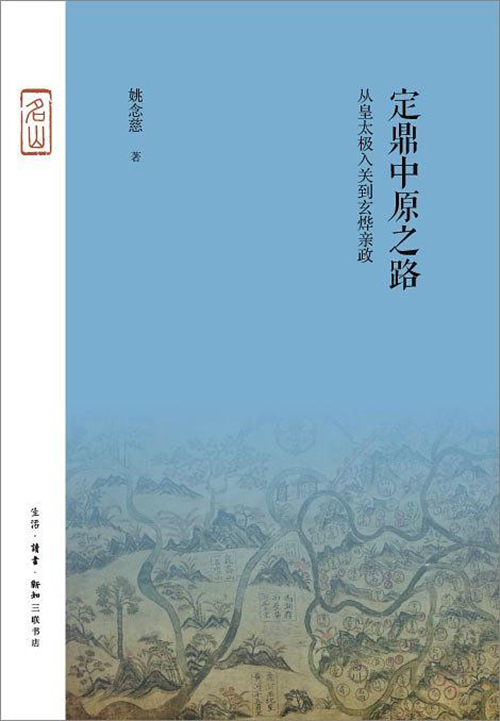
《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姚念慈著,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版,393页,75.00
2018年10月,姚念慈先生的新书《定鼎中原之路》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集结了姚先生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四篇文章,分别为研究明金己巳之役的《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研究多尔衮辅政时期的《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研究顺治时期国家政治的《评清世祖遗诏》以及讨论康熙初期四辅政大臣的《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师从王锺翰先生,在清史学界深耕数十载,在本书收录的四篇文章中,《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为姚先生新作,也是本书中最见功底的一篇。在清史新作如雨后春笋的今日,这样严谨的考证作品却较为少见。
“世事洞明”的政治史
区别于方兴未艾的社会史、医疗史、贸易史等专门史,政治史的叙事过程中除了依靠史料的连缀,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背景的了解和事态人心的分析。诚如作者所言:
然而政治史毕竟是人事的流变,政治形势无非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此消彼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无比,人的言行和心理动机也不尽一致,历史文献史料并不完全是真实客观的记录,往往夹杂着书写者的主观意见,皆须加以考订辩证。
个案本身的事实,极容易陷入海登·怀特式的历史迷思当中,即文字描述在多大程度上曲解了历史,而我们孜孜以求的所谓“事实”,到底是否存在?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特点就非常明显。事件本身是由多个叙述主体完成的,每个视角似乎都存在局限性,我们是否可以剥开记述主题的层层迷雾,接近事件本身,而这种接近行为的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
近些年广为热传的《历史学宣言》(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3月版)一书中论述道:“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反对微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将宏观和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融合,这才是关键。”如何通过关键性事件,窥见历史的大势所向,是作者所谓“实证史学”的第一要务。对此,作者认为:“政治史若仅从所谓大势着眼,回避个案,无视具体史实,历史叙事就很容易落空,变成概念和逻辑的演绎,政治制度演变的内涵无法得到显示,而且极有可能发生误解。这也实际上是研究乏力的表现。”
《历史学宣言》
己巳之变作为明清鼎革时期的关键性事件,对它来龙去脉的考证,既可以了解当时金、明的战略形势,也是对之后历史走向的一个预判。皇太极在自己皇权尚不稳定,亟需在统治集团内部建立威信的情况下,本欲东伐察哈尔蒙古,但在林丹汗远遁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南下伐明。皇太极与朵颜三部之前也并无盟约,苏布地在皇太极与明朝的两方逡巡之间并无明确行动,蓟镇空虚之下皇太极长驱直入。
在抵抗皇太极军队的城下之战当中,明朝政府廷议不定,既不能有效组织守军抵抗,又忌惮勤王军队的势力,甚至连粮饷发放都不能保障。在没有皇太极挑唆的情况下,崇祯将袁崇焕下狱,皇太极恐惧明军反扑断其后路,在京畿打劫之后一路北撤至山海关外。明援军渐集,皇太极之能脱身东奔永平,原因在于明崇祯逮系袁崇焕而导致关宁兵溃逃;金军攻山海关不克。
整个事件既不像清代官方史书中叙述的那样是皇太极一人运筹帷幄之功,也不像明朝方面表述的那样是浴血迎敌之战,相反,整个己巳之役是多个不确定的条件,在各自偶然性中的合成,并没有一部“上帝视角”的史书可以记录全部的“事实”,而对整个脉络的梳理基于作者对明清之际政治及各方势力的判断。
明臣集议之风与明朝对朵颜三部抚政的失败,导致皇太极可以直驱京畿;皇帝与封疆大吏的矛盾,导致袁崇焕一路迎敌而反遭牢狱,不独明代如此,而历代尽然;明末党争则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崇祯处死,而非乾隆皇帝为其先祖所加的“反间计”使然。这些线索串联出一个在当时政治情态下非常“合理”的历史事实,而这种事实的合理之处,则是考证整个历史的着眼点和归宿。
在《评清世祖遗诏》及《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两篇文章中,姚先生的论述中心之一,便是清早期的中枢政治制度。文章描述的顺治朝政治变革,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针对议政会议、内三院(内阁)的制度调整,以及世祖与汉大学士的关系。
议政会议,是后金以及清王朝建立之初长期存在的一种中枢决策机制。它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在君主主导下的廷议、会议制度并不相同,而是通过具有“议政”资格的宗室成员与八旗贵族担任的“议政大臣”共同商议国事,其决议具有很高的权威。十分明显,这种国家政治权力机关,与清朝皇权的构建存在巨大的矛盾。从崇德时期清朝统治者使用皇帝名号开始,清太宗皇太极就一直试图干预议政会议,影响其结果,削弱其权威。而到了清世祖亲政以后,随着清朝国家构建逐渐完善,议政会议制度也面临着被改造的命运。
八旗体系盘根错节,如何改造,颇费心思。为展示这一过程,作者考证了顺治九年(1652)十月起,世祖恢复因多尔衮专擅而一度权力旁落的议政会议后,所任命议政大臣的旗分、职衔和爵秩。与此相比,内三院(内阁)的演变,就要复杂得多。清初设内三院以掌文书,并无参决政事之职,入关后仍之,其地位低于六部、都察院,并非如明代内阁一般为百僚统率。而在世祖亲政以后,这一状况逐渐有所改变。据作者考证,世祖利用加衔的方式,调整满汉大学士品级,令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平级,又频繁驾幸内院,以行动彰显内院的地位。顺治十年(1653),世祖又改革题奏文书处理制度,令内院在中枢政治体制之中的地位大幅提升,成了朝廷发布政令的中枢。
不过,尽管世祖有以内院总揽政令、六部责成庶务,并结合议政会议协调国是的构想,但这一构想在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内院汉大学士地位的上升,引发满人大臣的嫉恨;而内院地位的上升,又引发了八旗体制的反弹。另一方面,汉人精英锐意于儒家传统文化及政治模式,亦不满足此一体制。
顺治后期朝廷之中满人大臣与汉大学士之间的争端,皇帝对汉大学士的疑忌,频见史册。世祖一面以打击陈名夏等汉大学士来对汉官施加压力,一面将内院改为内阁,明诏允许内阁、六科封驳敕旨,并援引汉唐“前代”故事、命翰林官入内直宿,以备顾问,为下一步的变革做好准备。只不过世祖突然逝世,以内大臣为代表的满人势力把持了世祖的政治遗产,遏制了世祖生前推动汉化的趋势,为此将与世祖原意不符的所谓“遗诏”强加身后,遂令这一历史进程中断。
非常遗憾的是,有些历史性的关键人物,本身却并不发声,除了来自各种第三者的表述,我们无法寻找其本人的言论,只能从其行事目的及历史位置做出合理性推断。那些好像发声的“无声者”,在本书的论述中也是一个重点。例如孝庄皇后、多尔衮和鳌拜,他们虽然是历史中的煊赫者,但同样在史料中仅是被描述的他者,种种加诸其身的功过,到底是否具有合理性,又是叙述者以什么样的目的赋予他们的,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历史学者有幸可以占据全部视角的史料,可以从多角度去连缀史实,而不幸又未身在庐山之中,对关节点的缺失通常要靠自己的推论加以掇补。如作者所言:“即使一个具体判断,也需要对大的历史脉络成竹在胸。个案研究若缺乏宏观的历史视野,其意义很难得到完全的展示。”例如对多尔衮与清代政权的关系,皇权与贵族权力的争夺,以及从二元制皇权向一元制皇权的转化,理应是这个问题的讨论重点及最后归宿,如果落入宫廷秘史的窠臼之中,显然研究的关注点就过于“小器”了。如何在庞杂的史料和多维的叙事中加以取舍,确实是“实证史学”中“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地方,也是治史者本身功底是否深厚的一个体现。
“站在史料的尽头”
中国古代史中,如何处理信息的不对等,是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一点在战争史研究中显得尤为明显。因为战争各方在信息的收集上都是不及时和不完全正确的,所以如何判断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以及对各方之后行动所带来的影响,是治史者的首要任务。
不同史料书写者的不同角度,造成史料产生各种偏差。然而我们在使用“偏差”这个词时,无疑是假定有一个“史实”存在,而这种“史实”并不是非黑即白地存在于任何一种史料当中,而是我们依靠各种信息指向及合理性的集中推断。这种推断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一种“历史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可以被定义,当然也可以被推翻,寻找这种“最合理”,恰恰是实证史学的魅力所在。作者需要说服自己,然后说服读者。
各种史料无疑都有存在偏差的可能性,但是也仅仅是可能性。我们根据史料记叙者的不同,将有可能出现的偏差分为:主角光环、叙事逻辑和观察视角。以作者在书中引用的史料为例,类似于某人的编年、行状,无疑会因叙述主体为某人,而使此人带上“主角光环”,而夸大此人在事件中的影响和作用。而所谓“叙事逻辑”造成的偏差,是指史料作者在有意无意当中,用想象内容弥补其不可知的事件链条,致使叙事整个过程出现与史实不同的走向。“观察视角”则是“盲人摸象”之误,这点在《国榷》的叙述中非常常见,史料作者非出于主观意图,而限于其观察角度,不可见事件全貌而产生的误差。
多语言材料的充分占有在清史——特别是清前期史的研究中,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技能,这样要求治史者除了关注汉文史料外,也要兼顾满、蒙文献。例如在作者《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中所提到皇太极东征蒙古的起因,引用了《旧满洲档》和《清太宗实录》中的大量内容。中国人民大学的乌云毕力格教授曾经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发表的蒙古文信件,认为喀喇沁台吉和塔布囊向皇太极谎称蒙古各部联军打败了林丹汗,于是皇太极根据喀喇沁部的报告,要求第二年初夏共同进军察哈尔。而在后来二手资料里,这两封信合二为一,被严重歪曲。这种歪曲首先从《旧满洲档》,然后《清太宗实录》《皇清开国方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官修史相继沿用和继续歪曲、杜撰。
除了多语言史料外,囿于时代,档案史料也是传统清史研究中应用得并不充分的地方。姚先生谈到入关后内院在中枢体制中地位上升的动力,认为当时清朝统治者曾以为可以维持关外的政治架构不变,结果导致六部机构臃肿、国家行政运转失灵(292-293页)。这一看法当系实情,但作者并未举出例子来加以展示,而仅用自己的语言推测。而事实上,就笔者所知,“北大移交题本”之中,顺治十年(1653)正月十七日恰有一件残档(档案号:02-01-02-2034-020),可以直接展示这种“失灵”的状况。
此外,以“逃人法”研究为例,除了《清实录》所录取的史料外,其余采用史料较少。但即使是清代各版本律例中,对此相关款项记载便不在少数,且律中所载远比《清实录》所载详细、严谨。此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阁大库档案》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顺治朝《内阁题本》中,有大量关于相关的逃人档案。当然,如此庞杂的档案梳理,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近乎不可能,于是应用其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也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清实录》
清代中枢政治制度,素来为研究者所关注。据我们所见,研究清代中枢制度的史料,以往所多见者大约有两类:其一是以五朝《清会典》《清文献通考》为代表,清朝人自己记载本朝制度条文的典章政书,其二是以《清实录》为代表,清朝人自己编纂的“当代史”。前者的记载往往失于静态,而且历朝《会典》之《内阁》等章记载均为简略,因而《清实录》便成为研究清代中枢制度的重要史料,学者往往从中撷取涉及中枢决策与政令发布体制的诏令和奏章概要,并加以简要阐释。
姚先生的研究整体上亦遵循了这一史料分析方法。但是对《清实录》的依赖,同时也带来了另一重问题,亦即《清实录》编者对史料的采择,是否会影响本文的结论。诚然,《清实录》作为清朝最重要的官修史书之一,没有人会怀疑其在清朝官方视野之下的权威性。然而,《清实录》不仅是一部朝廷行政文献的汇集,同时也是供后世“敷时绎思、继志述事”的媒介,其中对朝廷文件内容的调整和剪裁,在编者看来或许无伤其意,但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而言就未必全面了。
例如,在《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一文中(369-372页),作者统计了《清圣祖实录》中辅政时期议政诸臣所议事件,认为议政会议的活动渐趋减少,而且其职能与九卿会议渐趋杂糅。作者也意识到这些事例并非议政会议的全部事实,并在行文之中给予了声明(372页)。但事实上,《清圣祖实录》之中遗漏的议政会议发挥作用的案例可能远比想象中为多,这里举一则旁证。在辅臣体制结束十多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平定三逆方略》之中记载了清廷在平定叛乱期间有关军务的命令,这些谕令之中大量出现“议政王、贝勒、大臣”或“议政王等”作为受谕对象或会议政务的主体,而同样的事件在《清圣祖实录》中往往将相关衔号略去,只述谕令之大要,导致议政处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隐形。可知《清实录》编纂者对史料的剪裁,确会干扰我们对中枢政治的考察。
再举一例。作者在探讨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期大学士们的作用,认为此一时期大学士得到重视,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多尔衮篡位,并非源于统治者恢复中原传统政治秩序的意愿(294页),所举出的史料是《清实录》所载多尔衮去世后,大学士逮讯所列党附多尔衮之罪状。这种史料的偏向性,不难想见——事实上可以看到,作者所论证的方向,与《清实录》编者乃至这些“罪状”的起草者想要让读者相信的结论基本一致。而事实则远较这一“结论”复杂。清季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一册旧档,记载了顺治二年五月底至七月初内院诸臣在多尔衮处的对答,后由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多尔衮摄政日记》的名义出版。翻检这一文献可知,大学士们与多尔衮之间的对话,颇多涉及当时政务之得失,乃至具体章奏的批答意见;诸臣亦不乏以治道启迪于摄政王、期以能“得‘君’行道”者。这些情况在《清实录》的“罪状”里自然都是看不到的。
当然,讨论清初历史,史料的局限性始终是个大问题。所谓实证史学的困难之处,在于对史料的逐条辨析,不仅要辨别其是否存在偏差,还有探寻其偏差出现的原因,以及汲取其逻辑的合理性。本书在此方向上可谓用力极深,故而所得见解,也显得有很强的“合理性”。
《多尔衮摄政日记》
让历史研究回归“非关键词”
无论从史实连缀或是辨别上讲,实证性史学文章都要“格物致知”,即将所有资料收集、解读充分,以求将研究问题做到极致,这需要史学研究者的勇气与毅力,用姚先生的话说,这正是历史学的专业性所在:“历史研究带有极强的专业性质,真正的历史工作中必须心存敬畏,细细体味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琐事。”
在“实证史学”的研究中,为某一关键性问题做出第一篇研究文章的,固然不易,但是最值得赞叹的,是对这个问题做出的“最后一篇文章”。向时日本学者研究之精细,常以某问题的“定论之作”为目标,而近年来本国学者,反而失此初心。姚先生之文章最为令人欣赏之处,在于谋篇布局的精美以及论证上的“全面”。
以《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篇为例,己巳之变本身牵扯了蒙古、明朝、后金多方势力,梳理清晰便为难事。而蒙古诸部、明廷之中、皇太极集团内部,也有多种势力潜流,他们互相牵制,关系错综复杂。而文章以谋篇之功,将主要矛盾有条不紊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使集团内部斗争渐次浮出水面。这种多层次的布局结构,建立在作者本身对史料的了解和历史背景的熟悉之上,是治政治史应有之功力。
历史事件往往不是“好的故事”,而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史事之间的联系也往往细致而微。
这种联系可能反映在历史时间上,可能反映在地域的联系上,也可能反映在人和人的互动当中,而为史者除了多读多看,对史料竭泽而渔,似乎再无他法。
随着数据库的发展和史料电子化程度日益增强,有些时候我们“竭泽而渔”的方式就变成了“关键词索引”,这也是史学论文中越发常见的一个现象。即在不同的数据库中输入一个关键词,随后将所得史料进行连缀。这在历史研究当中是一种非常“省力”的方式,但结果无疑是史学的碎片化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成为一本深度解读的“词典”。
另一种“取巧”之法本为西方学者所长,即寻求一条极其明显的线索,以此为基点进行探讨,在新近出版的历史著作中,此现象尤其明显。无论公共事业、贸易、法律,寻找一个标志性的线索或是地域,对此进行“长时段”的描述。诚然,历史学家从来不曾想要放弃宽阔的视野和宏观的讨论,即便微观史学可能思考的也是如何以小见大,如复旦大学周兵教授所言:“卡罗·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揭示了近代早期欧洲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文化并存的社会文化,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深植于近代法国农村的法律、婚姻、家庭等社会背景之中。”
但是,如果以某一事物或区域为单一线索,史料收集虽然相对容易了,但是这一线索同样被赋予了“主角光环”,在其线索之下的很多细节——甚至关节都被忽略了,而史料的组织本来就是一件极受历史研究者主观控制的事情。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除了作者想让你看到的史实,读者可能看不到别的东西。
《历史学宣言》中曾经强调:“新的长时段较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更具活力和灵活性,也更具鉴别能力——这些特点的一大来源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大数据。”但这种灵活性同样会将历史学研究引入歧途。姚念慈先生此时重提“实证史学”,在清史学界有着更独特的意义。
相对于前代历史,清史有着档案资料丰富、私人著述庞杂的特点,换言之,是一个做“名词解释”和“主角光环”类研究更为适合的土壤。而潜心于政治、战争史研究,去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或者说是无法检索的历史,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历史功底,也要耐得住寂寞。以我的研究经验,一篇文章体量的“名词检索”,一个月便可成为“专家”,而这种作品除了为学术添一注脚,为自己完成了一篇发表任务,更大的意义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