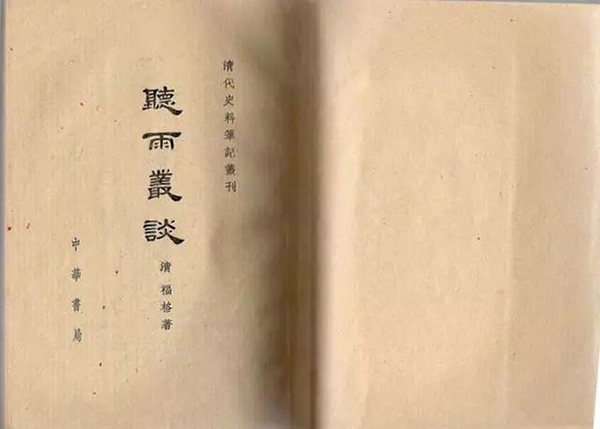鸦片战争后,列强侵华愈深而国门渐开,虽然各种为害日甚一日,客观上却也促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中国。对此等情状,固然有保守势力叫嚣“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奠安黎庶。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语出方浚颐《二知轩文存》),但枪炮胜于刀矛终归是铁的事实,因而最终国人还是对各种“洋人造的稀罕物”从排斥到接触直至接纳。这一过程,细察中国人的心态,往往能感受到别样的复杂、忐忑和矛盾,比如摄影术,就是很好的一例。
一、摄影师成了“催命鬼”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发明摄影术以后,很快风靡世界。恰好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外国商人、传教士从通商口岸涌入中国内地,打通了摄影术的传播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摄影术的引进和发展,乃是与全世界同步的。
摄影术在中国最早的应用,乃是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中。1943年两广总督耆英会见英国人璞鼎查时,璞鼎查赠送给他一张自己及家人的照片。耆英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外交礼节,便请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身份来华的埃及尔用银版照相机为自己拍照,并在次年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时,将四张个人小照赠送给对方。大约同一时期,学者福格在笔记《听雨丛谈》中留下了中国较早的关于摄影术的文字记录:“海国有用照相,涂以药水,铺纸揭印,毛发毕具,宛如奇人。其法甚妙,其制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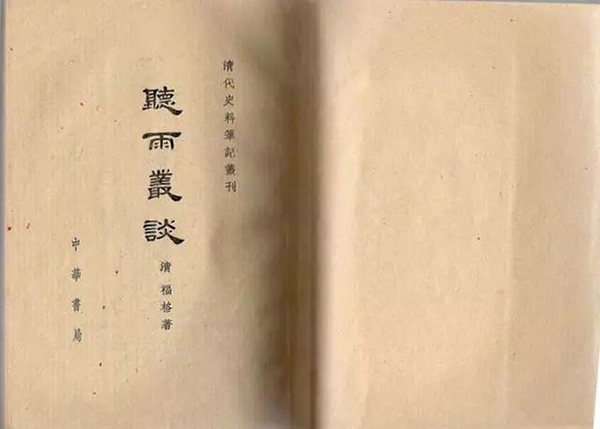
《听雨丛谈》
19世纪50年代后期,外国人开始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开设照相馆,兼以销售摄影耗材和照片。如法国人李阁朗在上海开设第一家照相馆,专门给当地人拍摄肖像照片,名扬一时,事事要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对不需绘画就能出现人的容貌的摄影术更是感到惊奇不已,争相观看和尝试。宦游粤东的广西桂林人倪鸿曾写过一首《观西人以镜取影歌》描述道:“竿头日影卓午初,一片先用玻璃铺,涂以药水镜面敷,纳以木匣藏机枢,更复六尺巾幂疏,一孔碗大频觇觎,时辰表转刚须臾,幻出人全躯神传。”
很快,聪明的中国人就发现,洋人不仅仅用照相机拍摄人和景,还用于军事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郝福森撰《津门闻见录》有云:“英匪入天津时,志颇不小,心亦过细。凡河面之宽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紧地方,无不写画而去。尤可异者,手执玻璃一块,上抹铅墨,欲象何处,用玻璃照之完时铅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画图也。如望海楼、海光寺、玉皇阁,皆用玻璃照去。”这更加快了那些志在报国的开明人士努力学习摄影技术的步伐。
但也就在这时,一些可怖的谣言开始不胫而走了:洋人的照相机其实是一种“摄魂器”,可以把人的魂魄夺走,封印在那么薄薄一张纸片上,而被摄走魂魄的人或者死去,或者听命于洋人的驱使为非作歹……可以想见,这些谣言出自那些持排外论者的臆想,再借助愚昧无知的民众加以传播,“效果”自然是“极好的”。在拍照时曾经遭遇围攻的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回忆:“那些有知识有地位的中国人向人群散布谣言,说照片会‘摄’走人的精气神。人在拍照后就会命丧黄泉……作为一名摄影师,我扮演的角色有些像‘催命鬼’。”
随着时间推移,当人们发现拍照并不会要人命的时候,那些荒唐无稽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不过,由于摄影术早期发展不够成熟时导致的照片模糊、虚影,加之国人普遍对摄影术的原理不够了解,导致另一种说法很快甚嚣尘上,那就是照相机不经意间常常能拍到“鬼影”。
二、轰动长沙的“鬼影照”
狄葆贤,字楚青,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年轻时曾经到北京来游学,结识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与他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随后的戊戌变法中,他积极参与,变法失败后他东走日本,1900年回国参加了维新人士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大起义,担任军火采购工作,“惜内部事机不密,功败垂成”。之后他再次逃往日本,以“平等阁主”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回忆往事故友,后来结集成《平等阁笔记》于1914年出版,其中谈到了一桩谭嗣同与摄影术之间的趣事。
“丁酉(1897年)春间,谭壮飞君过沪”,狄葆贤那时恰在上海,热情地接待了好友。谭嗣同与他闲聊时说,长沙的一家照相馆,“一日为一人摄照,忽人侧多现一影,其影较人短而怪,盖鬼影,偶不及避,为镜光所摄得也”。这件事在长沙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议论纷纷,谭嗣同别有见解,“谓能摄一鬼之影,则凡鬼必皆可摄,日后必有人能制镜,专为摄鬼之用者”。
狄葆贤和在座的朋友们听了谭嗣同的话,并没有当回事,谁知十年之后,狄葆贤在报纸上看到,“(欧洲)某博士创制一新法——照相镜,能摄鬼之影以验其形状”,不禁怀念起好友的预言来,“其时人颇疑其言,不意仅隔十年,此言竟验,今壮飞已宿草,惜不复见……”
事实上,欧洲当时确实刮起了一股“通灵风”,个别骗子用重曝或剪纸黏贴的手法拍摄出了“鬼魂照”、“精灵照”,就连著名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都上过当,替他们鼓吹,这也就难怪思友情切的狄葆贤会轻信其言了。
《平等阁笔记》
《平等阁笔记》中还记录过狄葆贤的好友宣子野听闻的一桩怪事。光绪二十三年秋间,高邮马棚驿有个名叫陆家庄的地方,有个农夫嗜赌,但经常赌输,挨老婆的骂。这一天他又在赌场赔了个精光,他知道自家床头还藏有银两,不敢返家去拿,就让表弟找个别的理由去代取。表弟来到他家,恰是夜晚,不知道表嫂睡下否,便隔窗一窥,“见农人妇正坐灯下纺纱,身后则立一衣冠人”,表弟以为那人是表嫂的姘头,正不知如何是好,却见表嫂专心纺纱,似乎对身边那人毫无察觉。诧异间,见那衣冠人手持一短杖,杖末微曲,“以曲端勾所纺纱,纱辄断,妇复连缀之,连断至五次”。表嫂叹息而起,饮泣良久,解下衣袋挂在房梁上便要伸首投缳。表弟一看也顾不得什么礼数了,大吼一声冲进屋里,表嫂惊倒在地。听闻喧闹,附近的邻居们纷纷赶来相助,也都能看到那衣冠人的形象:“僵立如木偶,冠缨帽,衣马褂并有马蹄袖,胸前挂一方袋,面有微须。”胆子大的后生上前推之,“空如烟雾,手过后一仍其旧,无丝毫损坏之迹”。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来表嫂家“讨替代”的鬼,多亏表弟及时喝止,不然只恐这家人要办丧事了。四五天后,那鬼还在,只是影像浅了一些。宣子野听说此事后,“乃设法往远处借得照相镜具,驰至其地”,本想拍到一段鬼影,谁知这时距事发已经二十余天,“但见有黑影一段,矗立屋中央,如一人形状而已,遂无从摄影”。
本来就是荒诞不经的故事,狄葆贤偏偏还要给出“科学”的注解:“此鬼于聚精会神之际,忽遇人声之震嚇,其幻形乃僵,其幻色乃凝结而不能骤散”。这解释虽然可笑,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西风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清末的人们对鬼神之事,不再是“存而不论”,而是力图给出合理的答案,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三、照片上惊现“蓬头鬼”
1892年,辽宁法库人任景丰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丰泰”,标志着照相业进入了中国的封建统治中心,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从此,中国的照相业开始兴旺发展,一张张照片“飞入寻常百姓家”,对国人在家居生活和思想意识上加快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照片鬼影”的说法依旧存在,宛若启蒙后时隐时现的混沌一般。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由丰泰照相馆拍摄的
仅仅在郭则沄著《洞灵小志》一书中,就有两则相关的故事。一则说有个姓许的官员在甘陇官廨与众僚友会饮,之后拍照留念,拿到照片一看,“见照片山石外板桥间,一女子影伫立,若遥窥者”。大家都很惊讶,官廨内从来没有这个女人。一个武弁看到了,忽然失声喊道:“她怎么来了?”大家讶而问之,武弁说是自己的亡妻,生前跟自己的妹妹不合,妹妹便撺掇母亲虐待嫂子,母亲跑到自己跟前来告儿媳妇的状,武弁一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一枪把媳妇打死了,然后才知道一切都是妹妹在背后搞鬼,却已追悔莫及,“不图其追随至此”。
《洞灵小志》
另一则写有京城有个“以刀笔杀人”的律师,携一家老小到廊房二巷的照相馆拍全家福。等到日子去取照片了,照相馆道歉,说是没有拍好,照片有污损,得重新拍摄一次。律师没办法,只好带着全家老小又去照了一次,谁知再去取时,又说没拍好,给不了照片,得重拍。律师大怒,带着一群人去“砸馆子”。照相馆老板实在没办法,告诉律师说:“第一次拍照时,我们洗出照片一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厉鬼,正扼着你的喉咙,所以才让你重拍,谁知照片出来还是老样子。”说完就把两次拍的照片拿来给律师看,果然如此!律师当场昏厥,醒后才悟出大概是被自己害得蒙冤难雪的鬼魂来算账了。
两则笔记,归根结底,讲的都是冤死的鬼魂心有不甘……这一点与历史上所有因冤成鬼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当然,进步也是有的,至少在“表现形式”上,鬼魂由平面的文字变成了更具观感的图像,或许在“教化人心”上更有震慑作用——当然,所有这些“照片鬼影”也终究不过是穿凿附会或臆想杜撰罢了,可怖尽管可怖,却无碍照相馆的生意,不妨摄影术的传播,毕竟对于国人来说,由摄自家魂魄到伸他人冤屈,接受起来要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