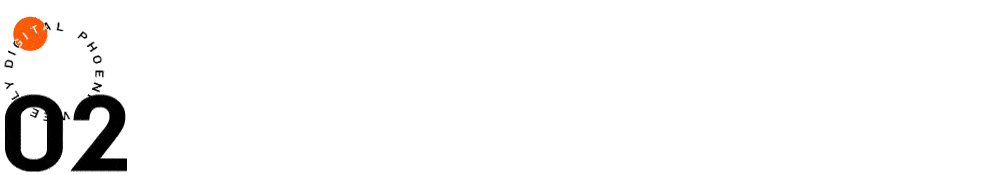作者/霍安治
编辑/陈祥
海峡两岸流行“轻食”。一杯咖啡、一盘沙拉,吃得半饥不饱,满足低糖低盐低脂的“健康风”品味,更油然形成都市白领的高档仪式感。
然而,各式各样的轻食餐馆的价格总是触目惊心,以轻食打造的仪式感是十分昂贵的。但依据中国连锁便利商店“便利蜂”2020年发布的《白领午餐报告》,高达65.2%城市白领,午餐消费金额在20元以内。
其实,中国人的轻食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形成最理想的轻食,不但低糖低盐低脂,而且美味能吃饱。若与今日轻食较劲,“仪式感”更直达皇家派头。
这种十全十美的轻食,就是街边巷尾随处可见的馒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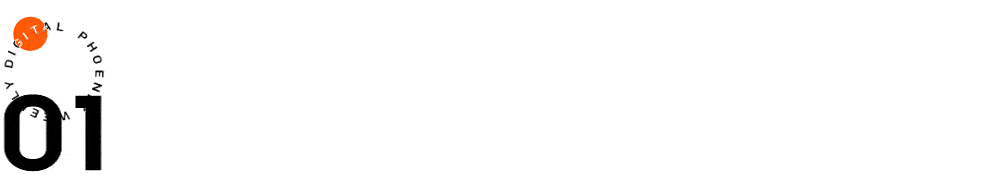
烙饼与馒头的较量
馒头成为梦幻轻食,关键在发面。
早在商朝,小麦就是五谷主食之一。“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中国最古老田园诗《豳风》记载的秦陇农家乐,就有小麦的一席之地。3000年前,渭北高原冬季严寒结冰,农民种植春小麦,于阴历十月收获入库。然而,小麦当成主食很难吃。因为先秦吃小麦只磨外壳不磨面粉,蒸煮麦粒成饭,粗糙难咽。
小麦的好处是耐旱。“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记载苏秦游说西周君,若不放水让东周种稻,必然迫使东周百姓改种耐旱而难吃的麦。小麦虽然入口粗涩,却能保障旱季温饱。因此,豳地(邠州)的农民以黍(黄米)、稷(小米)为主食,搭配菽(豆子)补充蛋白质,再种点昂贵的水稻酿酒,最后才种小麦,以备荒年。
中国人吃麦饭,由商朝吃到汉朝。刘秀进讨王郎失利,狼狈出逃,大雨夜躲进路旁空舍,大将冯异为刘秀张罗了一顿麦饭配兔肩。口嚼难咽粗粝,搭配膻腥烤兔肉,吃得光武帝热泪盈眶,贵为天子后,仍叨念着那碗“滹沱河麦饭”。而东汉的老百姓,却已渐渐摒弃麦饭,改吃面饼。
小麦要好吃,关键在磨粉。磨粉技术约于东汉发展成熟,中国人才能吃上“饼”。诸葛丞相南征,又发明馒头。宋代杂说家高承记载:“诸葛公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需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杀人以首祭,则神享为出兵。公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孔明发明的新食品虽以馒头为名,却未经过发酵,与今日的馒头大不相同。虽然好吃,仍不算“轻食”。
吃面讲究和面。把面粉加水揉成面团,称为“硬面”,可以烙饼、下面条或煮面疙瘩。但要达到“轻食”,还得“发面”,利用酵母使面快速发酵。到了唐朝,发面工序已经普及,馒头却因要不要夹馅,分裂为南北两种风格。
“我们乡下的馒头都是有馅的。不是猪肉,便是豆沙白糖。”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常年寓居北京,吃的馒头是实心的,回忆江南老家的馒头,却是有馅的“肉馒头”。南方人到北京想吃个馒头,话讲清楚不容易:“南方人到北京来,叫人去买几个肉馒头,这便成了难问题了。北方称有馅的为包子,馒头乃是实心的。”
江南的“肉馒头”是点心,不是主食。在全国最富庶的苏锡常,肉馒头的分量小,把面皮做到皮薄似纸,以蟹肉、虾肉、猪肉、豆沙或百果加板油(猪油)调成馅料,讲究的是入口鲜美多汁。周作人回忆家乡绍兴,只有餐馆望江楼:“专卖元宵大的‘候口馒头’,做点心极好,反正并不当饭吃。”
北方以面食为主食,一顿要吃饱,“肉馒头”是不足够的。周作人对北方馒头不大适应:“北边面食是正当的饭,包子有点近于奢侈品,要讲好吃的馅更是奢侈了。正宗还是馒头,而且是实心的、大个的。这蒸得好的,实在不错,但在南方却是不容易遇见的了。”
然而,周作人吃的“实心的、大个的”白面馒头,实际上是当时北方人的“轻食”,而不是“正当的饭”。
北方人吃馒头,习惯不配菜。而馒头是发酵膨大的松软食物,面粉的实际分量并不大,单吃白面馒头难以解饥。因此,普罗大众的家常正餐,常是实心的窝头。若搭配菜肴,则把硬面烙成饼。以饼卷菜,荤素皆宜,才能管饱饭。
若在外吃饭,填饱肚子也不能买馒头。普罗大众一般不上馒头店,而是到“切面铺”。面团轧成薄面,当场以大铁刀切成面条现下现吃,或者带回家下面。老百姓若下馆子,也不吃馒头。东来顺为劳苦大众专设的平价餐饮“大板凳”,出售饺子、馅饼、斤饼、斤面、贴饼子与玉米面,独缺馒头。只有以硬面烙饼下面,才能使劳动人民真正吃饱。
齐如山回忆老北京的大众饭铺,主餐面食是夹菜带馅的饺子、烙饼、包子、馄饨、馅饼、烧麦、锅贴与面条,也没有馒头。因为饭铺顾客多是“有职业,工作较忙,时间宝贵者之个人吃饭”,在主食之外“大致不备汤菜,只备小米粥”。而单吃馒头是吃不饱的。
发面的馒头填不了肚子,一般不当正餐,而是“轻食”。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涛回忆醇王府三餐,早餐主食是马蹄烧饼,午餐晚餐吃面食是煮饽饽、单饼、薄饼或面条,只有夜宵才吃馒头。
论主食的吃饱功能,馒头远不及烙饼,但发酵面的松软口感,却远远超过烙饼。因此,吃饭能配上荤菜的富贵人家,偏爱吃馒头。北方馒头俗称“馍”,西太后吃晚餐,想起殿前顶着寒风站夜哨的宿卫营士兵,派宫女赏餐。士兵苏勋丞回忆,老佛爷赏的晚餐是“一碗肉,一盘馍”。
老太后赏的馒头,虽然是御膳,今人吃来,却要皱眉头。因为当时的面粉、酵母与食碱,技术并不高明。
〓 1941年,中国西部,围坐在一起吃馒头的男人们,可以看出,桌子上没有菜肴。
机制面粉引发口感改革
馒头的原料是面粉,而面粉是十分昂贵的。在北京,无论城区还是城郊农村,普罗民众普遍不吃面粉。燕京大学于1928年进行的平郊农村调查,记录农民的主食是以玉米面蒸窝头、贴饼子或烙糊饼,配上大碴粥或小米粥。有时以荞麦面下面条汤与高粱米粥换口味,就是农家的一日三餐。同年,北平社会调查所调查北平市区工人与教员家庭主食,同样以玉米面为主,其次为小米面、荞麦与高粱。
至于白面,“人人好吃”,但价格太贵。燕大对北平郊区挂甲屯村100户抽样调查,发现:“百家中全年吃白面在五次以下者,约占半数。除年节外,平日几乎完全不见白面,竟有仅在新年吃上1次者;吃5次至9次者,占15%;10次至49次者,占1/4;50次以上者占1/10;每日吃得起白面者,共计5家。”
民初京城物价稳定,玉米面每斤价格保持在大洋5分3厘左右。小米与荞麦每斤7分,白面8分。所以老百姓主要吃玉米面,改善伙食吃小米与荞麦,有钱人家才吃白面。只是当时的面粉虽然价格高昂,品质却远不如今日的面粉。因为1928年老百姓吃的面粉,大多是传统磨坊以人工畜力碾制的“伏地面”。光绪初年,机械磨粉的洋面向中国倾销,按品质分为五种牌号,伏地面与洋粉一比,品质只相当于二号至三号洋粉。
宫廷吃的馒头,是以伏地面蒸成的。不但外观不如洋粉蒸的馒头,口味也大有差异。“土制馒头全为二号或三号面粉制造,不加其他原料,致口味不佳。宜加百分之五砂糖,及盐少许。”中央工业实验所酿造试验室主任金培松分析道,伏地面蒸馒头必须添加糖与盐,才能赶上洋面馒头的口感。
土法制馒头的另外两大原料,也被洋货无情超越。
发面依靠酵母与碱。酵母来自已经发好的老面,或者酿酒剩余的老糟;碱水则是由蒙古草原开采加工的土碱。面粉以温水和面时加入老糟,静置发酵。出现蜂窝状小孔时发酵完成,却有酸味,洒碱水中和除酸味,才能蒸馒头。只是土碱杂质较多,“颜色淡黄,碱性甚重,口味不良,且有害卫生”。而以老糟或老面产生的酵母,只能单纯发酵,远不如新式洋酵母能散放香气,发出微甜口感。
宫廷用的土碱,采自蒙古大草原的天然原碱,运到张家口以水熬煮过滤加工,称为“口碱”。大碱砖利用骆驼驮载,经居庸关辗转到北京,奔波数百里。那碱水之中,有着数百里日晒雨淋、人汗畜尿、风沙尘土与兽毛体臭的味道。
所以,慈禧太后赏赐的馒头不甜、不香、碱味重、口感粗,而且外观不洁白。
迎头赶上洋货,关键在面粉。1878年,上海沙船巨商朱其昂开办天津贻来牟磨坊,模仿当时欧美“火磨坊”,以锅炉引擎为动力驱动石磨,磨面粉用的石磨上盘也改用硬度较高的德国石块,磨出中国第一代“机械面粉”。
1880年代,欧美面粉厂改石磨为钢磨,机械更齐全,中国企业家急起直追。卸任知县章维藩于1894年在芜湖创建益新面粉公司,使用英国制造全套钢磨,热销长三角。寿州企业家族孙家于1900年在上海开办阜丰面粉公司,装置美国制造面粉机与钢磨,打响沪锡面粉业第一枪。1915年,天津商人办寿星面粉公司,引进日本机器,燃起华北企业家自办面粉厂的信心。一次大战导致进口洋粉大减,国内企业家乘机大建面粉厂,夺回机制面粉市场。自1914年至1925年间,全国新建面粉厂达到123家。
面粉厂的机器,门槛并不高:筛麦机去杂质、头道二道净麦机、钢磨制粉机、筛粉清麸机。1890年代时,这套钢磨是全球尖端科技,面粉厂必须雇用洋技师才能开工。到了1910年代,国内铁工厂已能精密仿制。首开中国机械磨面风气的贻来牟磨坊自办铁工厂,于1920年推出全套“机制面粉钢磨全部机器”,由“30英寸起线钢性铁磨制粉机器”,到“修理机器应用大小车床钻床刨床及整理机器各种零件”,完全国产,撑起国内机械面粉厂的底气。
一次大战结束后,国内面粉厂蒸蒸日上,但欧美洋粉低价倾销竞争,压低了机制面粉价格。在北平郊区,土法伏地面每斤8分,机器面粉每斤1角钱。
国产机制面粉迎头赶上洋货,国产纯碱也奋起直追。传统土碱杂质高味道重,洋碱则洁白如粉,碳酸钠成分高达99%。一次大战中,洋碱进口量大减,天津、上海与济南各地企业家争办碱厂。碱厂是高投资工业,资本以百万大洋计算,只有塘沽永利、上海天原与天津渤海化学工业社3家公司创业成功。
其中,天原电化厂生产清洁剂用烧碱,渤海化学厂生产硫酸钠与泡水碱等工业用碱,永利碱厂则生产可用于发面的纯碱。1932年,永利碱厂年产量高达45万担。洋碱进口量48.5万余担,国产纯碱已经站稳脚跟。
国产机制面粉与纯碱到位,就能蒸出美味的机制面粉馒头,但普罗大众还是宁肯吃玉米面。当时的面粉大厂,一大半集中在上海与无锡,依靠长三角的高价“肉馒头”点心维持销量。然而,庚子后的新政凭空产生一群大款消费者,为高价馒头创造了庞大的“轻食”市场。
〓 1900年前后,中国南方,两人在厨房外磨面粉。
新式学校学生创造馒头市场
馒头是“轻食”。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调查1930年代五谷杂粮的蛋白质吸收状况,每食用含蛋白质100克食物而能实际吸收的分量称为“营养价”,大米的“营养价”每100克高达88.32克、马铃薯78.88克、面粉只有35.56克。发成馒头,一口咬下大多是水与空气,面粉含量更低。三个大白面馒头的蛋白质,抵不了一颗土豆。
若论饱足感,吃馒头更是自虐。玉米等粗粮不易消化,饱足感可以维持大半天。白面馒头入口松软,但消化也快,三个大馒头,挺不过一个杂面窝头。
因此,只有富裕人家才舍得吃馒头。清废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皇帝的正餐,是一碗小米与大米合蒸的金银米,配一碗玉米糁粥,加半个馒头。然而,清末教育改革为馒头创造出巨大的消费新市场。
“在这一个国立的大学里,五百多学生。少说一点,每天要吃六七千个馒头。大学生都是正在发育的青年,从小养下的好口胃。每天三餐,盌大的馒头,每餐吃上四五个,毫不稀奇。”名作家谢文炳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纪实短篇小说《馒头皮》,描述母校学生吃馒头的胃口。
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因为自1904年起开办的新式学堂,各级学校学费高昂,公立中学的学杂费每年上百大洋,家中有钱才能顺利升学。因此,大学生多是权贵子女。学校兢兢业业办出贵族伙食,大学生要吃“机器米蒸的干饭,洋面做的馒头”,配上“四盘四盌四碟的荤素”。
大学生养尊处优,咽不下玉米面窝头,主食改成洋面馒头,还要挑剔卫生。谢文炳的同学们吃馒头,一定要扒皮:“蒸好了的馒头有一层皮,说不定蝇子叮过、蚂蚁爬过,至少是厨子的手搬弄过,断然不会干净。如果吃馒头不剥皮,同桌同学即使不给他一个白眼,心里也骂一句:‘瞧这家伙真不讲卫生。’讲卫生的,剥下馒头皮来,当卫生纸用。拿来擦筷子、碟子、匙子,顺便也擦自己手上的粉灰墨渍。在卫生之外要特别表示一点高贵的,不只剥皮,连肉也剥下一层来,只吃馒头中间的一点心子。有的如运动员,吃到高兴的时候,用馒头的皮肉,搓成一颗一颗的小弹子,和邻桌开起火来。”
这剥下来的馒头皮,与吃残的馒头,每天都得扫出几箩筐。蒸馒头的师傅看在眼里,不见“不卫生”的垃圾,只见老百姓平时吃不上的昂贵白面,于是出钱把这些被学生当成卫生纸的馒头皮包下来,连着几桶剩菜剩饭,扛到邻村出售。
村里“一年四季难得吃几回鱼肉的居民”,天天热烈抢购大学餐厅扫出来的馒头皮:“大学生吃剩下的荤素菜吶、各种汤吶,那油水比他家中的咸菜、豆渣、萝卜干、白水煮汤等等浓腻多了。至于残了的馒头、馒头皮,即使干了,细嚼起来,也比他们吃的黑馍馍、窝窝头来得味长。只需花五六个铜子,便可吃那么一盌杂碎似的菜羮,一盌馒头皮,真是何等的便宜。”
卖剩了的馒头皮,挑回家中,就是馒头师傅的晚餐:“卖剩下的菜羮,经过烧煮后,发出一股醒胃的菜香。饭上热过的馒头皮,看去也十分酥软。”家里的几个孙子,天天“欢喜地嚷着要菜羮、要馒头皮”。
教育为馒头创造了全新的消费群。谢文炳留美海归,前后于5所大学任教,个个都是馒头的消费大户。民国初年,工商业突飞猛进,金融投机更是火热,城市规模一日千里。都会新贵手无缚鸡之力,工作不耗体力,以“轻食”为主餐是恰到好处的,吃馒头当主食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然而,馒头成为美味“轻食”,还差最后一步。
馒头的香味,来自酵母。传统的酒糟与老面酵母虽然能发酵,但品质不齐。食品专家尝试改用欧美各国烤面包用的“压榨酵母”和面,大放异彩。金培松记载:“酵母菌种可采用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之面包酵母。制成之馒头有香气,微带甜味。不特适合口味,而且合于卫生。”
“压榨酵母”是机器制造的。原料是糖蜜或糖化麦芽,加入硫酸铵或过磷酸盐发酵,以机器控制加温、冷却与空气供应,酵母养成后以离心机高速分离余液,以压滤机过滤,产出的糊状酵母与淀粉和成固体,压成块状。环环制程参数都是欧美大厂的业务机密。
民初上海等大埠渐渐流行面包,外国压榨酵母大举入侵中国市场。在上海一埠,压榨酵母年销量高达数十万大洋,全是德国货。中央工业试验所奋起直追,进行逆向工程,由菌种选择、发酵醪浓度、含氮添加物试验到通气条件,全部从零摸索,成功制出国产压榨酵母。
机制面粉、纯碱与压榨酵母,是提升馒头风味的三大要素。抗战军兴前夕,国内厂商与研究机关已经成功破解三大要素,只待经济发展扩大高档“轻食”市场,就能风行草偃。只是抗日战争惊破了方兴未艾的轻食风,即使是消费力最强的大学生,也得改吃糙米饭。
然而,抗战时期消费力最低的军人,却误打误撞,扛起馒头的发展重任。军人甚至将吃馒头的习惯,散播到全中国最偏远的海角天涯。
大兵吃馒头
“自古当兵不发愁,不种麦子吃白面,不种芝麻吃香油。”袁世凯小站总兵,大幅提高部队薪饷。绿营的士兵月饷白银一两半,另发3斗老米主食。袁宫保的新军士兵月饷调高为3两3钱,另加9钱银子伙食费,部队从此吃上馒头。
馒头是“轻食”,原本不适合热量需求高的部队伙食,但馒头是最适合长途行军的军粮。部队要打仗,还得吃馒头。
经过发面的面食,可以在常温下保鲜多日。新鲜馒头只要不沾口,能放两三天,所以部队吃馒头,必须撕着吃,严禁直接啃。若是长途行军作战,将馒头晒干,就是能保质半个多月的最佳口粮。如果行军带咸菜,把发面轧成1寸来厚的大饼,微油入锅烙熟,水分更少,口感也好,同样能携行多日。
馒头与大饼,解决了千年无解的行军口粮问题。传统行军口粮是带煎饼,但煎饼是以杂粮面烙成的。小米、高粱与玉米和成杂面,表面营养成分高,但是人体实际能吸收的养分有限,入口又是坚硬干涩。
在煎饼之外,各种粗粮也不合军人胃口。左宗棠收复新疆,部队出嘉裕关,士兵背上八天份的生红薯,充饥解渴都是一颗红薯。只是红薯是粗粮,粗纤维产生持久饱足感,实际消化形成的热量却很有限。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在沙漠里吃了8天红薯,走到一半,体力就撑不住了。
因此,袁世凯让部队吃白面。每到作战前夜,部队全体动员揉面,蒸馒头烙大饼,伙食竟比普罗大众高一档次。只是馒头毕竟是“轻食”,行军作战固然可以充饥,但平时驻地训练如果还是天天单吃馒头,常会造成饥饿感。北洋时期财政破产,部队欠饷,办伙勉强吃着白面馒头,却没钱买肉炒菜。彼时的吴佩孚部流传着一首地下军歌:“约一约,约斤馒头,早晚两顿粥,小米儿菜,老盐菜,管吃不管够。一二三……四。”
“管吃不管够”的馒头,成为北方部队的固定主食。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60万大军约1/3是北方人,到了不产小麦的台湾,也得吃面食。于是,部队备上蒸笼,在一日三餐中热量需求最低的早餐吃馒头。早年台湾男子服义务役,每吃一次馒头,距离退伍就近了一天,军旅生活戏称“数馒头”。
“数馒头”虽然是不堪回首的柳营旧梦,军中馒头的制作却不含糊,沿袭了抗战前的馒头三要素。数足了馒头,官兵退伍离营,也把馒头带入台湾社会。台湾于日据时期一穷二白,又不产小麦,原是美食的绝地。老百姓以红薯解饥,下馆子吃一顿精白米饭配腌萝卜,已是无上享受。以一等精粉、纯碱与“压榨鲜酵母”蒸出来的馒头,激起台湾大众对馒头的热爱。
今日,中国人不分南北,对馒头已经习以为常,馒头进一步演化成最完美的“轻食”。早年的部队大馒头分量十足,半形如同半截杠子。今日馒头已大幅缩小,更在馒头三要素之外,增加万千口味,符合低糖低油低脂健康风。唯一的缺点,是缺乏“仪式感”。街边热气蒸腾的馒头店,“仪式感”比不上咖啡馆里点一份人民币40元的美式咖啡配“藜麦”南瓜沙拉。“藜麦”原产于美洲,连粗粮都要精心选用洋货,才能展现洋味“仪式感”。
中国人吃轻食,或许还是馒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