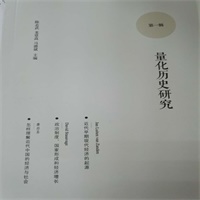苏芬战争中的芬军士兵和驯鹿
(图片来源于网络)
苏芬战争和战争赔款
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结构性变迁(Structural Change),即产业升级和劳动力从农业向更现代、更高收入、更依赖技能的行业转移(Lewis, 1954)。这种转型是否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的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来实现?尽管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已久,但关于大规模国家干预的长期实证研究仍然相对有限。本文研究了二战后芬兰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的独特历史案例,为国家工业政策的长期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1939-1940年,1941-1944年,芬兰与苏联经历了两场战争,都以芬兰战败告终。根据1944年的战败协议,芬兰需要向苏联支付高达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以工业品形式偿还,芬兰需要在1944-1952年间,向苏联输送总额相当于年均GDP 4%的工业产品,并且必须在六年内完成支付。这对当时仍以农业为主的芬兰经济来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迫使芬兰向重工业和制造业转型。
尽管战争赔款本是战败国的经济惩罚,芬兰通过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生产,不仅成功履行了赔款义务,成为二战后唯一按时还清战争赔款的国家,更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产业升级,奠定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基础。
图1 战争赔款与战前芬兰经济结构
长期影响:产业结构的永久性转变
为了满足赔款要求,芬兰政府不得不大规模投资相关工业,并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使本国企业能够生产苏联指定的如造船、机械、电缆和火车头等重工业产品。原本农业主导的芬兰经济向制造业倾斜,形成了一轮由外部冲击倒逼的工业化,形成了新的产业格局。
为了评估战争赔款对芬兰工业的长期影响,作者采用了双重差分(DID)方法,将涉及战争赔款生产的行业(如造船、机车、电缆等)作为处理组,而未受战争赔款影响但具有相似特征的制造业行业作为对照组。研究发现,受影响行业在1952年后保持显著增长,相较于未受影响的行业,相关行业的产值增长约 20%,就业规模增长约 18%,附加值提升约 15%。
然而,传统的双重差分(DID)分析可能存在一个潜在问题:二战后整个欧洲,包括苏联和西欧,都在进行战后重建,这可能导致对重工业产品的普遍需求上升。如果这些行业的增长主要源于欧洲范围内的普遍需求上升,而非芬兰政府的政策干预,那么双重差分的估计可能会夸大战争赔款的作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引入三重差分方法,将芬兰与挪威进行对比,利用挪威工业数据作为额外的对照组。选择挪威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挪威的工业数据采用与芬兰类似的四位行业分类,使得数据在时间和行业层面上具有可比性;其次,挪威与芬兰同为北欧国家,经济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是一个合理的参照对象。结果表明,芬兰特定行业的增长并非是整个战后重建工作的普遍趋势,进一步确认了战争赔款推动了芬兰工业化。
图 2 芬兰 vs. 挪威工业增长对比
个人层面影响:收入增长、教育提升与社会流动性增强
战争赔款不仅推动了芬兰的产业结构转型,也深刻影响了个人的长期经济状况。
作者跟踪个体超过30年的收入和教育轨迹,发现战争赔款推动的工业化显著提高了受影响地区居民的长期收入,他们在1970年代的收入水平远高于未受影响地区。
此外,这些地区的子女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更有可能完成高中及大学学业,尤其是进入高收入行业(如技能密集型制造业,如造船、机械制造等领域),推动了社会向上流动性。
战争赔款还增强了个人的职业晋升机会,在受影响地区,工人不仅获得了技术培训,也更有可能进入高薪行业,从而打破了代际贫困的循环。
结论和启示
战争赔款加速了芬兰的工业化,并形成了持久的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如此,在个体层面上,战争赔款推动的经济转型提升了个体收入水平,使更多人有机会通过高薪工作和教育投资改善生活,提高了社会流动性。
从战败到工业化成功,芬兰的战争赔款案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实验,展示了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生产如何塑造长期经济发展。即使是被动接受的外部经济冲击,也可能成为塑造长期经济繁荣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