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普京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再次谈及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使“乌克兰成为中立国,以及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细数了新纳粹在顿巴斯地区的所作所为。
乌克兰的新纳粹主义从何而来?本文追溯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乌克兰的国家构建历程,从20世纪20年代顿佐夫领导的早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二战期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的共谋,冷战时期奉行激进民族主义的流亡政府,到苏联解体后反俄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最终发现:在乌克兰的国家构建历史中,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传统并行存在,其历史叙事的内核是反俄主义。
本文摘自《乌克兰前线:边界危机》(Frontline Ukraine: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由上海三联书店引进(待出版)。作者为英国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译者为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朱积慧。
文 理查德·萨科瓦 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译 朱积慧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乌克兰国家一元论(monist)和多元论(pluralist)的两种愿景长期对立(参见 《理查德•萨科瓦:两种乌克兰国家模式,一直争论不休》 ),2013—14年的乌克兰危机正是两者之间的一场战斗。
一元论的民族主义(monist nationalism)认为,当乌克兰的国家构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育不良后,乌克兰民族必须要抓住机会加入民族国家的行列。他们认为,1654年由博格丹·赫梅尔尼茨基将军【Hetman Bogdan Khmelnitsky,译者注:盖特曼(Hetman),乌克兰语为гетьман,意为将军,是15至18世纪波兰、乌克兰及立陶宛大公国军队指挥官的头衔,地位仅次于君主。】签署的将乌克兰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佩列亚斯拉夫尔条约》(The Pereyaslavl Treaty)要被取消,随后的几个世纪的俄罗斯化进程也要一并被取消。后者只是在19世纪末期才转化为有意识的俄罗斯化计划。乌克兰化首先意味着要给予乌克兰语以官方语言地位,将其作为国家单一的、最重要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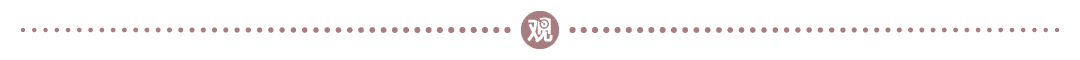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顿佐夫与早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乌克兰国家的一元主义观点部分吸取了乌克兰民族主义作家迪米特洛·顿佐夫(Dmytro Dontsov)的观点,他的激进思想塑造了1929年在维也纳成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rganis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由于曾在帕夫洛∙斯科洛帕得斯基将军(Hetman Pavlo Skoropadsky)的政权任职,随着1919年该政权的垮台,顿佐夫也受到冲击。乌克兰在革命和内战时期独立建国的最终失败,使他后来的思想和政策更加激进。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族的人口聚居区分散在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几个国家之间,位于苏联境内的部分成为了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顿佐夫写下了对于乌克兰在1917—1921年之间独立失败的批评,包括了对当时主要乌克兰领导人物的人身攻击。他否定了他青年时代倡导的社会主义,转而接受了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排除了与俄罗斯达成共识与合作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新的“契约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f the deed)和统一的“民族意志”(national will),并认为暴力在推翻旧秩序方面要发挥重要作用。他谴责了乌克兰社会中部分存在的俄罗斯主义、波兰主义或奥地利主义,反而主张创建拥有“热忱和石头心肠”的“新人”来摧毁乌克兰的敌人。他认为,民族文化是神圣的,应该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加以捍卫。
顿佐夫没有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但他的作品为这次运动提供了很大的启发,而且他直至今日仍在整个乌克兰民族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由主义、民主和缺乏政治意愿被当作未能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罪魁祸首,随后民族主义者们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
尽管意识形态存在固有的烦乱和矛盾,法西斯主义关于国家重生的想法却深入人心,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恰恰符合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对法西斯主义通用的定义:“一心要动员所有‘健康’的社会和政治能力来抵制‘堕落’,要充分利用政治文化与社会和伦理文化的再生,以实现国家复兴的目标。”精英主义、强人领导、军国主义价值观和群众动员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要素,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并不一定是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所说的“最低限度的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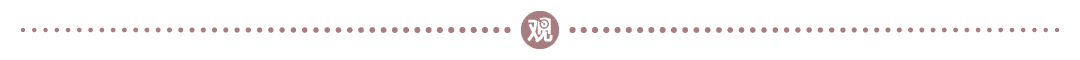
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安德烈∙梅尔尼克(Andriy Melnik)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了抵抗波兰统治的运动。1933年6月,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加利西亚的全国负责人,而加利西亚地区在一战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班德拉领导了针对波兰官员和政策的刺杀运动。他于1939年9月从波兰监狱释放,并搬到德占波兰的政府首都克拉科夫(Krakow)。
左:纳粹宣传照片,右:乌克兰捷尔诺波尔的班德拉雕像(图自前进报)
在这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裂成由梅尔尼克领导的更为保守的派系“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梅”(OUN-M)和由班德拉领导的更为激进的派系“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班”(OUN-B)。按照1939年8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条款,加利西亚首次被纳入苏联。但和平只持续了两年,1941年6月22日德国的入侵首先受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欢迎,因为他们预计德国将重新以某种形式建立乌克兰国家。
班德拉信奉着一套有毒的整体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这是一套独一无二的、以种族为中心的乌克兰民族定义独有的民族主义定义,还伴随着对那些他们号称会破坏此愿景者的诋毁,特别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他认为俄罗斯人是最糟糕的。
班德拉的支持者认为,他实际上提倡的是一套容纳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包容性国家构建政策,只要这些人支持他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在德国占领初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之所以参与屠杀犹太人,与其说是由于强烈的反犹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在特殊情况下与纳粹结盟。到1941年底,他们的暴力行为开始针对德国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国家来统一乌克兰族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愿意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支持。
组织的另一个目标是否认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历史道路,用顿佐夫的话说,“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与欧洲的统一都是我们外交政策的绝对必要条件。”
1941年6月30日,班德拉在利沃夫宣布建立乌克兰国家,任命他的同伴雅罗斯拉夫·斯特茨科(Yaroslav Stetsko)为总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配合德国人作战,对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犯下了暴行。而纳粹德国却是一个善变的盟友,7月5日,班德拉和同伙被捕,他们在德国集中营一直待到二战结束。班德拉被带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泽伦鲍(Zellenbau),1944年9月被释放,因为当时德国人认为可以利用他对付进攻中的苏联军队。
班德拉的追随者们组织起了由乌克兰人组成的武装党卫队夜莺营(Waffen SS Nichtengall Battalion)和罗兰营(Roland Battalion),残忍地造成了50万人的死亡。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班的军事部队,乌克兰起义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于1943年在沃伦(Volyn)建立,为战后的乌克兰独立而战。这导致了波兰与乌克兰长期内战更趋激进。
从1943年7月11日“血腥星期天”开始,乌克兰起义军在沃伦屠杀了大约7万波兰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以及一些手无寸铁的男人;到1945年,起义军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至少杀死了13万人。在1944年夏天乌克兰被苏联解放后,在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的支持下,乌克兰民族主义抵抗者(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班和乌克兰起义军)继续开展了对波兰和苏联的战争,直到1949年。1959年10月,班德拉本人在慕尼黑被克格勃暗杀。
巴亚尔大屠杀纪念中心。图自建筑日报ArchDai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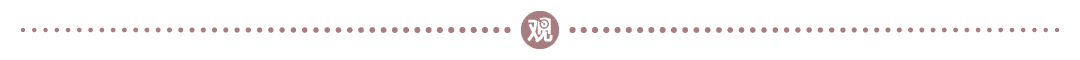
班德拉成为乌克兰化主义者的一大象征。1945年击败纳粹德国并没有给加利西亚带来和平,苏联军队还与班德拉的叛乱武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在班德拉去世后,这种军事化的激进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血脉,伴随着明显的反俄意识形态在海外移民中延续下来。斯特茨科在1959年班德拉去世后接管了乌克兰流亡政府的领导权,直到1986年去世。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领导者都与该组织有关联,包括2000年至2010年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
尤先科是乌克兰第一位支持恢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及其具有争议性的领导人班德拉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最具分裂性的行为之一就是在2010年1月22日授予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头衔,这一举动受到了欧洲议会和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等机构的谴责。直到一年后,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才正式宣布该奖项无效。
尤先科将承认大饥荒的种族灭绝性质作为其总统任期内的核心支柱。2006年,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提出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一举动与总理亚努科维奇以及200多名来自东部的国会议员产生强烈分歧,他们大多弃权或不参与投票。第二年,尤先科试图将否认大饥荒和大屠杀的行为视为刑事犯罪,但议会没有对该法案进行投票。
流亡运动启发了被俘民族委员会(Captive Nations Committee)的成立,该委员会于1959年说服美国国会正式承认了“被俘民族周”(Captive Nations Week)。这种被美国认可的纳粹主义将乌拉尔人(Idel-Ural)和哥萨克人(Cossackia)视为“被俘虏的民族”,俄罗斯则被描绘为“俘虏者”。
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在这种传统中,俄罗斯被认为是天生的邪恶者,俄罗斯帝国主义在苏联之前与之后都被认为是压迫性的,因此苏联的衰败并没有带来丝毫的改变。这种不可调和的反俄主义成为了一元民族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阻碍了美俄两国发展具有建设性和务实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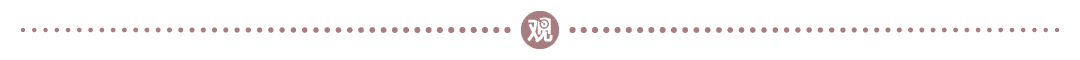
苏联于1991年解体时,准乌克兰国家获得了独立,领土变得比从前更大了。苏联的治理机构被自由民主的治理形式所取代,苏联经济开始向市场体系过渡。然而,与乌克兰争取独立国家的斗争有关的创伤仍然在国家意识中存在。
2007年10月,利沃夫市以班德拉的名义竖立了一座雕像,乌克兰西部的其他几十个城市也纷纷效仿。极右翼的领军学者安德里亚斯·乌兰德(Andreas Umland)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是所有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的历史灵感主要来源,尤其是更激进的政党。”
2014年1月1日,在基辅独立广场举行的抗议活动高峰期间,一场1万5千人规模的火炬游行庆祝了班德拉的诞辰150岁周年,支持者不仅有民族主义的斯沃博达党(Svoboda Party),还有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的祖国党(Batkivshchyna Party)。
所有这些对于东南部的大量亲俄居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和不可理解的,对于他们而言,苏联时期是一个发展和进步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赋予了现代乌克兰国家的领土形态,包括在西部和东部有争议的领土以及南部的克里米亚。
红黑色的乌克兰起义军旗帜再次被视为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的象征。正如在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乌克兰国家构建也采用了删减版的修复模式。虽然所有1991年生活在乌克兰的人都自动获得了公民权,包括许多驻扎军人,但民族化的国家仍然倾向于使最终社会“乌克兰化”,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强乌克兰语的单一语言地位。
经过激烈辩论后,这一观点被纳入1996年的宪法中。第10条在诋毁俄语的地位方面很值得玩味:“乌克兰的国家语言是乌克兰语……在乌克兰,少数民族自由发展、使用和保护俄语和其他语言的权利得到保护。”在这句话中,“俄语”之后的内容特别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政府开始将俄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混为一谈。
这个新国家试图创造自己的象征和神话,但却没有统一的民族叙事。事实上,过去二十年来有很多讨论都是关于乌克兰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和乌克兰化进程的弱点与不足,他们认为俄语使用者更像是这一过程中的烦恼而非重大障碍。乌克兰发展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共同体,在其中,乌克兰的文化和艺术实际上可能已经有所减少。
然而,深层次的文化斗争一直持续不断,记忆的政治、现世的圣人们都被用作政治交换的资本。与许多东欧国家一样,民族构建都伴随着明显的受害者狂热(cult of victimhood),这成为了新冲突的温床。尤其是“大饥荒”(Holodomor)对民族的自我认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乌克兰化首先意味着要将给予官方语言以最重要的优先地位,将其作为国家单一的、最重要的标志。这种形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肯定了族裔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民族化的野心和意识到乌克兰是一个脆弱的民族和领土集合体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激起了对乌克兰国家凝聚力的担忧。
因此,由于担心该国的领土完整,乌克兰的民族精英坚持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一元模式是综合的一种民族主义,其中国家是一个民族化的国家,利用乌克兰主义的传统来填补现有的边界,与俄罗斯区分开来。这也意味着单一的官方语言、单一制和文化特殊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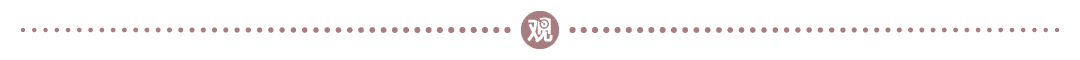
综合民族主义(integrated nationalism)与整体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的经典思想有一些共同点,但也有差异。综合民族主义基本上是面向国家发展的公民模式,并且包容多样性和公民权利;整体民族主义推崇以单一语言、文化和神话统一人民的法西斯主义路线。
而复原性民族主义(restitutive nationalism)是一种狭隘的、非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其目的不是要反映既有的现实情况,尤其不是要反映构成当代乌克兰领土的不同历史叙事,而是要恢复某种理想化的国家形象,达到重建国家地位的目标;在极端情况下,它继承了20世纪法西斯运动支持的整体民族主义的方方面面。
军事民族主义团体——斯沃博达党(Svoboda Party,意为自由党)正是如此。成立之初,该组织以乌克兰社会民族主义党(Social–National Party of Ukraine,SNPU)自称,显然是参考了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党,1991年在利沃夫由奥列格加戈尼博克(Oleg Tyagnybok)、安德烈帕鲁比(Andriy Parubiy)等人建立,宣扬“公开的、革命的超民族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主张,将乌克兰的所有弊病都归咎于俄罗斯”。这也是“招募纳粹光头党和足球流氓”的首个政党。
2004年,该党改名为斯沃博达党,官方标志从新纳粹的狼獾(德语为Wolfsangel,英文翻译为Wolf's Hook)替换为三根手指组成的三叉戟(乌克兰国徽),加戈尼博克成为唯一领导者。直到2013年之前,他们都在传播乌克兰版的纳粹主义。反犹主义在斯沃博达党内深深扎根,但是它的恐俄主义情绪(Russophobia)的程度要厉害得多。斯沃博达党还与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意大利的新法西斯组织三色火焰(Tricolour Flame)结盟。
2008年的经济衰退使乌克兰备受打击,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分歧,右翼民粹主义开始抬头。更主流的祖国党(Batkivshchyna Party)也同样强烈地反映了乌克兰一元论民族主义者渴望创建一个文化统一的、说乌克兰语的国家的主张,这与文化、语言多样化的多元主义的乌克兰形成鲜明对比。
一群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参加了选举,特别是斯沃博达党。在乌克兰独立后的前二十年历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极右主义将最终被释放出来。在2012年10月28日的议会选举中,斯沃博达党在比例代表制选举部分获得了10.44%的选票,25名候选人获得最高拉达席位,另外还有10名候选人在单一选区选举中生出。议会成为了与“犹太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渣滓作斗争”的讲台。欧洲议会当时通过的决议谴责该党为仇外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
民族国家化的进程既可以采用公民民族主义的形式,也可以采用更激烈的排外民族主义的形式。与西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同,即使是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也支持加入欧盟。对他们来说,欧盟的体制和规范结构并不具有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是泛欧洲(Wider Europe)所代表的政治空间。欧盟扩大到后苏联地区和乌克兰意味着逼回俄罗斯的影响力,限制其地缘政治主张。换言之,对于斯沃博达党而言,欧盟与欧盟所包含的人权、善政的规范性价值、特别是克服冲突的逻辑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眼中的欧盟意味着经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强化后的西欧地缘政治的对外投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偏爱欧盟并不是为了它的原则,而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系列与俄罗斯利益相悖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