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临近,
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开卷!
真正的“硬核出片玩家”,
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一路向西,深入敦煌戈壁。沙海中,数万面镜子和光伏板追逐着日光。外星基地的科幻感满满,来这儿你分分钟化身《沙丘》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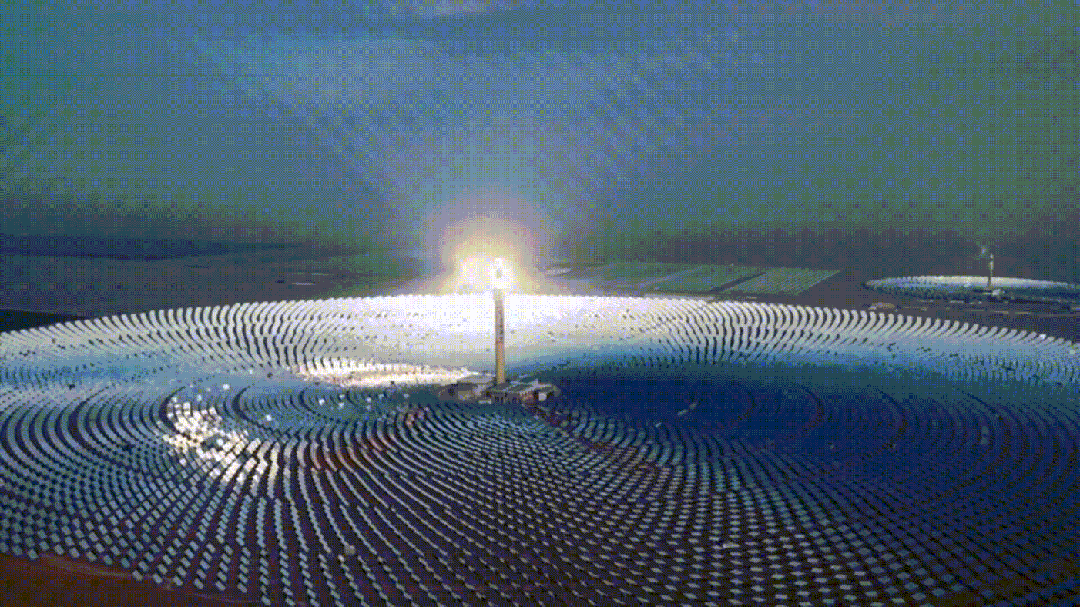
中国首座百兆瓦级光热项目: 敦煌熔盐塔式光热电站 图源敦煌发布
觉得太热?也可以试试去浙江临海的括苍山巅。云雾翻涌,几十层楼高的白色风车缓缓转动,如同宫崎骏《风之谷》的童话梦境。
全国四大风电场之一: 括苍山风电场 图源俯瞰宁波
以上这些,并非孤例,它们正是中国清洁能源版图上日益增多的标志性景观。就在今年4月底,国家能源局发布了一项里程碑数据:我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历史性地首次超过了传统的燃煤火电!
我国火电及煤电装机容量 图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王磊明绘
然而,风电与光伏属于“看天吃饭”:风不会一直吹,太阳也会下班。如何让这些转瞬即逝的绿色能量,也能在需要时稳定输出?
答案,或许就藏在一种最常见的元素里——氢。
今天TTone桐频走进致力于此领域的先锋企业:氢辉能源,对话其创始人兼董事长李辉教授。
“为什么是「氢」”
1869年,科幻大师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里就梦想着用氢气驱动“鹦鹉螺号”潜艇。
在他的想象中,氢气作为燃料高效、清洁,而且来源极其广泛,在地球各个角落都有丰富储备。而今天,这个百年前的梦想,正一步步变成我们身边的现实。
《海底两万里》“鹦鹉螺号” 图源BBC
田桐:
李教授,当“氢能”作为清洁能源被提到时,总是免不了与“绿色”挂钩。氢能源是自然界唯一的脱碳资源,使用它作为燃料唯一的产物就是水——也就是说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氢吗?
李辉:
氢气(H₂)占物质75%,是宇宙最丰富的元素,以水形态广泛存在。在传统化工领域,氢气常常作为还原剂。而现在它也是重要的清洁能源载体,可以通过燃料电池将风光电转化的氢气再发电。
氢 图源pixabay
田桐:
您提到了风光电这类新能源,跟火电、水电相比,风电、光电主要“靠天发电”,发电高峰可能用不完,低谷时又不够用。甚至电流忽大忽小,还会威胁电网稳定运行。那氢在这一领域具体有怎样的作用?
李辉:
当电网还不能完全去消纳这些风电和光电时,我们就需要使用存储和调峰等等方式配合可再生能源电网。氢储能凭借跨季储能、空间转移等优势,成为消纳风电和光电的主要方式。
宁夏 光伏太阳能发电板与风力发电机同框画面 图源人民日报 周序鹏摄
田桐: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近几年在生活中听到比较多的是氢能源车。2019年曾经有一辆“加水就能跑”的神车刷屏,其实它的原理就是与制氢相关。相较于现在更常见的锂电池电动车,氢燃料汽车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辉:
与锂电储能相比,氢储能储时较长,具有时间、空间及应用领域灵活性。氢燃料电池汽车续航里程长,如小轿车一公斤氢气可行驶100公里;充气快,充满一箱氢气仅需三分钟,且氢气发电过程零碳排放。
氢能汽车 图源ChinaEV100
田桐:
但现实中氢能源车在充能方面不太方便,加氢站的普及度远不如充电桩。而且运氢、储氢还在发展当中,这是不是氢能源车发展的一大阻力?
李辉:
目前加氢站数量确实远少于充电桩,不过五年前充电桩也不普及,所以这一点不是氢能车发展的主要瓶颈——目前的核心制约其实在于氢气供应,特别是高纯度氢气从生产地运输到城市的成本比较高。这是一个涉及制氢、储氢、运氢等各个环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环节共同克服。
“走出实验室”
李辉教授的科研之路始于清华,曾赴氢能“硅谷”加拿大温哥华深造,亲历氢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全球浪潮,后归国任教南方科技大学。
李辉教授主页
2009年受德国著名燃料电池专家Jürgen Garche和美国电化学专家Chris K Dyer的邀请为“电化学能源大全”撰写了“质子交换膜燃料污染”一章。
李辉教授参与编纂“电化学能源大全”(Encyclopedia of Electrochemical Power Sources)
其创立的氢辉能源研发出的多项技术属国内首创、国际领先。包括开发80~100微米双增强型质子交换膜(PEM) 、抗渗氢膜电极(MEA)。她为何押注氢能?当论文走出实验室,又会遭遇哪些挑战呢?
氢辉能源主要产品
田桐:
现在,主流的电解水制氢技术包括碱性电解水(ALK)、质子交换膜电解水(PEM)、阴离子交换膜(AEM)等技术路线。您当下主攻的是PEM和AEM技术,它们主要的难点有哪些?
李辉:
这两条技术路线的核心材料均为膜,PEM为质子交换膜,AEM为阴离子交换膜。目前PEM技术成熟度约6-8分,已大规模产业化,目前亟需降低成本。AEM技术成熟度仅3-4分,大规模应用尚需时间。我们认为这两种技术特别适合应对风光电的波动性,在未来制氢领域有独特优势。
田桐:
氢能技术涉及材料、电化学等多学科交叉,门槛极高。您作为从实验室走出的创业者,如何看待产学研转化中的“死亡之谷”现象?论文成果该如何走出实验室?
李辉:
我本人是本硕博都是化学工程和电化学工程,工程和材料的有机结合也有利于学术到产业化的跨越。学术研究的质子交换膜尺寸只有A4纸那么大,但是产业化需要实现每年数万平米的连续生产。从a4纸到10万平米一年的飞跃,这里边牵扯到工艺流程放大、品控等等问题。
李辉教授为田桐介绍质子交换膜电解槽(PEM)
田桐:
氢辉的团队架构是怎样的呢?
李辉:
我们团队是明确的“博士+工匠”组合,硕博和博士后这类研发型技术人才占比约70%,还有经验丰富的生产人员,比如具有10年经验的机长。
“绿氢崛起之路”
2022 年俄乌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危机,欧洲多国能源供应中断。中国每年进口约4000亿人民币的天然气,可见能源供受地缘政治影响的风险极高。
而氢气,这种看似普通的气体,或许是改变能源格局的关键。据统计,目前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推出绿氢战略及相关政策。发展绿氢,不仅能减少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还能将风光电资源就地转化利用,意义已经上升至国家级战略层面。
绿氢 图源凤凰X+
田桐:
在以前运用过程当中,PEM的质子交换膜是一个海外卡脖子的技术吗?
李辉:
其实不光是海外,全球在两三年之前都没有这个增强膜,都是用杜邦质子交换膜117,甚至传统的117在中国是很难买到的。不过从我们氢辉去年开始产业化增强型质子交换膜的时候,整个电解水的电流密度都大大升高,去年一年成本就降了1/3。
氢辉能源增强型质子交换膜产品
田桐:
根据国内外的反馈,你们的质子交换膜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领先。现在具体是多厚?
李辉:
传统的是180个微米,我们这款是80微米、50微米的,我们还在研发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希望它越来越薄,导电性变高,成本变低。同时我们要在一些机械强度、化学强度等方面增强它。
田桐:
2024年有国际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产氢大国,预计每年可生产22万吨绿氢,比世界其他国家总和都多出6万吨。总量虽然看起来多,但绿氢的占比仅有1%,因为我国的氢气制取仍以黑氢和灰氢为主,占比超过80%。绿氢、灰氢、黑氢——它们都有什么区别?
灰氢、蓝氢、黑氢、绿氢的区别 图源凤凰X+
李辉:
它们主要是根据在制备的过程中碳的排放量来定义的。黑氢是煤制氢,灰氢是天然气制氢,这二者是非常传统的现有技术,尤其黑氢制备过程当中碳排放量很高。简单来说,你如果是用绿色的电,也就是风光水电,制备出来的氢气就一定是绿色的。
田桐:
所以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绿氢。中国行业研究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加氢站将建成1500座,2050年全国氢气需求量近6000万吨,每年经济产值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在国家氢能蓬勃发展的当下,你们的愿景是什么?
李辉:
我们希望绿氢科技创造零碳未来,我们目标就是要成为全球最领先的绿氢科技供应商,至于说是两年实现还是三年实现,我觉得我们正在路上。
绿氢科技创造零碳未来
“Tech Tone
田桐视角
“我们正在路上”——李辉教授这句话,朴实,却掷地有声。
在能源领域,技术发展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会引发新的产业革命。薄薄的一片膜,竟然能让绿氢成本骤降1/3,这又再一次印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作为桐频TTone第一季的收官之访,李辉教授氢辉能源这一期的技术深度,对我和团队而言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不过,我的角色只是记录者、转述者。真正直面科研和产业化实践中每一次困难和考验的,是本季接受采访的朋友们。
谢谢本季所有的“探路者”。在充满挑战与未知的征途上,感谢你们不断突破技术的疆界,重塑我们共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