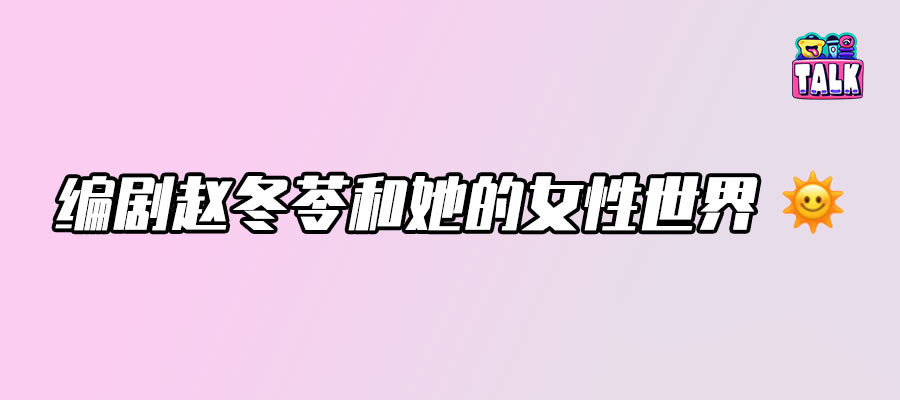
作者 / 耳东陈
编辑 / 朱 婷
运营 / 狮子座
在中国影视剧的创作版图上,编剧赵冬苓绝对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从《红高粱》里野性难驯的九儿,到《幸福到万家》中倔强维权的何幸福,她的女性角色总是带着一股“不服”的劲儿,既扎根于泥土,又试图冲破枷锁。
而当她的笔触划过悬疑赛道,《沙尘暴》中“全员恶人”式的女性角色群像又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从杀丈夫烧房子的王良生母琴,做暗娼的程春,再到设计指使丁宝元杀人顶罪的孙彩云,被父亲兄弟毁掉前途孤注一掷复仇的刘盈盈,这些女性用近乎自毁的方式上演了一出“中国版绝望的主妇”的故事。
身为资深电视剧儿童,有时候难免感慨:赵冬苓,不愧是写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女人!
从《母亲,母亲》到《沙尘暴》,赵冬苓笔下的中国女性都具备一种“地母性”,她们不是完美的“大女主”,也不是被动的受害者;既具备中国传统美德中的温良恭俭让品性,又有超越时代的独立精神;既是在历史的洪流中盘桓的群体,也是在历史夹缝中真实呼吸的个人。
一、赵冬苓笔下的女性角色:生活里的“幸存者”
当下的影视市场,流行两种极端的女性形象:要么是“圣母型”完美女神,要么是“黑莲花”复仇爽剧女主。当行业还在用"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糖水剧情收割流量时,编剧赵冬苓笔下的女性早已在战火、法庭、商海中杀出血路——我们顶半边天的妇女啊,终于能痛快角逐“铁王座”了。
从《沂蒙》里扛起革命大旗的农妇,到《无所畏惧》中单挑男权社会的律政新人,赵冬苓的女性群像如同手术刀,剖开了转型中国的隐秘伤疤。她笔下的女性角色,拒绝被时代洪流淹没,而是主动在历史的褶皱里开辟自己的路。
在传统叙事中,女性常常是历史的“旁观者”或“牺牲品”,但赵冬苓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女主角,往往是历史变局的“搅局者”。
《红高粱》里的九儿,就是一个典型。她不是等待拯救的弱女子,而是在土匪、日军、家族利益的夹缝中,用智慧和胆识周旋,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她的生存哲学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这句粗粝的台词,恰恰道出了赵冬苓笔下女性的核心特质——在绝境中,她们总能找到一种“野蛮生长”的方式。
再看《中国地》里的赵妻,同样如此。抗战背景下,男人在前线厮杀,而她守护的不仅是家庭,更是一个村庄的魂。她的坚韧不是口号式的,而是体现在一粥一饭、一针一线的细节里。她擅长用日常去解构宏大,让女性在历史的“缝隙”里,成为真正的主角。
赵冬苓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游走在善恶之间,充满人性的矛盾与灰度。矛盾和灰度背后,是父权和夫权对女性的蚕食和压迫。
《猎狐》里的杨建秋和于小卉成为经济犯罪的牺牲品,前者是被迫过早承担起家庭顶梁柱的责任,供哥哥读书,给爸爸治病;后者是被爱情冲昏头脑,成为罪犯的帮凶。这剧中的女性与《沙尘暴》中的女性群体有异曲同工之处:女性在家庭中的权益被父兄夫蚕食,偏偏个人又争气,为挣脱牢笼却不曾想一步步踏上不归路。
这里kk不是为罪犯洗白,而是编剧笔下呈现的女性犯罪者的命运不得不令人追问犯罪的成因。罪有应得无可厚非,而令人痛心的是,谁偷走了她们原本应当大好的人生?好的“反派”女性,不是用来衬托正义的工具,而是一面照见社会病灶的镜子——她们的堕落,往往始于无人听见的呼救。
许多“大女主”剧喜欢用“逆袭”套路:遭遇背叛→突然觉醒→大杀四方。但赵冬苓的女性角色,往往是在一次次跌倒、爬起、再跌倒的过程中,缓慢地找到自己的方向。
《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就是一个典型的“慢觉醒”角色。她从农村媳妇到法律意识觉醒,不是靠一场演讲或一次打击,而是在无数次不公平的遭遇中,一点点学会抗争。她的成长,不是“爽剧式”的,而是充满反复与妥协。《安居》里的城市女性面临拆迁,同样如此。她们在利益与情感间摇摆,既想争取权益,又怕伤了邻里情分。赵冬苓没有让她们轻易做出“正确”选择,而是展现这种抉择的痛苦。这种“慢叙事”,反而让女性角色的成长更有厚度。
赵冬苓的剧本,之所以能跨越年代依然打动观众,正是因为她的女性角色不是“工具人”,不是符号化的“独立女性”,也不是被消费的“苦难样本”,而是有血有肉的“幸存者”。她们在历史的夹缝中求生,在道德的泥潭里挣扎,在漫长的跋涉中寻找自我。
二、为什么是赵冬苓?
女性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女性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如何对待它的每一个人的故事。
赵冬苓塑造的女性角色,某种程度来说,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晴雨表”。她们从被动的“家庭角色”逐渐转变为主动的“社会角色”,这一过程恰恰映射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反复研究她的创作,kk发现本质上她是在用女性命运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红高粱》《中国地》等作品中,女性角色(如九儿、赵妻)的生存环境,仍然深受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她们被期待成为“贤妻良母”,但历史的动荡(如战争、饥荒、政治运动)迫使她们走出家庭,承担起原本属于男性的社会责任。 当社会结构崩塌时,女性往往最先被抛入历史的洪流,却也最先被迫学会生存。九儿的泼辣、赵妻的坚韧,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乱世中求生的本能。
《北上》中的夏凤华、《无所畏惧》中的罗英子,则反映了市场经济时代女性追求的变化:我想要什么。这种变化背后,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人主义思潮。女性不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单一身份,而是试图在事业、爱情、自我价值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塑造方式,暗合了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的兴起——女性不再是被动的“被拯救者”,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但从她笔下的女性命运中也不难看出,这种觉醒往往是缓慢的、充满反复的,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
赵冬苓笔下的女性角色,是中国女性从“他者”到“主体”的意识觉醒过程的艺术呈现。在《红高粱》中九儿的情欲自主、《幸福到万家》中何幸福的法律维权,都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
赵冬苓没有让她们成为“完美国女”,而是允许她们有欲望、会犯错、敢反抗。《沙尘暴》中的“恶女群像”、《猎狐》中女性犯罪群体,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当女性试图用男性规则(暴力、贪婪)去反抗时,反而可能陷入更深的异化。
她的角色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她们不是抽象的“女性象征”,而是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人”。从这一角度看,赵冬苓的女性叙事,已经超越了性别议题本身,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
三、赵冬苓的高产和不可复制
当韩剧女编剧已到next level 的时候,我们的内娱还在期待年逾古稀的女性编剧仍能保持“高产”(据坊间传闻,赵冬苓年产量能到达惊人的150集,其本人也在公开采访中提到,至今仍保持着近乎全年无休的状态,要么写作,要么采风),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赵冬苓聊《沙尘暴》:在荒漠刑侦叙事中打捞那些被现代化进程“吞没”的人|Talk对话
而“以妄为常”的整个内娱编剧生态到底还将持续多久,没人知道。
赵冬苓能坚持自己的风格,部分源于她早已确立行业地位,但大多数女性编剧面临更复杂的文化桎梏:行业默认男性编剧擅长历史、权谋、战争等“宏大叙事”,而女性则被期待写爱情、家庭等“微观表达”。
以《因法之名》为例。因为剧中涉及司法冤案等情节,这种“烈度”的呈现,大概率只能由有名气、有地位的编剧完成创作,否则极有可能在剧本阶段便面临夭折。而如今平台对项目的预算上,如遇新人编剧,更恨不得把编剧预算卡到最低——牛马尚要吃草,编剧喝西北风能活?“登学冲击”和“经济压制”双管齐下,妙啊!
再加上,商业影视的流水线生产,挤压了严肃女性叙事的生存空间。即便是赵冬苓本人,恐怕也难以再现《红高粱》《幸福到万家》等经典作品,并非创作遭遇瓶颈,而是这类作品创作往往需要长期打磨,深入历史或社会调研,但当前国内影视行业更倾向于“短平快”的商业模式,像赵冬苓这样坚持现实主义、深耕女性命运的作品,在商业上未必能迅速变现,导致行业更缺乏培养此类编剧的土壤。
再加一条,主流奖项、行业话语权仍由男性把控,女性编剧的严肃作品常被归类为“女性向”,难以进入“正剧”范畴。当《好家伙》被当成“坏东西”,《热辣滚烫》被叫做“减肥片”,有时候就不得不悲痛欲绝地认命:希望如赵冬苓一样有名有位的女性创作者能再坚挺几年,观众还能再吃几年细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