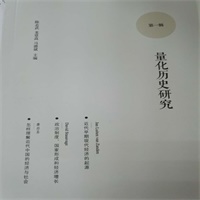(图片来源于网络)
1945年3月,日本鹿儿岛市的步兵第145联队被派往硫磺岛。当美军登陆时,这支部队接到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命令,2727名士兵仅有162人生还。五个月后,广岛原子弹爆炸,市区90%的建筑化为废墟。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投降时,这座城市的24万人口中已有超过14万人死亡或失踪。
两场悲剧在战后日本形成了两条平行的政治轨迹。广岛成为和平主义的象征,其市民组建的“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会”至今反对修宪扩军;而鹿儿岛则长期是自民党的拥护者,支持通过修宪摆脱“战败国宪法”的军事束缚。这种差异引出一个重要问题:战争中的军事伤亡与城市破坏会如何塑造一个民族的政治选择?
哥伦比亚大学井上静香等三位学者在NBER发表的工作论文“Martyrs,Morale,and Militarism:The Political Impact of Devastation and Slaughter”通过分析1958-2021年的选举数据与战争创伤的空间差异发现:军事伤亡多的地区在战后成为自民党修宪扩军的铁票仓,而遭受轰炸的城市却孕育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这一分裂的政治遗产持续影响了三代人。
一
日本政治的军国主义发展
国家安全是日本近百年来的核心政治议题,不同党派围绕是否实行军国主义,是否利用军事武装力量对外扩张展开了长期的争议和行动,这为研究战争后果如何塑造政治态度提供了历史实验。
1925年日本实施成年男性普选后,国防问题成为选举焦点。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领导的政友会主张“普及国防思想”,以反对军备控制为纲领赢得1928年大选。后来田中内阁因陆军刺杀张作霖事件被迫辞职,民政党上台期间签署了限制日本海军发展的《伦敦海军条约》,政治短暂倾向和平主义。然而,政友会于1932年再次掌权,并于1936年废除条约,日本走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
二战结束后,美国迫使日本修订新的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要求日本放弃战争,并禁止日本维持武装力量或使用武力解决争端。这一结果引起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不满,原政友会成员组建自民党,以修宪和重新武装为核心目标。其代表人物岸信介称修宪是“恢复国家地位”的前提,认为拥兵可摆脱驻日美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则反对修宪,维护和平宪法。
自民党在战后获得国内选民支持,长期执政,并一直秉持亲军事(pro-military)立场,98%的成员要求修宪。其支持者在加强日本自卫队等重要军事议题上也更加激进,反映出政党立场与选民认知的高度契合(见图1)。
图1 日本自民党及其支持者对重要军事议题的政治态度变化
注:左右列分别为日本自民党政治家和其支持者在重要军事议题上的态度变化,议题从上至下为加强自卫队、修宪和参拜靖国神社,纵轴刻度1-5表示非常同意到强烈反对。
1993年日本股市与地价泡沫破裂后,自民党选举失利,反对党趁机联合执政并于1994年改革选举制度。新的选举制度使得以前无法在任何选区赢得席位的小党派,也有机会在多个选区获得足够选票的情况下成为国会议员。这削弱了自民党的主导地位,迫使其与日本社会党、公明党等和平主义政党联合执政,修宪计划也受到阻止。这场因经济危机而推出的选举改革提供了检验选民态度变化的自然实验。
二
二战的军事伤亡和城市破坏
二战期间日本的陆军招募采取家乡联队制度(hometown regiment system),军队按士兵籍贯组建联队,随机派遣战场。这导致不同地区的军事伤亡呈现明显的随机性,例如派往菲律宾、硫磺岛的联队死亡率近100%,而驻守台湾、朝鲜的部队却鲜有伤亡。此外,战场选择的战略需要和军事风险也与士兵籍贯地的政治倾向和经济水平无关, 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由于士兵阵亡数缺乏统计数据,作者使用日本1950年20-44岁的性别比(女性人数/男性人数)作为代理变量。自然情况下,女性数量要略低于男性,这一比例约为0.943。然而战争期间军事伤亡严重的地区,如鹿儿岛,其性别比高达1.17,意味着因为战争失去了1/4的青壮年男性。
与军事伤亡不同,城市破坏主要是因为美军的空袭和轰炸。作者使用人均建筑物毁坏数量作为城市破坏的代理变量。空袭受天气因素影响强烈,轰炸机需要考虑风力、云层厚度等自然条件投放炸弹,因此作者假设不同城市的破坏程度也是外生的。
三
实证分析和结果
作者根据1940年日本300个最大的城市构建了战争后果和选票分布的数据集,自民党的得票率反映了选民亲军事态度的强弱。作者将1955-2021年期间的自民党得票率和1950年性别比、人均建筑毁坏数量分别回归发现:前者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性别比越高,即军事伤亡越严重的地区,越支持自民党;而后者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人均建筑毁坏数量越多,即城市破坏越严重的地区,越反对自民党。
为了进一步比较军事伤亡和城市破坏的差异化影响,作者将二者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并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图2展示了1950年性别比系数的时间变化。可以看到虽然系数在1994年选举改革后大幅下降,但始终显著大于零,说明军事伤亡促使选民支持亲军事的自民党。
图2 1950年征兵队列(20-44岁)性别比对自民党得票率的影响
图3展示了人均建筑毁坏数量的系数变化。可以看到与军事伤亡相反,该系数始终小于零,意味着经历更多轰炸的城市选民对自民党的投票倾向更低。这表明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促使选民更倾向反军事的和平主义。
图3 人均建筑毁坏数量对自民党得票率的影响
1994年的选举改革同时削弱了两种战争冲击的效应,这一现象加强了实证的可信度。当自民党因结盟不得不放弃强硬军事立场时,其核心票仓立即惩罚了这种“背叛”,而原本就倾向和平主义的选民则乐见其政策转向温和。
尽管自民党执政已有数十年,但日本至今未能成功修宪。因此,作者设计了一个反事实模拟来推测城市破坏所带来的强大和平效应。具体而言,作者假设如果美军只在战场上实施军事行动,而不轰炸城市,那么日本能否完成修宪?根据作者的计算,在无轰炸情境下,日本在1960年的自民党议席会增加17位(当年自民党实际席位296位,仅差15位达到修宪门槛),刚好达到修宪要求的三分之二,这意味自民党早在60年前就可能达成修宪目标。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作者做了三组测试。首先,作者检查了军事伤亡的效应是否由特定年龄群体所驱动,在回归中加入了其他年龄组的性别比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只有20-44岁年龄组的性别比显著增加了自民党得票率(见图4),这表明只有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的士兵伤亡才可能影响选民的军事倾向。
图4 不同年龄组性别比对自民党得票率的影响
其次,由于城市破坏同时带来平民死亡,这可能会产生与军事伤亡类似的效应。作者在回归中同时加入人均建筑破坏数量和人均平民死亡数量发现,前者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而后者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城市破坏导致的和平主义倾向主要来自建筑等物质层面的破坏而非普通人员伤亡。
最后,作者排除了选民支持自民党是为了获取退伍军人福利的解释。由于日本共产党和自民党同样支持退伍军人福利,但反对修宪,因此日本共产党的得票率可以用来检验选民的经济动机。回归结果显示,军事伤亡高的地区,日本共产党的得票率更低。这说明选民更重视政党的意识形态而非经济利益,自民党是因为其亲军事立场才得到二战期间军事伤亡严重地区的选民支持。
五
总 结
1943年,美国国会议员弗雷德·布拉德利在演讲中宣称:“日本本土可以被彻底、高效、迅速地轰炸到屈服。”他不会想到这句预言不仅成真,更在70年后仍然塑造着日本的政治走向。那些在战火中死亡的士兵,依旧影响着人们支持军事和战争;那些被夷为平地的街道与房屋,则凝固成了宪法里的和平。
文献来源:Inoue, S., Weinstein, D.E., and Yamagishi, A., 2025, “Martyrs, Morale, and Militarism: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Devastation and Slaught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842.
轮值主编:林 展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