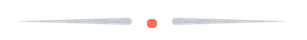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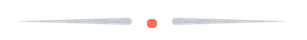
第二期的特征与表达开始模仿真正的人脸。当然,这种特征只是相对而言。僧人的开脸决不能看起来像凡夫;第二和第三期雕塑的中国作者在处理抽象的佛、菩萨彼岸世界和次要存在的人物现实之间是有区分的。但和第一期相比,第二期的开脸还是显得更加丰富细腻和圆润,古典式微笑的痕迹更少,对眉毛、眼睛和鼻子、嘴唇的处理更加小心。同时,图像开始慢慢地有生活气息。
作为原则,我们能察觉的是,图像开始逐渐远离姿势的僵硬感,其中一只腿的紧张有所松弛,于是整个身体的弯曲着力于臀部,腰部朝一个方向弯,肩部则向相反方向靠。这是印度雕塑者经常使用的三屈式姿势。但直到第三期,中国雕塑者也不能完全用印度的视角来观察和创作。中国雕塑中,从来没有作品能与印度的那种有意识的舞步姿态感相比,印度雕塑中的较少拘谨的作品中则常见。第二期雕塑很少暗含Siren所描述的那种有节奏律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图30的这种作品,其“流线缓缓滑动,平衡感超凡,起伏均匀”。
图30
所有这些特征在天龙山的白色砂石洞窟雕像中都随处可见。该洞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的数英里。这一大师级作品于北齐开始建造,唐代和唐以后还有继续。天龙山的印度佛像特征很明显,正如Siren所说,印度的雕塑者或许就在那里参加过塑造,这里的洞窟内容代表着中国佛教第二、第三期雕塑最为前卫的部分。
图28b展示了天龙山最古老的作品之一,位于第三号洞窟的西面墙壁,时间为560年。简洁和有秩序感的雕塑排列特点突出。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的三位佛是北面墙壁的中心图像,东面墙壁则是阿弥陀佛,西面墙壁是弥勒佛为中心的三佛。有些装饰性人物以浅浮雕表现,墙壁和天花板曾经彩绘过,颜色鲜亮,而且此处严谨的排列与云冈石窟以及龙门石窟第一期的杂乱无章排列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主要图像的雕塑,从第一期的标准来看属于令人惊讶的高浮雕。衣服的表现仍然属于线性,但褶皱比以前的处理要深;褶皱边以及下摆仍然像翅膀羽毛那样突出,但整体的面貌要柔和得多,浑圆得多,所以其情感色彩的张力有所减弱。
往期文章链接:
处女翻译·429《中国艺术》(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