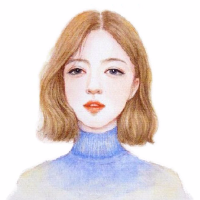看完片子,窗外天空中飘起了雨丝,朋友问我,你想到一个词语来形容吗?我说,你的呢?他说,这是一个讲失缺的故事。
我想这是一个伤感但是不绝望的故事。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一个缺失的世界,我们在其中,如何观看自我,如何修复或者是带着缺失继续上路。
城市里有高高低低的楼,一览无余的阳光照耀之下,有闪闪烁烁的影子与破碎的阳光。
这是一部没有废话的电影,就像平日里沉默如金的男子,有时候他的话你需要在心里几番流转。再一次看,提前知道了一个本没有悬念的故事,你没有了惊奇,更多的是留意细节以及转念一想的细细的微笑。
酒好喝,正是因为它难喝。刘正熙说这句话的时候,原来正是他和她的一个开始。
层叠交错的高架桥,糜烂明亮的城市的夜光与尾随的车灯,追逐罪犯的阿邦,恰好路过了一场车祸,原来正是这一场车祸使一个她与另一个他阴阳相隔。
原来,身边的人有一天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竟然是这么的可怕。
阿邦的白衬衫,鲜红的血迹。
他回家时候准备好好的从新开始,窗外的天空已经泛白,阿邦的女孩没有给他机会。你不知道她为什么就选择了放弃,一个同床共枕五年的人,你像陌生人一样看到她在酒吧里等待,却不知道她为了什么而选择了放弃。
你接受了他人的给予,你也给予了他人你的接受。
她在你们的墙上画一个哭泣的女孩,在锁骨上添上两只流泪的眼睛。
如果她真心爱的等待的是在高架桥上男子,一个失约的约会是促使她死亡的因果吗?
我想丢失的不是信任不是希望,而是纯朴。人与人之间,简简单单的相处。
厨房的瓶罐后面躲着正熙每天给淑珍放的安眠药,淑珍每天自若明了的吃下他放的药。暗房的开水杯后面躲着淑珍的威士的。她喝完威士的,然后喝下他送来白色杯子的水,然后抱着靠枕在乳白色的沙发里睡去,然后她的丈夫把她轻轻唤醒,她轻轻的笑出来,:“大概是太幸福了吧。”
本来他与她之间,是夫妻之间温和平淡的相处。
我们也许可以选择我们的死亡,但是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生。生活在我们的面前铺开五色大道,似乎有无数的可能,但是你走的永远只是一条路而已。
淑珍可以与父亲在席间不发一语。她十八岁离开大屋子,她不知道她的父亲。一个曾经不眨一眼杀戮正熙家人的毒枭,在妻子离世后,隐居在香港,是一个不敢给陌生人开门的老人。
那个管家的柜子里挂满了衣服,貌似平静而劳累的养老的日子,是他曾经做一个警察时曾想到过的吗?或者他收取与杀戮之时的畅快想得到的是这样的日子吗?
一把进门后不输入密码一分钟后就自动报警的门锁。刘正熙本来被关在这扇门外的。他选择在新婚之后,与岳父大人一面之后径直跨过那扇门。他眼神坚定,没有丝毫的犹豫,他选择用佛像头作为最后一击的武器。
刘正熙非常幸运非常不幸逃脱了灭门的惨案,有时候我在想,他以前的生活未必是欢喜,悲惨的也大概不是一夜之间的一无所有,你让一个孩子去承受从极大欢愉直坠到血与火的直面观视。这样的落差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一个孩子半夜里长久的恶梦。
刘正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不,应该说是陈伟强,真正的刘正熙是一个有着小肚腩一家餐馆的主人,曾经四次拿走校际乒乓冠军,惟独在1978年输给了陈伟杰。陈伟杰是多么的雀跃,拿着奖励的新球拍欢奔回家。
一个礼拜之后修女发现饿晕的他,修女问他的名字,他随口而出的是他家人永远不会知道他战胜过的刘正熙。
他是个假面人吗?一个让阿邦引以为朋友知己的多年老友,每周一次的见面,这样的交往中他都是一个冷静而温和的戴金属眼镜的男人。这样的他不是真实的吗?
我对朋友说,戴着眼镜他是刘正熙,放下眼镜他是陈伟强。
他用三十年的时间自以为布了一个完美的局,他迫不及待的走进去,以为这会是一种彻底的结束。所以阿邦就幸运的多,他遇到了一个啤酒女郎也许她不聪慧但是她会含着棒棒糖对你微笑。纯真与温暖,也许是疗伤的良药。
淑珍也许正是他需要的那帖药,她温和知性,聪敏而清澈,最主要她爱他,所以无条件的保护他最为重视的一个乒乓球拍,即使大火蔓起。
朋友说,如果他给予双方更多的时间,也许悲剧可以避免。也许这是一个可能,但更大的可能大概只有他直面了对她的伤害之后,他才会恍若醒来。一个人三十年所有的执着只是为了一个目标,他必须走到那面南墙之下,撞破了他的鼻子,他才会觉得原来除了墙,还有痛,还有别的,譬如爱。
我始终固执的相信,医院里不分昼夜的服侍是他对自我的救赎。他流下的眼泪,他对阿邦说,她是不是谁的女儿已经不重要了,她是我的妻子,与我的爸爸妈妈,妹妹奶奶一样,是我的亲人。
淑珍醒来,两个人的相望,我一直爱这个细节,那时候的他已经是温和的陈伟杰,就像尘世间等待着妻子醒来的丈夫。她爱他,他接近她只是为了要杀害她的父亲。我想,这是她不能触及最大的伤痕,即使面对他对她爱的肯定,她依然连死都拒绝戴上结婚戒指。
他死之前,重新给她戴上了戒指。
如果,我说如果,淑珍给双方再一点时间,或者上天再多留一些日子给两个受伤的心,他们会不会在救赎中相互的取暖与修复呢?为什么一切都在死亡中嘎然而止了呢?大概命运永远不会给予我们答案,我们只能在其中不停思索。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忽然想起胡兰成先生的半句话:故乡白云天涯,村前马樱花。
花开花落,有人在树下讲一个故事,有些人觉得他听懂了,有些人在揣测讲者的隐含,有些人在否决有些人的揣测,这只是一个故事,重要的是你与你想一起看的人一起看了故事,这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