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是自由职业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你还没有小孩,就要躺平当家庭主妇吗?”
去年八月从餐饮大厂离职后,可颂给各种纸刊和品牌供稿,一边旅游一边工作。尽管她的月收入已经是原来的三倍,但在部分长辈和同龄人的眼中,这种接单结账、没有固定单位可托底的“打零工”生活,依然叛逆而脱轨,直到可颂拿出有自己署名的纸刊,大家才认可这份工作。
数字游民的概念,最初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借助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一些人可以不受地理位置限制,进行远程工作,在保持一线城市收入水平的同时,享受更低的物价和更闲适的日常生活。近年,法国、意大利、泰国等40多个国家都推出了数字游民签证,无需流水和在职证明,只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就可以丝滑进入当地生活。
近半年,这一小众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大众认知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这背后,经济形势的变化既影响着社会气氛,也直接刺激零工经济人群的增长,在离职博主、县城热等社交网络热门话题背后,数字游民也作为一条隐线出现。
这种充斥着不确定性但又充满自由诱惑的生活,吸引着越来越多都市打工人成为数字游民,他们通常在山清水秀的宜居城市居住或旅游,以一线城市的工资支付二三线城市的房租。在B站,一些UP主自称旅行青蛙,在视频中带领观众了解一些非主流小城的生活环境、物价水平。
很多低线城市、一线城市郊县,以至于乡村开始将数字游民社区作为吸引年轻人的新标签:云南大理、安徽黄山、四川成都、上海金山等地兴起了一批线下的付费数字游民聚居社区,它们大都建在郊区或村落里,而这些数字游民们既在当地付房租和消费,又有收入来源维持消费循环,甚至逐渐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今年,许多数字游民社区所在地的政府纷纷提出要打造数字游民友好型城市,例如浙江安吉县就表示,要在今年7月全面打响“乡村创业首选地”品牌。
主动“脱轨”
在深圳的跃林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远程工作。
从需要坐班的头部房地产公司辞职,跃林跑去给一家广州的公司从0到1策划内容IP,得益于此前的招商和策划经验,她和老板谈判,最终争取到留在深圳远程工作。
干了两年播客,和老板理念不合,跃林又离职了,跳槽到旅游业外企的中国办公室,负责高端邮轮的市场营销,月入两万多,只需按时在线上交付工作。
这家外企成立于1991年,自那时起,全球各地的办公室就是远程工作模式,现在,大家全靠办公软件Teams和飞书在线上沟通交流。搬家、旅游等不用向上级报备请假,“要不要跟同事们说这些情况,全看私人交情如何,大家的个人动向都不是很重要,按时完成工作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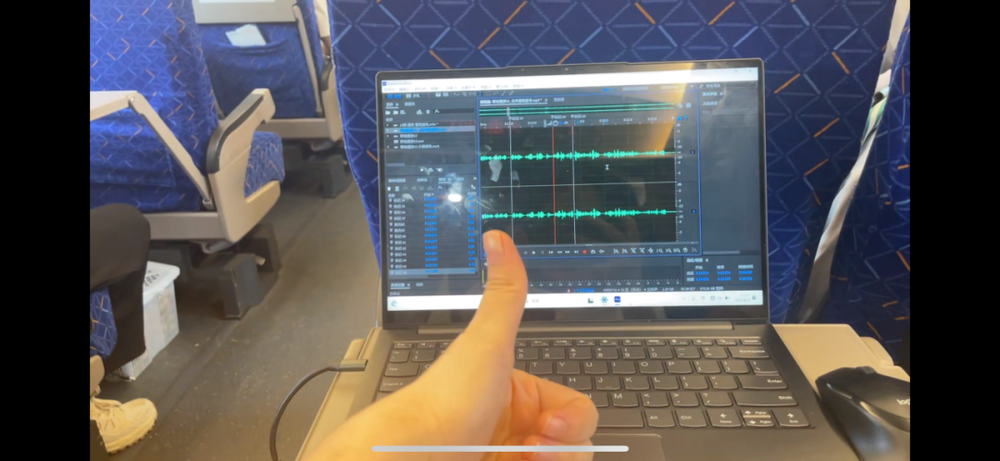
跃林在高铁工作时
跃林已经带着工作去了敦煌,又去了贵州,没跟老板说,老板也不会主动过问她现在的地理位置。
这其实就是《Digital Nomad》一书中,在1997年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预言:未来的人类社会依靠wifi和移动设备来实现工作生产,一个固定的工位不再是必需品,像游牧民族追逐季节而四处流动一样,这些追逐着信息而生活的人们是数字游民。
如今,数字游民的界限被不断扩宽,在全职远程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多的细分职业如撰稿人、插画师、疗愈师等,遵循着出售专业技能、自主寻找客户、按项目结算的“零工式”工作方式——总要卖点什么,文章也好,修鞋也罢,都是用技能获得报酬,形成一个人经营一家“小公司”的业务链条。
可颂就这样吃上了写作的饭碗,有一段时间,她懒得再向别人一遍遍自证,每当有人再好奇地问起,她都简单回答:“我是卖字的。”
刚毕业的时候,汪曾祺在《四方食事》里的一句“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就让她从共青团转到长沙晚报,又继续转型到新媒体做美食文案,进入餐饮公司做写作相关的外宣工作,最后离职成为了一名到处旅行、写作谋生的数字游民。
可颂在各个场景工作
外宣几乎没有周末,节假日也被工作包围,可颂和家人总是不能一起吃饭。有一天,她发烧请假,出门散步时,才发现原来小区里还有秋千。
本来,离职只是心里的一个小苗头,可颂曾经担心过,离开了现在的公司,一个30岁的已婚女人还能在当地找到更好的工作吗?直到爷爷在夏天生病,领导却拒绝了她的请假申请,并回复“除非病危,才能请假。”她下定决心辞职了。
抛却看似稳定的工作,去拥抱另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可颂不是孤例,只要在社媒上搜索“辞职”,成千上万的帖子都在述说类似的故事:几乎没有人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自由职业,基本都在经历了一段全职工作的生活后,难以忍受职场压力和公司制度,辞职后,为了生存,在将自己的技能变现的过程中,慢慢走上了自由职业的道路。
甚至还有人在比对了同等收入下的不同压力后,总结道:“自由职业月入一万等于打工月入五万”,收获了不少共鸣。
一人公司
2024年,社媒最拥挤的赛道当属离职博主。“妈妈,人生是旷野”的金句带动一批又一批标题“大厂裸辞自由高效一天”的vlog收获百万浏览量,这些视频里,大家最关心的是博主本人吃了什么,穿了什么,去哪个咖啡厅打卡,并跟随博主的推荐,下单打卡同款体验。
一个人、一台电脑所能撬动的能量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短时间裂变,自由职业中“技能变现”的基本属性让大家得以抛开各种繁琐的外部因素,以个人能力接单赚钱。
可颂还在职的时候,给民宿和杂志写稿是她的爱好和副业,离职后,在法国旅行的路上,她的朋友在朋友圈刷到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招募信息,有一本杂志需要一位写风景游记类的作者,于是,可颂以巴黎为主题,在葡萄牙写完了她的第一篇自由撰稿作品,此后,不断地有品牌和杂志找到她,希望能合作撰稿。
可颂的爸妈在体制内工作,最初并不理解她的选择,要求她在35岁之前考上公务员。直到可颂把发表的文章转发进家族群,把署名的杂志邮回家,两位长辈才开始逐渐地理解可颂的工作——在60年代生人的眼里,上杂志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杂志上,可颂在巴黎蓬皮杜看展的照片
如果可颂的文章是一件商品,那么一件商品诞生和推广乃至销售的全链路,比如和编辑对接、写稿、发布跟进等,全由可颂一个人把控负责,这和创业的底层逻辑很像,因此,她的亲戚里,做过生意的人最能理解自由职业到底是什么,无非是当个一人公司的小老板,只是不挂证,不招员工。
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可颂认识了一对80后夫妇,上海本地人,从事设计行业多年,现在自由接单,奢侈品、汽车等都是他们的客户,一个项目能赚三十到五十万不等。这对夫妇甚至还雇了几个在线上工作的人,如果项目时间和旅游有冲突,他们会把项目再分包给其他人。
他们的80后邻居们,也有像可颂一样的自由撰稿人,之前在国际广告公司工作,离职后,背靠前司的资源,也可以接到很多撰稿需求。
“我爸妈现在觉得这份工还蛮好,又能赚钱,又能有自己的时间,”可颂回忆,“只是偶尔也会念叨一下,工作不稳定,老了怎么办?”
跃林的父母觉得女儿现在的工作“很爽”,但她却发现,远程工作久了,自己像一座孤岛。“我没怎么见过同事们,中国区的员工们也都只在出差时碰个面,一年一两次。”这种极具边界感的工作模式带来的职场浅社交,既让全职坐班的朋友们羡慕,又让跃林每天只对着电脑工作,一天见不到一个活人。
跃林工作时
为了保持跟社会之间的链接,从传统职场主动脱轨出来的跃林又主动走进了各种线下社交场域,比如打羽毛球、见朋友、建一个深圳的远程工作交流群,她每天都会为自己安排社交时间,会去朋友的办公室工作一天,“最起码要跟别人有互动”。
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的社交需求,但不能完全根治。
文旅新标签
大曹曾经先后三次来到大理。社媒上,大理一直是数字游民们的快乐老家,宜居、物价便宜、房租低。年轻人前仆后继地来这里,花三千旅居三个月,甚至,还能兼职卖水果、卖花、做运营等各种活计挣到额外的生活费。今年,大理州政府开始打造“数字游民”联谊会,并计划引入“数字游民”创业孵化器。
某种意义上,大理已经成为了“数字CBD”,行走在大理,大曹才把之前隐约听说过的“数字游民”真正具象化。她开始像前辈们一样,利用之前的项目经验,接单做品牌营销相关的项目,还把自己住的小院子改造成朋友聚会的据点,来小院聚会的都是拥有一份或多份远程工作的朋友,这就是NCC社区的雏形。
NCC活动现场
仅一年半时间,NCC社区在大理和黄山稳定经营,还通过发起“共居联合计划”,与杭州、西安、莫干山、清迈等20座城市的线下社区合作,跨界、跨年龄到了养老业态,让数字游民在全国和更广阔的范围内流动。
“在北京,大家都活在各自的信息茧房里,虽然城市很大,但真正和你有关系的人很少,在数字游民扎堆的社区,尽管地方不大,但在短时间内能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借鉴别人的职业经验。”
让一个一个孤岛们连接起来,同时为县镇乡村这些“失落的一角”带去创业活力和资金,就是数字游民的线下社区模式能一直持续的原因。
2021年,浙江安吉的溪龙村出现了国内第一家游民社区“DNA公社”,2022年7月,安吉县余村启动了全球合伙人公开招募计划,由天荒坪镇政府主导,围绕新经济、新农业和新文旅三大类型招募创业者和机构企业。DNA公社原班人马打造的余村数字游民公社(DN余村)以政府采购项目落地。
随后,以“共聚共创、创业孵化器”等为标签,云南大理、北京、成都、乃至鹤岗,各种各样的游民社区们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今年8月底正式营业的上海金山区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还顺应免签的政策,打出了邀请国际数字游民体验入驻的口号。
为什么数字游民们可以盘活乡镇的经济活力?全球数字游民中,青年群体占据58%;打造了DNA公社和DN余村的许崧团队的调研中,在这两个社区居住过的63%为90后,本科学历59%,硕博学历30%;在NCC社区主理人大曹的观察中,这类人群对市场风向敏感,拥有专业技能,且愿意追逐新事物。
也就是说,一群愿意冒险、可以变现的青年群体来到乡村,带来了新的业态。比如,2022年,安吉县的梅溪镇红庙村党委和7位大学生创业者就把废弃的水泥厂改造成了“深蓝计划x”咖啡店,运营至今,小红书上有关该咖啡店的帖子多达两万条,至今还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前去打卡,顺带逛一逛红庙村。
和安吉重视数字游民相似,作为安徽黄山的第一家数字游民社区,NCC也经常会迎来本地的媒体和电视台关注报道,慢慢地,大曹也被邀请加入一些行业交流会,比如乡村建设、城市更新、社区制度的会议等。
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启发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项目。
在黄山黟县的NCC社区正式开放两个月后,到此旅居的保险经理人颜珣被52岁的社区成员启发,想要在附近做一个与老年康养休闲相关的“乐活旅居”。目前,NCC已经两次邀请老人们到社区来体验生活,称为“老年体验官”,这些老人们有的刚退休,有的来自高知家庭,孩子已经出国不在身边。
“大家聊天的时候,这些老人才凑过去一起听,”大曹介绍道,“他们还会希望大家别歧视自己,不要觉得带着自己很麻烦,也尽量不给大家产生麻烦。”
老年群体需求与一个以青年为主流的社区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化学反应,大曹和团队成员们还想过,如果把“乐活旅居”这个项目做成熟,都可以开一家真正的养老院——在这里,老人们可以自由地学钢琴、编程等各种技能,而年轻人们又可以和老人们交流来获取更多人生经验,看到更多的人生选择。
“相当于提前考虑了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老年问题,并把它纳入了现在正在做的社区事务里,我们也在反复探索老年和青年人在同一个社区里的人数配比。”并且,由于这一社区在黄山,而安徽黄山本身出台过建设世界康养旅居目的地的政策,未来的业务开展可能还会迎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营业两个月,黄山黟县的NCC社区成员来来去去,已经住过了将近一百人,目前,社区本身能容纳30多人同时居住,但还是住不下。NCC社区附近有一个老酒厂宿舍,大曹正在加速将其改造成社区二期的住宿空间,预计10月底完成。
近两年,类似清华文创院等各种大学和政府的相关机构都关注和发起乡村振兴的内容,即通过文化内容去改造乡村,近日,大曹也参与了由清华文创院发起的活动,梳理黄山当地的文旅发展。
当被问起,目前的状态是否与当时离职的设想一致,大曹回答:“很难直接描述,但怎么说都比上班强。”
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上班时,自己总是会以忐忑的心态面对社会压力,随时处于紧绷状态,现在她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尽管漏水、扯皮、人情关系等各种之前没接触过的事儿都蹦了出来,都需要大曹亲力亲为,但随着自己亲手一砖一瓦搭建出来的社区成型,和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当地发展的建设中,她已经不再焦虑,因为“现在已经更有能力去解决未知的困境。”
充满冒险和惊喜的世界正在她眼前徐徐展开。
作者:郭仪(长沙),监制:张一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