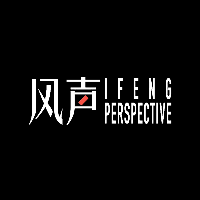作者|维舟
专栏作家
备受关注的胡鑫宇案,现在有了最新进展:从他遗留的录音笔中复原的音频来看,他两度表达了清晰的自杀愿望。虽然肯定还有人不愿意相信,但合理地推断,他最有可能的自杀动机恐怕是厌学之下的重度抑郁。
说起来,“心理问题”也不是什么新问题。然而,知道归知道,人们也本能地觉得这有什么地方不对,却往往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我也没天天快乐,但也不至于就去自杀吧?”
正因此,心理抑郁最大的问题就是其隐蔽性:那原本就是一种不可见的心理活动,如果孩子说出来你又不当回事,那他就更不愿意说了。结果便是,很多孩子在走上绝路之前,已经在黑暗中孤军奋战了很多年——自杀,乍看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其实只是这一过程的合理结局。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心理抑郁,究竟应该如何应对?都说“救救孩子”,那怎么救?孩子又如何自救?
胡鑫宇们为何会走向自杀的深渊?
实际上,受困于心理抑郁的,绝不只是孩子,谁没有时不时感到疲惫、焦虑、失眠、恐慌、无助、内疚、愤怒、抑郁?心理感受特别敏感的青春期学生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可能是最脆弱的群体。一年前,寻亲男孩刘学州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百多天前,江西学生胡鑫宇翻墙出校选择了自缢。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因抑郁而自杀的年轻人,都是“矿井里的金丝雀”,在向我们这个社会发出警讯。
当然,大部分人都不至于走到自杀那一步,但也受困于负面情绪,所谓“精神内耗”。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想得很多,但能做得很少,而这往往不是你不想做,而是可做、能做的太少,以至于个体像是身处一个逼仄处境中的困兽,不断焦虑地寻找出路,但内心反复思虑,仍然茫无头绪。
精神危机的蔓延,让越来越多的人面对着一个卡夫卡式的困境——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知道造成问题的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卡在这里、又怎样才能走出去。
这种困境很明显地也表现在了胡鑫宇身上,当10月14日他试图在宿舍阳台跳楼自杀时,录音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态:“说实话没有理由,只是觉得没意义,如果真跳下去了会怎样?不确定。”在五个小时后,他又用录音笔再次表达自杀意愿:“已经没有意义了,快零点了,干脆再等一下,直接去死吧,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已经有点不清楚了,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乍看是某种个人心理问题,其实是结构性的社会困境在个体身上的反映——具体到学生身上,可能是教育领域的极度内卷,也可能是家庭与学校等环境带来的身心受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之一,是把社会问题显化成为了心理学问题,由个体自行承担、消化。然而,如果不深入理解、进而去解决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仅靠个人实际上是无法解决这种心理问题的,会源源不断有人陷入同样的困扰。
为什么会陷入“精神内耗”?一方面是原有的各种社会共同体在不断加速瓦解,就像胡鑫宇的父母们为了养家糊口而外出打工,母子之间本该拥有的陪护等就缺失了;另一方面,陷入孤立无援的个体,想找到一个稳定的落脚点,又发现太难了。
根据案情通报可以得知,胡鑫宇在致远中学就读后,因学习成绩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上人际关系、青春期冲动带来的压力,造成了他的心理失衡,经常出现入睡困难、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等睡眠问题,还使他经常陷入内疚、自责、痛苦、无力无助无望感、无意义感等情绪问题,甚至连进食都会出现异常,存在着明确的厌世表现和轻生倾向。
试想一下,这就好像你落入汪洋大海之中,水流变幻莫测,不知道要把你带往何方,而你甚至看不见岸在哪里,既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游,身边也甚至都没有一块能救命的浮木,焦虑乃至恐惧是人之常情。
当新的一代人陷入心理挣扎
像这样的事,以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实际上,几乎每个社会都曾有过类似的。传统社会既保护了人,又束缚了人;现代社会则相反,既解放了人,但又让孤立的个体单独去面对所有不可测的风险。
一百年前的民国时代,当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第一批“新人”摆脱“家国天下”的秩序,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时,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为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高兴,而是一种深深的烦闷。那是一种“在经济上没有前途,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在思想上没有方向”的处境,因而在1920-30年代青年的文字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苦闷”二字,刊物中常有“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这一类字眼,他们不知出路在何方,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其实,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精神内耗”。
回到百年后的胡鑫宇身上,根据他失踪前的种种行为,可以想见他生前在校时的孤独感。尽管他在校在家都表现得非常懂事,但这种过分懂事有时反而容易给他自己造成反噬。
根据心理学家的访谈与分析,他“很在意他人看法。少与人做深入的思想情感沟通,情感支持缺失,缺少情绪宣泄渠道,常有避世想法”,尽管“随时随地在书本上记录自己情绪、想法的习惯”,但仍然没有逃离自杀的深渊。
一百年前的苦闷青年们,用投身于宏大理想的实际行动来消解内心的苦闷,通过拥抱集体的行动来消除内心的迷茫。而如今我们这一代人,从去年的刘学州到今年的胡鑫宇,当他们再度面临这种缺失方向的内心挣扎时,能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吗?
胡鑫宇在自杀之前曾三次向母亲打电话哭诉,如果当时能够正确认识到这些心理问题,或许能够抓住机遇帮他摆脱自杀的诱惑。在此最重要的是,避免把“心理抑郁”“精神内耗”看作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旦把这看作是某种“问题”,势必会把这些苦闷、不满视为个人缺陷,进而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年轻人“心理素质差”,是其过分敏感、病态和缺乏受挫能力所致,结果导致这个年轻人陷入到无处可说,走投无路的绝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产生“精神内耗”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至少意味着当事人对时代变动是敏锐的,也正在焦虑地寻找新的方向和新的自我。在任何时代,环境的变动都可能超出个人掌控,此时最重要的是掌控自己所能掌控的事物,从小处着手做起来:当你不知道如何着手、该做什么,又没人引导时,那么至少你可以从能做的事做起,不必想着“一次就能选对”,也不要担心做错,可以“边做边想”,不断调整,“做起来”比“做得完美”更重要。
可以想见,在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过程中,苦闷是在所难免的,有时甚至要经历严重得多的精神危机。就像胡鑫宇从初中到高中的精神层面,学习成绩的前后对比,父母期待与自身成绩的对比,甚至“曾因为没有多考1分而感到自责”,这种不同时期形成的新旧之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悬差。过分懂事的他,反而更容易身陷困境,这就让他从厌学走向了厌世。
去世前与母亲的三次通话,在他的人生中显得非常关键。当他在电话里哭诉时,他的精神已经抵达了临界点,这时候除去他们自身精神层面需要学会坚强之外,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都需要去完善并保障个人的权益,关照他们的精神困境,陪护着他们更好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不要让孩子陷入独自面对抑郁的境地,才能避免胡鑫宇们的悲剧重现。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