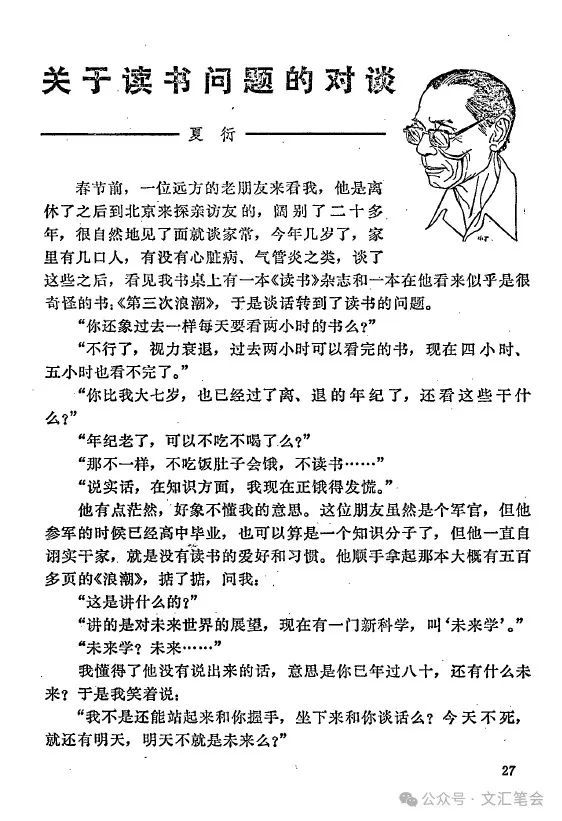
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
春节前,一位远方的老朋友来看我,他是离休了之后到北京来探亲访友的,阔别了二十多年,很自然地见了面就谈家常,今年几岁了,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心脏病、气管炎之类,谈了这些之后,看见我书桌上有一本《读书》杂志和一本在他看来似乎是很奇怪的书:《第三次浪潮》,于是谈话转到了读书的问题。
“你还像过去一样每天要看两小时的书么?”
“不行了,视力衰退,过去两小时可以看完的书,现在四小时、五小时也看不完了。”
“你比我大七岁,也已经过了离、退的年纪了,还看这些干什么?”
“年纪老了,可以不吃不喝了么?”
“那不一样,不吃饭肚子会饿,不读书……”
“说实话,在知识方面,我现在正饿得发慌。”
他有点茫然,好像不懂我的意思。这位朋友虽然是个军官,但他参军的时候已经高中毕业,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但他一直自诩实干家,就是没有读书的爱好和习惯。他顺手拿起那本大概有五百多页的《浪潮》,掂了掂,问我:
“这是讲什么的?”
“讲的是对未来世界的展望,现在有一门新科学,叫‘未来学’。”
“未来学?未来……”
我懂得了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意思是你已年过八十,还有什么未来?于是我笑着说:
“我不是还能站起来和你握手,坐下来和你谈话么?今天不死,就还有明天,明天不就是未来么?”
“不跟你扯这些了,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解放的?回到家里,不是说所有的书,都被抄光了么?”
“书,的确是荡然无存了,用卡车拉走了,经过交涉,七七年冬退回了一部分,其中有一部残缺不全的《资治通鉴》,我历史知识差,就利用这一段空闲的时间读历史,也觉得很有兴趣,而且得益不少,对我个人来说,读中国历史,感慨最深的是中国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特别是宋明以来的道学和礼教的影响之深,为害之烈。我还想到,远古以来,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市民,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颇不相同,他们都有一套相当高明的处世权术,也懂得做官之道。士大夫得意时则讲孔孟,失意时则讲老庄,或者逃禅学道,他们懂得怎样对上,怎样对下,怎样对同俦,怎样保护自己的官职。官僚主义是四化的大敌,是改革的大敌,但要彻底地清除它,看来也很不容易,老百姓是痛恨官僚主义的,但对它们硬是没有办法。”
“我同意你的讲法,别说大官大府了,连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负责人,官僚主义也很厉害,我们那里这几年‘包公戏’大流行,可能表示了一种人民的朴素愿望。……可是,你说的是读历史,怎么会和未来学连系起来呢?”
“这说来就话长,八○年以后,我得到了可以买内部发行书籍的权利,于是开始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这一类书很多,也有公开发行的,几乎整整着迷了一年,其中最花工夫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这是一部‘大部头书’,这书没有丘吉尔特有的文采,但它的好处是言必有据,绝大部分材料来自政府和军方的档案,我从这里知道了雅尔塔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一些细节,知道了英美苏三国对战后世界的蓝图,知道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这一来,兴趣就转到中国的党史问题上去了,于是挤时间读党史和有关的回忆录,正面的读,反面的也读,读了这些,我才恍然大悟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上海地下党三次大破坏的实情,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李竹声、盛忠亮这两个大叛徒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分子,才开始懂得了看事物——包括读历史也必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具体实际,才懂得了照搬外国模式、不问具体情况、一切搞本本主义、一刀切的害处。”
“老兄,你讲了多少次‘懂得了’,‘才懂得了’,早已过去的事,‘懂得了’又有什么用处?”
“你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什么想法?……”
“这,你怀疑我对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决议的态度?”他似乎有点发怒了。
“我的意见是:‘觉今是而昨非’,不知道过去走错了路,犯错误的原因,尽管口头上讲拥护,今后在实践中还是会犯错误的。你在十年浩劫中受了委屈,吃了苦,不妥协,顶住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想问你,当你第一次接触到农业政策改革的实施,听到安徽、四川实行了三中全会的农业政策……例如‘承包’‘个体户’‘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时候,你怎样想,怎样看的,你一点都没有怀疑,一点都没有抵触?”
“那是有,这是老实话,还有人对我说,这会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的话哩。我是八二年秋收之后,亲自回到过去打游击的老区去看了一下,和当年的老房东谈了几天之后才明白的。那时那个村子的人均收入还刚到一百一二十元,可是他们高兴极了,一个劲地问我现在的政策会不会变。这时我才懂得了土改之后,合作化之后,再说‘越穷越革命’这句话是错误了。”
“哈,你也说‘我才懂得了’了!”
“这是‘闻道有先后’的问题,和你谈的读书问题关系不大。”他反驳了。
“‘闻道’的‘道’是哪里来的?也用一句古话吧,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前一句,我你都做到了,但是不读书,感性知识不上升到理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懂一点历史唯物论,错误是会重复的,碰到新事物,又会犯错误的。”
“好,这一点我承认,回去之后,把三中全会以来的红头文件再读一遍两遍……”
“这才对了,你也懂得了读文件的必要了吧,但是文件要读,理论书也要读,我劝你再学习一遍《实践论》和《矛盾论》,能下决心读一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当然更好。不过毛主席的那两本书的好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且容易懂。这两本书,我们读过不只一次了,但你不妨试试看,经过了十年浩劫之后再读,会有更深的体会。要认识我们这些所谓老家伙,就是书读得太少了,想得太少了,知识底子薄,于是就跟不上时代,我开头说的‘饿得发慌’,就是这个意思。你我都该老老实实地承认,解放以来,我们对知识这个问题注意得太不够了,智力投资太少了。”
“饿得发慌这句话,对我说是对的,对你这样的文化人,就不对了吧。”
“你对我的估价不对。我们这些二十年代的留学生所占有的知识,正如我国五十年代进口的机器一样,早已经老掉牙了,现在是八十年代,人家叫我们‘发展中国家’,这在语言学上是一种‘委婉语词’,或者‘模糊语言’,说得老实一点,就是‘落后国家’,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不久前,一位老同志颇有感慨地说:‘要是我们在解放初期,即五十年代肯下决心,像日本明治维新时下一个“教育敕语”,挑选几十万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干部,让他们上学校读书,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精心培养,几十年之后,十万人中能出一两千个郝建秀、李鹏式的干部,那么开创四化新局面,实现翻两番,就容易得多了,不幸的是逝者如斯,无可奈何了。’”
“这一点我同意,那,事到如今,该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是大力提倡读书。我们面临着‘第三次浪潮’,或者说科学技术上已经经过了三次‘产业革命’,现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再不注意这个问题是不行了。”
“十八世纪英国有过一次产业革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三次、第四次……?”
“对,十八世纪中期,说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吧,英国发明了蒸汽机,有了火车、汽船、皮带传动的机器,这是第一次产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价这一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科学发展没有停止,再过一百多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又发明了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可以把水力或火力发出的‘能’输送到千万里之外,这就是人家所说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又发生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原子能的使用开始于一九四五年,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开始于一九四六年,这之外,当然还有外层空间的探索(宇航工业)、遗传工程、合成材料、激光科学等等。第一次与第二次和第三次比,可以说是如小巫之见大巫,发展的速度也大不相同。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间隔了一百二十年,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只相隔了八十年,而现在呢,单讲电子计算机吧,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制成于一九四六年,这部机器有一座洋楼那么大,一共用了一万八千个电子管,运算速度是每秒钟五千次,可是,时间只过了不到四十年,现在已经从电子管(第一代)到晶体管(第二代),再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第三代),又从集成电路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第四代),这种第四代的电子计算机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可以在一块几平方毫米的芯片上,集成几十万个元件,因此,它体积小,耗能低,运算快,可靠性高。三十八年(一九四六——一九八四),换了四代,每一代都是一次飞跃,是不是就此停步了呢,它还在飞,还在跃,日本人放言,要在一九九〇年造出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赶在美国前面,美国人当然不肯示弱。现在,微型计算机、处理机不仅已经进入了生产,而且侵入了学校、家庭乃至文艺领域。‘计算机’这个名词是中国人给它取的(香港叫它电脑),今后可能要改一下了,因为它的功能已经远超过‘计算’的范畴,它开始进入了‘人工智能’,它会‘感觉’,谁也不能说它不会超过‘感觉’而到达某种程度的‘思维’。反正,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之后,科学的进步、变革,不会再用世纪计,不会再用年代计,而真的‘日新月异’了。科学是最活跃的生产力,生产力是要影响生产关系的,这些事,作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不关心、不理会是不行的。十二大以后,我们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电脑’也已经不再是奇怪的东西了……”
“原来如此,所以你又想啃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的世界观是和我们不同的,他对‘第三次浪潮’可能带来的前景的看法,我们也不一定能同意。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即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的十几年之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化。这对我国的四化规划,是一个必须密切注视的信息。”
“注意到了又怎么办?我们还这样落后……”
“还是一句老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我认为是有办法可以赶上去的。我最讨厌十年浩劫后颇为流行的民族自卑感。锁国是不行的,当鸵鸟是不行的,‘我行我素’,依旧搞‘十年、二十年一贯制’更是不行的,不要忘记‘扬长避短’这句话中的那个‘长’字。中国是有许多长处的,除了地大物博(能源、资源、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稀土元素)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真正懂事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说这几年生活好起来了,主要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这是对的,可是在科学这个问题上,我们起步太晚了吧。”
“现在还不迟,只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执行十二大决定了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靠’科学,——这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智力投资分不开,不妒贤嫉能,不搞平均主义,十六年后翻两番是有把握的。我们不是在外国封锁的情况下,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发射和收回了人造卫星,从海下发射了导弹么?这些都是在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做到的。中国人不仅不笨,而且很聪明,美国在电子计算机方面号称世界第一,但美国‘电子计算机大王’王安就是美籍中国人,美国不断吹嘘他们的宇航事业,他们宇航工业的高级研究员中有好几个华裔,高能物理方面更不必说了,丁肇中、杨振宁、袁家骝……可以数出一大批,连‘世界桥牌女皇’杨小燕,不也是中国人么?不久前报上大登的修瑞娟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决不是少数,问题还是在于坚持和认真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选贤任能,信任科学,信任知识分子。从古以来对人类社会提供了多多少少发明创造的中国人,是一定能赶上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浪潮的。”
“今天报上看到,上海、广东,还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在应用和推广微型电子计算机了,我也相信,中国人是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
“不止电脑这一门,在遗传工程(主要在植物学、医学方面)、宇航工程……中国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决不能算落后,只要安定团结,好好埋头苦干若干年,不管它第几次浪潮,中国是不会落后,也许还会冒尖的。”
“这一点我也相信,可是,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离开了工作岗位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做些社会工作不好吗?对青年人做些爱国主义教育,讲讲我们年轻时代受到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讲讲我们前辈推翻三座大山的艰辛,对了,假如你同意,讲讲学科学的重要性、紧迫性,不也很有意义么?”
八四年二月
壬申杂记
一九九一年过去了。按传统的干支,这一年是辛未、羊年。中国遇到了特大的洪涝灾害,但是这只是气候上的灾年,而不是政治、经济上的灾年。在西方的世界,一九九一年是对称年。对称年这个词开始于十一世纪,这就是顺读倒读都一样的那一年,如一〇〇一、一二二一、一九九一等等,按洋迷信,对称年是多事之年,这一年也的确多事,从年初的海湾战争开始,经过华沙条约的消亡,南斯拉夫内战,到十二月的苏联解体。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连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没有料到。
从十月革命算起,迄今七十四年,从组成苏维埃联盟算起,也已经六十九年了,十月革命的炮声一响,丘吉尔就叫嚷要把这个新生的婴儿掐死在摇篮之中,当时有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兵支持白卫军反苏反共,但不到三年,就被不正规的红军赶出了俄罗斯国土,这之后是封锁、制裁、颠覆,但没有成功。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一直打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但是,苏联不仅顶住了德军的进攻,而且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一九九一年以前的世界格局,是一九四五年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的,二战之后,苏联成了超级大国,以柏林为中轴,欧洲一分为二,东欧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则组成了欧共体,它的后台是美国,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的资本主义阵营。美对苏、北约对华约,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局面持续了四十年,在六七十年代,苏联采取了攻势,北起芬兰,南到罗马尼亚,后来终于出兵阿富汗。当时,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了霸权国,勃列日涅夫提出过“主权有限论”。苏联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奢侈、任性,但在文化、科技——特别在航天工业方面还超过了美国,说他是“一世之雄”,一点也没有夸张。可是,为什么一九九一年“八月事变”之后不到四个月,竟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突然出来公开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了呢?这是一个很难解释、也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出兵,没有注入过资本,也没有干涉过苏联的内政,一九八八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过一本书:《一九九九年——不战而胜》,下一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写的《大失败》一书中,则把社会主义消亡的时间拟定在二〇一七年,即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那年,他半开玩笑地说:到那时,克里姆林宫的红场将成为一个旅游点。而现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把这个日程提前了十年或者八年。苏联自我解体的原因很复杂,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代变了,国际形势变了,有了核科学和电脑,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思想僵化,脱离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在农村,依旧坚持他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在工业方面坚持他们的铁板一块的全方位的计划经济。一九八五年以后,冷战结束了,但苏联依旧在大量增加军事经费,而不向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戈尔巴乔夫也讲改革,但他的改革只限于“公开性”而没有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是粮食出口国,去年,苏联却进口了两千万吨粮食,现在还在向欧美要求粮食援助。陶醉于超级大国的美名,满足于陆基和海基远程核导弹的数量超过美国,而不注意经济体制的改革。
东欧变色,苏联解体,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巍然不动,理由是很清楚的,因为早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九亿农村人口,所以我们从那时起就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我们裁军一百万,军工转民用,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也开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让集体和个体经济为补充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加上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同时进行的,我们设置经济特区,我们大胆地引进了外资和侨资,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十三年,中国已经改变了面貌,我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逐年增涨,大部分地区已经从温饱走向小康,按眼下的形势,只要政策上不犯重大错误,不再遇特大自然灾害,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国民经济总值翻两番,人均年收入达到八百美元,是有把握的。这就是说,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找到和坚决地走这一条路,新中国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一九九二.一.十
作者:夏衍
文:夏 衍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 明
转载此文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