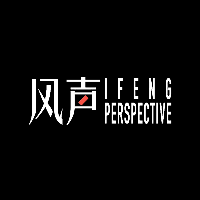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 《建国大业》拍摄现场
作者丨张建伟
近些年来,编剧行业值得关注的话题很多,一些冒犯编剧权益的事情常常引起舆论上的波澜。
原因之一,编剧创作的剧本作为一剧之本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如此,不少编剧对于自己创作的剧本的价值与自己作为编剧的尊严受到冒犯,啧有烦言。有时,一个剧本落到某些导演手里,就成了随意宰割的羔羊,改得高明也就罢了,但不乏加料减料、恣意而为,乃至荒腔走板的。
浅薄的情节编造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建国大业》的成片中,有一段插进去的情节:解放军打到了北平城下,遥望苍茫中的巨大城门城墙,片中一位连长大喊:“报告团长,前边有个地主大院,院墙太高,爬不上去,手榴弹炸不开,请求火力支援!”照明弹下,团长(葛优饰)郑重向上级司令员报告:“突击团已到达北平城下!”这段情节令人讶异,谁都知道北平是和平解放的,解放军距城五公里,围而不打;因此,这段对话就显得生硬荒谬,所谓“打到北平城下”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把北平城错看成 “地主大院”,更显愚不可及。如果将士是这等文化素质,连战略目标都不认识,岂能成为胜利之师?
| 《建国大业》剧照
毛泽东为了保护北平的古建文物,曾给北平前线指挥部,两次下达保护京城古建的命令。哪里会出现一个连长违抗军纪,用手榴弹炸城墙,并要求炮火轰击北平呢?
这段情节,是原作者笔下的剧本中没有、也不会有的东西,不知为何塞入其中。这种浅薄的情节编造,是剧本改写者调侃戏谑解放战争的一个把戏,犹如一桌国宴大餐里赫然出现了一碟臭豆腐。
未经原创者的授权,随意篡改歪曲原创,显然触犯了“保护作品完整权”。电影《九层妖塔》就是因为侵犯了《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作者的此项权利,被法院判令停止发行、播放和传播,从而彰显了《著作权法》以保护原创为核心的主旨。
“副导演”变成“编剧”?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时不仅剧本被篡改,甚至连作者的署名也会被“冒用”:一位叫董哲的电影业内人士,参与了电影《建国大业》的拍摄,在电影片尾字幕和海报上,署名为排名第三的“副导演”,同样是片尾字幕和海报,编剧署名是王兴东、陈宝光。编剧署名本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事,却出现了让人不解的事:不知何时,董哲后来就成了《建国大业》的“编剧、主笔”,“系建国三部曲创作者”。
| 《建国大业》的片尾署名
在一些公开场合,人们用这一身份去指称他,他也不予纠正。在央视周涛的对话节目中,他自称是《建国大业》“主笔”,意思是剧本由他主创。百度百科和不少公开信息显示:董哲乃“《建国大业》编剧”。《中国电影报》也分别在2012年5月24日、2017年11月29日发表的文章中,在董哲的名字后面赫然注明他是《建国大业》编剧。
对于这部电影的编剧身份出现了这种情况,原作者王兴东不能接受。
电影剧本《建国大业》,是王兴东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主动向全国政协申报的宣传人民政协的影片创作项目,这一申请得到肯定。而这部反映人民政协历史的电影,只有充分了解人民政协在协商建国中的历程的人才能写。
王兴东是知名编剧,尤其擅长主旋律作品的创作;作品包括《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黄克功案件》《建国大业》等。1998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创作了人民政协选定五星红旗为国旗的电影《共和国之旗》;此后,2007年为迎接人民政协六十周年,他主动提出并着手创作电影《建国大业》。
王兴东表示:“国家重大革命题材的电影剧本通过审查,备案立项,有了拍摄许可证,才有这部电影的摄制。当全国政协领导审阅剧本的时候,导演在哪儿都是未知数。没有我和陈宝光创作的剧本,董哲怎么会接触到这个题材?电影字幕署名刀刻般清楚,在作品上署名,即表明作者身份。法有明文,目有实证。关键是,很多人明知道这件事情(冒名)不实,都作皇帝的新衣的庸臣,而不是那个说真话的孩子。这是今天知识产权和电影界的莫大悲哀。如果不保护原创者的权益,谁还来做原创,没有原创电影还怎么能有竞争力?”
王兴东、陈宝光将董哲、《中国电影报》社告上法庭,海淀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原告的诉讼理由是:董哲以“《建国大业》编剧”自命,对于以此为内容的虚假宣传安之若素,让人们误解他才是《建国大业》的正牌编剧,贬低了王兴东、陈宝光作为原创者的声誉;《中国电影报》社对于这样一个很容易澄清的混淆,不加分辨核实,以权威报纸的行为对于董哲的侵权行为起到扩大影响的作用,均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 图源微博:@王兴东-编剧
原告的诉求是,董哲应停止使用“《建国大业》编剧”的身份称谓,删除网络董哲词条的侵权信息,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这场官司形成了判决,一审法院对王兴东、陈宝光部分诉求予以支持,认定董哲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处董哲登报声明,为侵权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王兴东、陈宝光人民币十万元和合理费用24500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2022年2月24日作出终审判决书,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董哲的上诉。
这件事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牛浦郎的故事,这个年青小子在甘露庵理读书,老和尚见他有上进的念头,说要拿出两本诗给他看,说了又不肯马上取出,过几日老和尚到乡下给人家念经,牛浦郎“三讨不如一偷”,趁此机会把那两本诗偷了出来,原来是一本锦面线装的《牛布衣诗稿》,心想:“他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并不曾有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这两本诗可不算是我的了?我从此就号作牛布衣。次日,用偷来的钱找刻了两个图章“牛浦之印”“布衣”。正巧过了些日子,老和尚被请去京里报国寺做方丈去了,无人对证,真正的牛布衣已经故去,牛浦郎索性冒名牛布衣,做起名士来了。
这个故事,本是借无人对证之机所为的不轨。而上述案件,原作者健在,编剧圈子也不算大,互联网时代,一切摊在阳光下,冒名的难度比儒林外史的时代要大多了。但是,也没挡了当代牛浦郎“冒姓名小子求名”之路。
特定身份侵权如何判定?
尽管原告获得了胜诉,法院也认定了董哲盗用原作者身份的事实,但是,这起案件留下一个疑问。该案的核心问题,不是不正当竞争问题,而是编剧与原创作品的身份关系及其权益。
此案的本质,是侵犯了王兴东、陈宝光与作品《建国大业》的特定身份关系,也就是假冒创作者身份,行欺世之实,法院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支持这一诉讼主张,原因是董哲没有将侵权行为直接针对或者直接使用于《建国大业》这一特定作品。
| 《建国大业》剧照
“没有直接使用”可以理解,“没有针对”就不好理解了。
事实及其性质的认定,离不开事理逻辑和一般民众都具有的普通判断力,这一案件法院不支持对于文艺创作者署名权及其衍生身份的权益保护,只以不正当竞争为侵权性质的认定,让人难免有舍本逐末之感。
对于原创者的侵权,不限于对于作品上署名权的侵犯,还有针对作品的特定身份宣传上的侵犯。这种特定身份在作品之外具有衍生性权益,不在作品上署名不等于不侵犯“署名权”,法院的判决主文没有将这个案件的实质彰显出来,令人感到遗憾。
这一案件,事实与证据以及案件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本来很快可以认定下来,作出判决。但这样一起容易明断的案件,硬是经历了四年诉讼才作出终审判决。王兴东不禁感慨:“拖了那么久,谁还敢打这样的官司?”
这场官司,对于编剧行业来说,具有公益性质。电影的源头是文学原创,因为是编剧的发现和发明构成了剧本的版权,剧本的版权诞生了电影的版权,因此编剧在《著作权法》规定排名在导演之前,编剧的署名身份权不容剥夺和侵占,维护编剧权益就是保护电影的命脉。
将窃取他人名誉当做终南捷径,假冒著名作品的创作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贪求名气,以待与名气相关的重大利益,是一种野路子。对于这种风气,不亮出明确态度,不通过法律来维权,只怕是越来越蔓延。
经过这一场官司,人们会产生一个愿望:“编剧要维权,希望不要太难。”
作者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辑|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