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与书院教育思想
王立斌
(原文刊于《新国学》第36期)
朱熹是改革书院教育的创始者,他的书院教育及社会学思想博大精深,平正笃实,影响中外书院教育达七百年之久,在研究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与社会思想发展史的同时,必须承认朱熹在改革书院教育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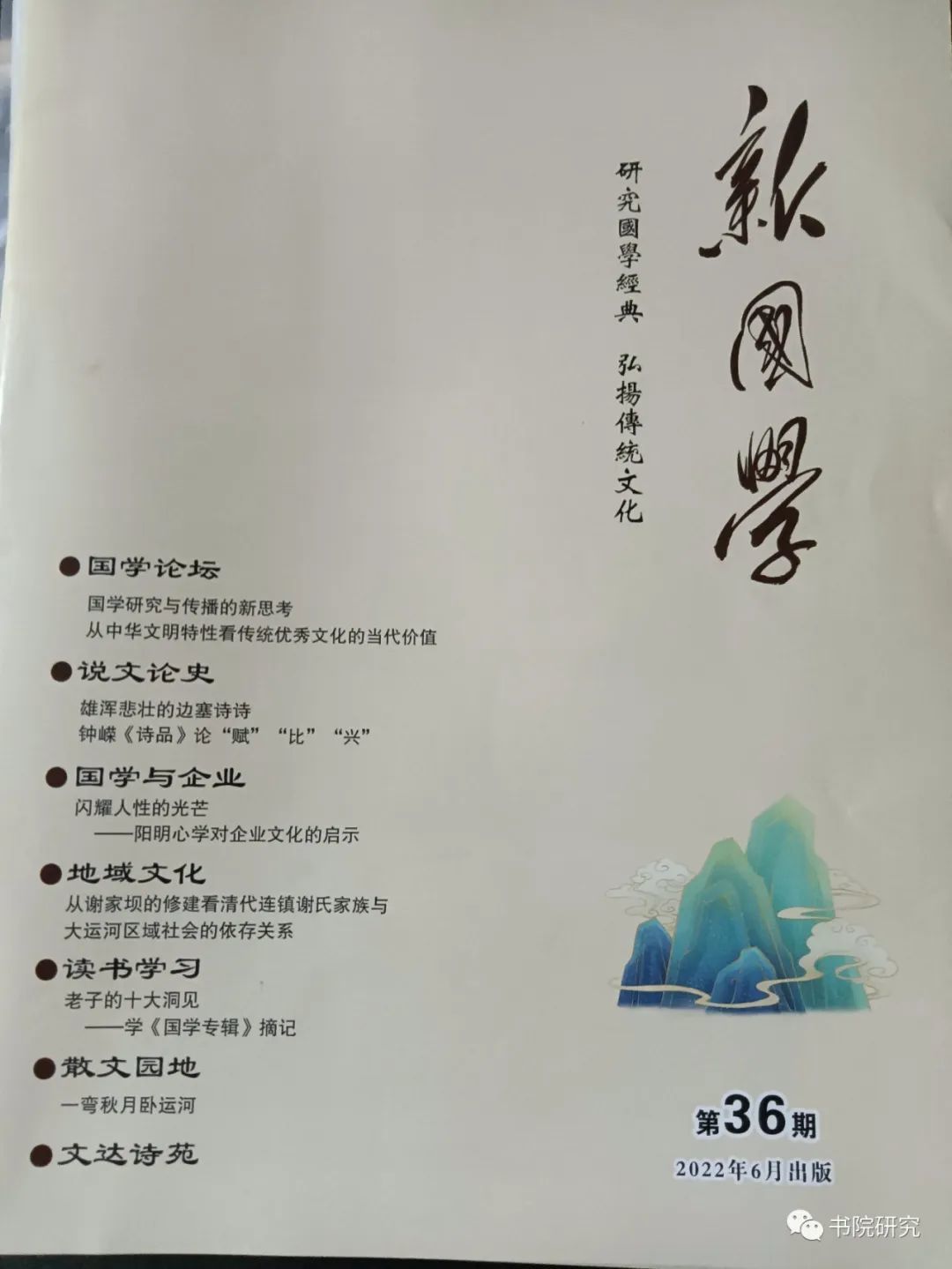
朱熹像王安石一样是一位富有理想的人。他虽然对人才问题也十分重视,但就教育改革的总目标而言,他的重心不是放在人才问题上,而是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通过改革教育与文化建设的途径到社会稳定、健全发展的目的,他以孔子仁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有教无类的方针,着眼于人类社会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在十一世纪未的南宋、朱熹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制度的措施,他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接受基础教育,所谓“当世之人无不学”,是指作八岁至十五岁“小学教育”,大约相当于现代的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阶段,这种基础教育是从“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都必须接受的教育是,治隆于上,俗美于下,即政治清明,国家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风俗习惯趋向良好的根本保证。
这种以六艺为基本教育内容的“小学”包含着群育、德育、美育与军体教育诸方面的教育因素,这种“六艺”教育是知能兼求、文武兼备以求个性人格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与王安石改革教育理论相比较,朱熹更重视扩大教育对象和实行全民的基础教育问题,就这一点说,他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在土地兼并日益激烈,社会贫富悬殊十分显著的南宋时代,朱熹要求把教育对象扩大到每个社会成员,把普及基础教育当作关系到人口素质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战略问题来认识,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夸美纽斯也提出:“不独有钱有势的人的儿女应该进学校,而且所有城镇乡村男孩和女孩,不论贫富贵贱,都应该进学校。”(1)
朱熹“当世之人无不学”的思想虽然还达不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及夸美纽斯提出的那种高度。但已经使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具体化了。“开发其聪明,成就其德业”,朱熹改革书院教育目标是以这一基本观念确立的。他重视基础教育,也不忽视造就社会需要的人才的问题。他在《大学章句序》中将教育制度分为“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就是为了更妥善地处理好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和造就社会需要的人才问题的关系。他认为“大学”(相当于现代的高等教育)主要的任务是造就德才兼备的人材。限于时代条件,朱熹还是把统治者的子弟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对象,但已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他迫切要求将“大学”的教育对象扩大到“庶民”阶层中去,“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2],这在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社会中要真正实行是比较困难的,但能提出这种意见并为此而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对打破高等教育的门第观念,使普遍民众中有才华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而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材,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朱熹是个大胆改革书院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他恢复、创办的书院是古代私立高等学校,书院的教育对象就不限制于皇亲国戚、文官武将的子弟,“草野之芥民”,“总角之童子”都可以“环以听教”,讲友、门生都是慕名而来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原则,来者不拒,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个性的讲友与学生,都受到书院热情欢迎与周到安排,《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著录的讲友和门生有一百一十多人,有父子同拜朱熹为导师的,如蔡元定与蔡沈;有兄弟问学于朱熹的,如辅广及其从弟辅万;有不同学派的学者求教问难于朱熹的,如湖湘学者胡大时,先以张南轩为师,后又以朱熹为师,最后又师事陆象山。再如王介,同用师事吕祖谦与朱熹,还有慕名徒步专程要求教的,如朱熹、吕祖谦“讲学于婺”舒“徒步往从之”;讲学和听讲是自由的,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感情也相当深厚,这与当时“太学”的“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是大不相同的,这种良好治学风气影响极为深远,直到清代顺治年间的白鹿洞书院还规定:“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或有远朋,闻风慕道,欲问学于其中者,又不可却,……当留洞中,以资切磋。”(2)这说明书院教学是实践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原则的。
从先秦到南宋,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一般是由王室、贵族、官僚所垄断,殷商时代的“右学”或“西学”,周代的“辟雍”,汉代的“太学”,“鸿都门学”、“贵胄学校”,晋朝的“太学”,“国子学”南北朝的“玄学馆”、“文学馆”、“儒学馆”、“史学馆”、“聪明馆”、“虎门学”,隋唐时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辟雍”等等高等学府,招生对象基本是王公、贵族与官僚子弟,只有少数低级官员与平民子弟才能进入这些学校学习,隋唐时期的文化教育发展极为迅速,但高等学校教育对象的等级界限仍然十分严格,不仅学生入学有等级限制,而且各大学之间也有等级区别,如弦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都严格规定了官员的品级,只有四门学接受文武七品以上的子弟和“庶人”中的“俊秀者”。
宋代三次兴学,范仲淹王安石都改革了高等学校的招生规则,除“国子学”专门招收七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入学外,太学、四门学、武学都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各级官员的子弟以及部分庶民子弟都有入学的资格,等级界限不再像唐代那样森严了,第二次兴学时,由于王安石改革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才,即“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认为民众受教育则“多智诈、巧伪滋生,所以难治,”尽管他也大力发展地方教育,但收效不大,特别是私学受禁之后,地方教育和普通基础教育颇受影响,地方高等教育几乎没有新的发展。朱熹提倡改革书院教育制度,创办地方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范围,在教学上进行重大改革,这是继范仲淹、王安石改革教育之后的一次大胆的革新。
朱熹改革书院教育,还大胆地提倡和尝试了以名师巨儒传播文化,振兴书院教育,从而达到了推动书院教育制度的勃兴。当时围绕改革书院教育及治学的观点,在淳熙二年(1175年)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的《鹅湖之会》。
(二)
当年朱陆围绕治学方法、修养方法的问题展开了面对面的探讨。终因意见不合而散,而问题的焦点就是朱熹所提出的“即物而穷其理”居敬与穷理并用。而陆九渊则强调:“尊德性”即“心即理也”。朱熹强调读书人应做个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圣贤,去博览群书,去观察外物来启发内心的知识,还要求每个“学者必须置身于法度规矩之中,使持于此者足以胜乎彼,则自然有进步处”[3]。陆九渊认为,要做一个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圣贤,首先要端正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才能获得“放心”便可穷理。这就是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世界所倡明的“心学”根本。也就形成了与朱熹学说抗衡的异同分界线,而产生鹅湖之会的原因所在。
列宁说过:“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4]。朱、陆鹅湖之会,不但没有达到观点上的统一,反而面对面地展开了一场锋芒毕露地讥讽与诋毁。朱熹讥陆九渊为“禅学”,陆九渊诋朱熹为“俗学”,双方互不相让,自我标榜,鹅湖之会论辩数天,毫无收获。因此,不欢而散,为以后的书院治学教育埋下了伏笔。
三年以后,朱熹仍未忘怀鹅湖之会,他带着诚挚的友情心平气和地步原韵和了陆氏兄弟一首诗:“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过寒谷,又枉蓝与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加涵养转深沉,欲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5]朱熹的和诗柔中有刚、绵中藏刺,从诗中还可看出其为人治学修养,求同存异的宽阔心胸,而他一生高尚道德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与陆九渊在学术上的论敌,生活中的挚友情感的具体表现。
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在论述鹅湖之会时曾说过:“假令当日鹅湖之会,朱、陆辩难之时,忽有苍头仆子,历阶升堂,摔陆子而殴之日,我以助朱子也?将谓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达而逐子矣”![6]从黄宗羲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来朱熹学术思想的影响在历代学者中地位,千百年来都视为儒家的典范。
淳熙八年二月(1181年)朱熹在主南康创建白鹿洞书院时,还特邀陆九渊前来书院主讲《论语》,而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束然心动。朱熹更是感慨万千,并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7]事后朱熹还请陆九渊将“讲义”勒石刻之,以念同志。朱熹还对别人说:“当时陆九渊说的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象朱、陆这样两大学派的创立者,能如此开阔心胸,尊重他人优点,推崇他人学问,保留自己的观点,确是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鹅湖之会,首开了“治学论辩”的先河,此后为书院“讲学”逐步形成了制度。尽管学者之间、学派之间主张不同,观点各异,但往返讲学辩难并不拒绝。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全国书院互通声气,著名学者不辞辛劳地千里赴会,使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直至清末。
(三)
朱熹在他多年的教学活动中,提出和总结了不少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但是有很多是发人深思的见解是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的。例如,下面几个治学原则是他在治学中经常强调和运用的,它体现了朱熹治学思想的成就特色。
一、朱熹在治学过程中是十分重视启发诱导的。他常与“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21]所以在“解疑”(解决疑难),“精思”(精心思考)以及强调做学问要注重融会贯通等方面,他是积累了一些有启示性的经验的。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8]朱熹把读书看做是一个从未知有疑,渐疑,是疑到解疑,无疑的过程。朱熹这个观点说明了学习知识必须经历从浅到深,从表象到本质,从粗枝大叶到融会贯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学习认识过程的一些特点。
朱熹还主张读书必须“精思”。“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神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9]“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朱熹主张凡书必须“熟读”,“精思”其内容,主要是指对儒家经典意旨的领会,把治学内容和教学原则、方法适当的区别开来,做为一个教学原则,朱熹的“熟读”和“精思”还有它值得吸收的一面。例如:对学习的内容必须熟习,其中一些重要的篇章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背诵,在学习的过程中强调必须神心思考,提出疑难,力求对知识的实质有所理解,这些意见看来还是合理的。
朱熹还提出了做学问不能坐井观天,抱残守缺,他对张载的“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说法是十分赞赏的。所以他也说:“学者不可只管守以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10]他曾有诗一首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1]这首诗它描述了一个透明如镜的池塘,它之所以如此清沏,是因为有源头活水的不断流动补充的缘故。他以此来比喻做学问也应“通而不塞”,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知识或新见解来补充,才能使人见识通达,头脑清新,这个比喻是十分形象和发人深思的。
朱熹还强调学习知识必须反复钻研,逐步消化,才能有所收益,他打了一个比喻,“臂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朱熹这个说法表明了学习知识必须融会贯通,才能理解它的实质。
二、在书院教学过程中,朱熹认为光是“读书穷理”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与“躬行践履”相结合,知与行是不能分离的。所以,朱熹把自己学问和指导学生学习的指导原则规定为:“穷理以致其知实”。[12]但是朱熹所说的“穷理致知”的过程,并不是指对客观世界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而是指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最高范畴“理”(即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的领会。他十分坦率的说:“穷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无别物事,只有个仁义礼智,看如何千变万化,都率此四者不得”。[13]
然而朱熹强调人们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对封建主义道德教条的领会和认识上面,更重要的是掌握的这些教条付之于行动。他说:“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14]“学之之博,不若行之之要;行之之要,不若行之之实”。朱熹所说的“行”、“体之于身”或是“践履”,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强调了“穷理”的目的必须落实于“践履”。也就是视读书穷理必须与躬行践履相结合,这就是朱熹在治学上关于知与行关系的看法。至于他的所谓“行”或“践履”的具体内容就是他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规定的“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室欲,迁善改过”这类的封建主义道德行为,以及他在《小学书题》中所说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类的封建主义的礼仪细节和规矩典范。
可见,朱熹所提倡的“笃行”或“践履”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实践,他所主张的知行并重,也不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浸透到人们的思想里去,要求他的学生在行动上必须按照这些封建主义的原则去做,使人们和他学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接受封建主义道德规矩和礼仪的束缚。所有这些,它的目的无疑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它是朱熹治学思想中的糟粕。但是,同时也看到了朱熹在治学教育中思想和行为的联系性,道德信念必须转化为道德行为习惯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到教学过程或德育过程的一些侧面。朱熹这个思想在中国书院教育史上是有很大影响的,至今还可借鉴。
三、朱熹又是一个在治学上积极倡导“循序渐进”的教育家。
他对“循序渐进“做了较多的阐述。
1、朱熹主张做学问要打好基础,臂如造屋一样,必须打好地基。他说:“识得道理源头,便足地盘。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墙基,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无好基址,空自今日用得多少好材去起屋,到时,只能是房塌人伤,自家身体自没顿放处。”(15)“须就源头看,放大底道理透,阔开基,广开址。如要造百间屋,须著有百间屋基,要造十间,须著十间屋基”。(16)“学,须行理会那大底,理会得大底了,将来那里面小底,自然通透。令人却是理会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寻里面大小节目”。(17)
朱熹的上述这些话主要是想阐明下列几个观点:一是说无论是学习或做学问,基础必须牢固,如果没有牢固的基础,就好象把屋架在别人地上,等于空中楼阁。学问根底不深、不实,要枝繁叶茂也就困难。二是说学习或做学问要扎扎实实,步步为营,如要造多少间屋,就要打好多少屋基。三是说把基础的东西弄懂了,其他细微末节的东西,也会迎刃而解。
2、朱熹主张读书要循序渐进,方有成效。他说:“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所谓循序渐进者,朱子曰:‘以二书言之(指《论语》、《孟子》二书),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末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18)朱熹对读书要注意“循序渐进”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因素,就是学习必须根据每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和能力(“量力所至”),来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和次序,并严格遵守它;同时学习不能囫囵吞枣,没有弄懂前面的东西就急急忙忙去搞后面的东西,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会好的。
3、朱熹还主张学习要从易到难,从浅到深,从近到远。他说:“如攻坚木,先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33)“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19)朱熹的上述思想是符合“循序渐进”的治学原则的,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教学和治学的经验之谈。
四、朱熹治学又是一个严格要求学生学习或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的老师。他说:“读书须是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更不问外面有何事,方见得一段道理出。”(20)“读书看义理,……只专心去玩味义理,便不会心精,心精便会熟。”(21)朱熹要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要人们在读书时要专心去领会封建主义的“义理”,这也是为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朱熹要求学生做学问,读书应该专心致志,全神贯注,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在学习上面。“人做功课,若不专一,东看西看,则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22)“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23)“看文字须大段着精彩看,耸起精神,竖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24)
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观点看来,朱熹要求人们学习时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防止分散松懈。严格要求学生读书时要有认真、仔细、专心和苦钻的态度和精神,象这样的教学思想无疑是值得继承的。
朱熹最后归结到人的学问能否有所成就,学习能否有所长进,关键在于“立志”。“立志不定,如何读书”。“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理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学者须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乾,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
朱熹关于“立志”的治学观点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第一:求学、读书必须有较高的志向,没有确立崇高的理想,要想攀登学术的顶峰是不可能的。第二:有了较高的志向,才能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才能产生坚强的学习毅力,和不屈不挠的钻研精神。第三:凡是“立志”不坚者,根本不可能把学习的积极性高度发挥起来。胡混的打发日子,学业不可能有任何成就。朱熹的这些话对一切愿意在学业上努力做出成绩的人来说,是一番很好的“忠告”和“良言”。
(四)
儒家经典著作《中庸》里说:“尊德性而道问学”。然而,朱、陆在治学与教育上的争论焦点是各自都把“尊德性”和“道问学”分开来理解,朱熹讲用“即物而穷其理”居敬与穷理相互运用。只强调读书人应做个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圣贤,去搏览群书、去观察外物来启发内心的知识。还要求每个“学者必须置身于法度规矩之中,使持于此者足以胜乎彼,则自然有进步处”(25)。而陆九渊则认为,要做一个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圣贤,首先要端正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强调“尊德性”先立乎其大者,“心即理也”。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人人固有的“本心”才能获得“放心”便可以穷理。其实他的认识论与修养方法论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涵泳本心”之说。他所主张“尊德性”是以纯粹的唯心论者的态度教人。这就是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所倡明的“心学”根本。也就形成了与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学术观的异同分界线。
马克思说过:“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理论目的。”(26)列宁又说过:“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心主义的。”(27)朱、陆在鹅湖之会上,不但没有达到观点上的统一,反而面对面地展开了锋芒毕露的讥讽与诋毁。陆九渊底朱熹为“俗学”,朱熹讥陆九渊为“禅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28)双方互不相让,自我标榜,赋诗责难。陆标榜自己的学说是“之质高明、故好简易”以“尊德性”为宗。而朱熹则标榜自己学说是“之质笃实,故好邃密”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人圣之阶梯。”(29)陆九渊还自负地认为自己的学说“易简工夫终究大”,而讥论朱熹的学说是建筑在没有根基的沙滩浮土之上的“浮学”。鹅湖之会辩论了三天,各知据理力争。谁也不被说服,故而也就达不到吕祖谦设想的那种目的。因此,不欢而散,就此告终。会后各位参加者都以此会为推崇,据吕祖谦在给信中所说:“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其欲著实看书讲演。”(30)
朱熹从事书院教育达五十年之久,主创过白鹿洞书院,并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定立教条,亲自讲学论辨。他任潭州太守时,同张拭一道改革了岳麓书院,使湖湘的书院教育改革面目一新。所谓的“潇湘为泗洙,荆蛮成邹鲁”就是指朱、张在湖湘的书院教育改革的重大贡献。朱熹还为各地书院、学校的改革撰写文章,如《衡州石鼓书院记》、《信州铅山县学记》、《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静江府学记》、《珍州学记》、《福州州学经史阁记》、《州江山县学景行堂记》,在文章中大胆地批评腐败的官学教育制度,提倡颂扬新型的书院教育制度。他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民于读书,读书之法,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即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精辟地概括了“学、问、思、辨、行”的读书方法。并倡导书院教育改革首先要创办地方特色的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范围,建立符合人性的、平等的、可选择性的教育制度,而这些改革措施至今还适用于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
研究朱熹改革书院教育的社会学思想,结合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改革,论述朱熹一生用于教育治学理论,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朱熹的一生精力都耗费在恢复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站在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勇敢地抨击,致力于弘扬,发掘蕴含在《诗经》、《楚辞》、《易经》、《礼记》中的文化哲学精神,大胆地革新倡导新的南方文化教育体系,抗衡佛教,道教与儒教文化系统的凝聚群体的功能,完成了韩愈、欧阳修、胡瑗等人辟佛的历史使命,实现了“当世人无不学”、“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的教育理想。这就是朱熹一生致力于改革书院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
(注释略)
作者简介:
王立斌,江西省上饶市鹅湖书院管委会原副主任、书院院长、研究员,上饶师范学院朱子研究所研究员,江西省2011计划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书院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江西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博与书院文化研究工作,现任北京七宝阁书院《书院纵横》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