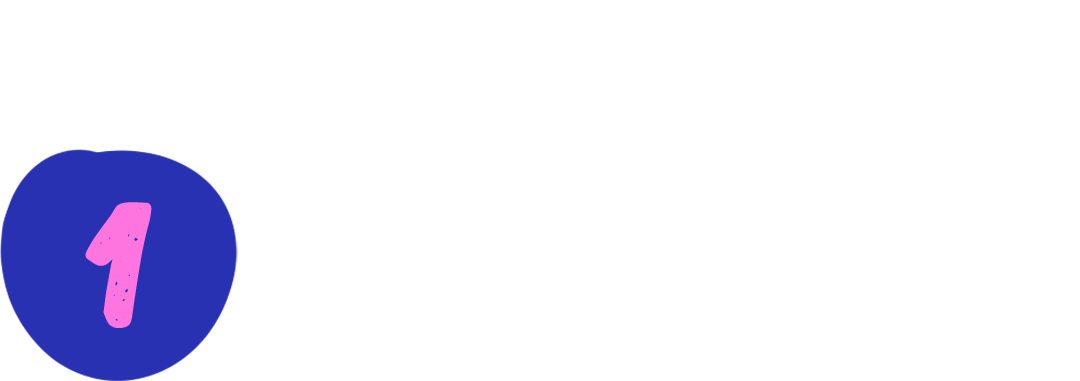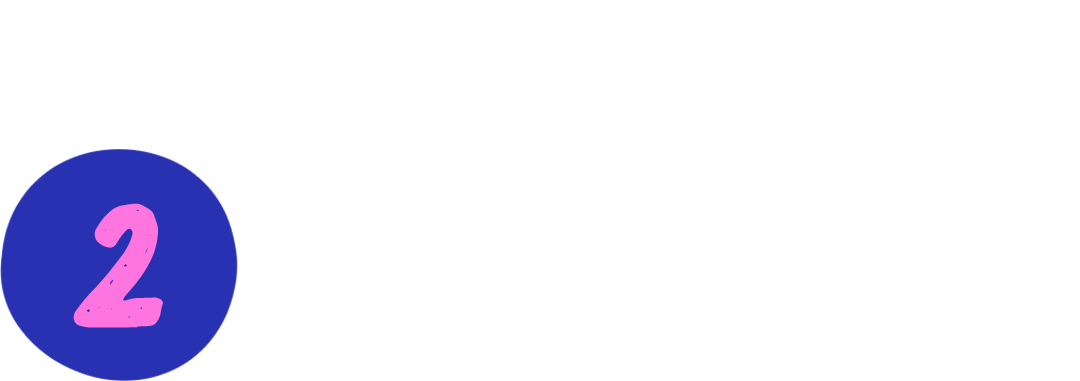作者 / 向 向
编辑 / 朱 婷
运营 / 小饼干
跟现实流逝的时间不同,文艺作品呈现出的世界往往是永恒且绚烂的。所以,我们往往在得知创作者离世时,总有种难以置信的感受——那些在作品中感受过的情感适时析出,跟不可置信混合均匀,构成眼下复杂的感情。
今日下午,根据中国美术学院官方消息,导演万玛才旦于5月8日凌晨因突发急病医治无效去世。太过突然,无论是电影从业人员或是单纯的影迷都感到震惊且悲痛。因为工作,kk曾在不少公开场合群访/对话过万玛才旦导演,他一直都很纯粹、谦逊有礼。听闻此消息,震惊之余,更多是惋惜与不舍。
不久前,万玛才旦的新作品《陌生人》才刚刚宣布杀青;在落幕不久的北影节上,他也才刚刚露面;甚至昨天,他还在朋友圈“为年轻的电影人祝贺”。
死亡总是突如其来,只来得及把故事说完一半。
土地的故事
作为藏地电影浓墨重彩的一笔,万玛才旦的名字以及作品,都与这块土地有着深深的联系。
1969年12月,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位藏族学生,他是特别的。同时,作为一位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制作人,他曾获得的荣誉也是显赫的。
作为电影节常客,他的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走的是釜山-鹿特丹这条再经典不过的路线。此后,万玛才旦两次入围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寻找智美更登》和《五彩神箭》各有获奖。而影片《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和《气球》均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其中《撞死了一只羊》获得最佳剧本奖。
万玛才旦并不仅仅只是导演。作为藏区电影的坚持者,他坚守的是一种民族声音的表达。20余年来,他始终在不同语言中游走,他把藏地的故事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带给世界。他的汉语小说集有《故事只讲了一半》《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乌金的牙齿》,藏语小说集有《诱惑》《城市生活》《岗》。主要翻译作品集有《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德本加小说集》等。
作为“藏地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万玛才旦低调朴实,但从不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就在前不久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上,作为“注目未来”单元国际评审团主席的万玛才旦,携法国制片人科琳娜·博普、美术指导李淼、演员齐溪以及日本导演深田晃司等评审团成员亮相。走在红毯上,他显得意气风发。
2005年,万玛才旦拍摄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上映。这是第一次,由一个藏族导演,把藏区真实生活带到了大银幕上。这一年,《静静的嘛呢石》击败顾长卫的《孔雀》,获得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
但到2015年《塔洛》上映时,他的故事才真正得以在全国公映。这是他的第五部藏语长片,万玛才旦并因此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等13项国内外大奖。
万玛才旦在颁奖词中说:“《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2017年,万玛才旦写下小说《气球》,发表在《花城》杂志。那一年,西藏成为影视圈的“热词”,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将11位藏人的朝圣之路投射在银幕上,凭借对现代都市人灵魂的想象性救赎,斩获1亿票房。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和《塔洛》上映时惨淡的排片相比,藏地的故事如同虔诚的磕长头,一起身,一附身,一部又一部,把真实的信念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飞走的气球
但大部分影迷们都认为,《气球》是万玛才旦用情最多的一部作品。它也是万玛才旦导演第三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长片,讲述的是一个牧区藏族家庭里,一只气球——其实是避孕套,引发的一系列窘事。
在影评的话语体系中,《气球》被认为是一部揭示传统与现代冲突及女性觉醒主题的电影,也是万玛才旦“渐显大师气象的作品”。
《气球》像一支小小的望远镜,望着藏地人民的生活,他们与轮回转世的命运紧密相连,因着独特的宗教信仰,拥有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孩童背上长痣,被长辈说是奶奶转世留给他的记号;老人死去后,家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安葬,而是向上师请教老人转世的去处;甚至丈夫强迫妻子生下孩子,就是奢望能为死去的亲人前世接环……
提起万玛才旦的电影,始终又绕不开文学性。实际上,他的文字或影像都有同一种能力,我们能在他的文字中窥见画面,又往往在影像中得到收获诗意的文字反刍。
而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他的影响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看他早年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等片会让人想起阿巴斯、布列松的写实风格。《塔洛》用上了考验耐心的固定长镜头,让人如同反复困在一成不变的死水中。《撞死了一只羊》似乎沾染了监制王家卫视觉风格万但在《气球》又摇身一变,吕松野的手持镜头配上藏青色的调色,像一种青涩的不安。
万玛才旦常说,“文学和电影,这两种我都喜欢。文学有文学的优势,电影有电影的魅力。”
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在中关村的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
“那个意象一下抓住了我,想起电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也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地的事情,心里有了故事的雏形。”万玛才旦说。如同他很多故事一样,《气球》也拥有一个开放式结局。
我们总是无从得知气球飘向远方后的结局,如同万玛才旦创作过的那些故事一般人戛然而止,也如同他才华横溢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