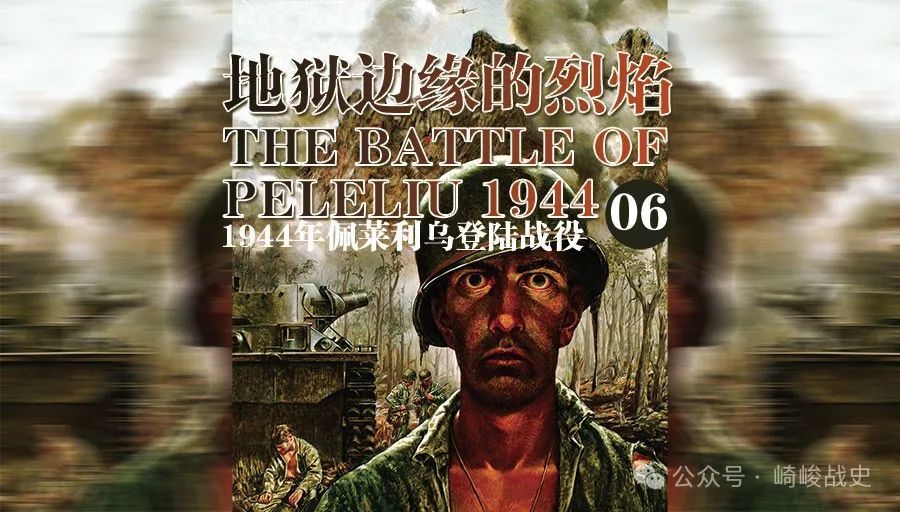
左翼的煎熬
与进展相对顺利的右翼和中路相比起来,位于陆战1师左翼的陆战1团的经历是最为惨烈。他们从登陆日开始就是血战不断,一直遭到以血鼻山为中心的日军主力守军激烈并有组织的抵抗。
9月16日,刚刚抵达滩头指挥所后的鲁佩图斯少将命令将陆战7团第2营(师预备队)调给普勒那处境艰难的陆战1团,以“保持冲击力”--这个词不知鲁佩图斯之前已向普勒絮叨了多少遍。
陆战1团第2营上岸时是面朝东,9月16日开始左转前往夺取机场和山脉之间的建筑区,半小时之内他们就穿越机场达成了目的。然而最左翼的陆战1团第3营根本没能前进一步,作为团预备队的陆战1团第1营在16日下午被投入战场协助第3营。经过残酷战斗后,陆战队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终于攻占了450米长的“要点”珊瑚岭,第1营B连还和被孤立近30个小时的第3营K连取得了联系。夜里又击退了日军的一次联合反击之后,至9月17日上午,编制235人的K连只剩下了78人,只能撤至后方充当预备队。
■ 上图:9月16日拿下了机场北部建筑区的陆战1团第2营部队,这里也早已在登陆前的炮火准备时被炸得只剩下一片瓦砾。
■ 在飞机从东南部对血鼻山脉的南部群山进行观察。
17日当天,陆战1团主力还首次和血鼻山之敌碰面。从战前的航拍照片上很难看出这条山脉的真实自然条件,当时它的斜坡上盖满了常绿的丛林,所以看上去也并非特别险恶,但现在经过了海军舰炮和飞机轰炸之后,丛林已经差不多被完全铲尽,狰狞的地形真相这才显露出来,后来陆战1团的团志中是这样描述的:
“除了大片嶙峋的珊瑚外,到处都是布满碎石的悬崖、山脊和冲沟。”
陆战1团到9月17日时的伤亡人数就已经过千,结果其全部三个营都被投入了团正面战线,第3营负责左翼,第1营居中,第2营在右,新近抵达的陆战7团第2营作为预备队。
陆战1团第2营首先遭遇血鼻山守军,该营起初推进还算顺利,但冲到众多山脊中的第一道(200高地)跟前就突然被迫停下。官兵们沿斜坡奋力攀爬,经过惨烈的白刃战并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在夜幕降临时将该山头控制,但随即遭到下一道山脊(210高地)上的日军炮火覆盖,不得安宁。
居中的陆战1团第1营最初进展同样顺利,直到碰上了一个之前未被海军舰炮发现的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后来在随行的炮火引导员呼唤战列舰的14英寸舰炮直接命中之后,它才轰然消失。左翼的光景稍好一些,陆战1团第3营是沿着比较平坦的西岸平原推进,越走越快,直到出现与右侧的第1营失去联系的危险才停下脚步。
■ 刘易斯·巴维尔·普勒(1898-1971),绰号“牛头犬”,来自弗吉尼亚州,20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后来先后被派往加勒比海、海地和尼加拉瓜服役,二战前还被派到过中国,1933年在上海担任过陆战骑兵队指挥官。从1941年8月起,历任陆战7团第1营营长、陆战7团副团长、陆战7团第3营营长、陆战5团第3营营长、陆战1团团长和陆战1师师长等职务,也是历史上唯一获得过五枚海军十字勋章的陆战队员,他于1955年退役,最终军衔为陆战队中将,1971年10月11日去世。
到9月18日,普勒的陆战队第1团伤亡人数已经攀升至1236人,但普勒仍被鲁佩图斯催促要“保持冲击力”,结果普勒只好把包括工兵、工程兵和指挥部人员在内的所有后备力量都当成了步兵来用。早上6时整,作为师预备队的陆战7团第2营也前往战线中路换下陆战1团第1营,后者暂时转为预备队进行短暂的休整。18日的战况根本就是17日的翻版,而这样的场景还将日复一日地重演。身处左翼沿着海岸平原推进的陆战1团第3营当天进展又是极顺,只不过再次要为与中路的陆战7团第2营保持联系而停下。在陆战7团第2营和陆战1团第2营的联合夹攻之下,日军在210高地上的突出部被急剧压缩,但是日军却转头向200号高地发起了凶猛反攻,逼得陆战队员撤下了这座昨天傍晚才拿下的山头。下午14时,右翼的陆战1团第2营营长拉塞尔·洪佐维茨中校(Russell E. Honsowetz)报告称本营形势极度危急,需要立即增援。因此,刚刚转为预备队的陆战1团第1营B连火速赶往支援。该连赶到之后被立即投入向205高地的突击,出人意料的是,占领这个高地的过程相当顺利,但后来发现它的位置在群山中比较孤立,只能够当做一个观察点。刚一拿下205高地的该连随即继续向前冲,但却被一个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为恐怖的地形给挡住,被迫后撤,这里全是绝壁和断崖,几乎没有一个可以攀爬的支点,后来该地被称为“五姊妹山”。与此同时,陆战1团第2营的最右翼部队沿着200高地下面比较平坦的地面向右平推,试图与陆战5团的左翼接上头。
■ 上图:在珊瑚岩构成的山体和高地中艰难前进的陆战队员,再加上日军在这样的地形中构筑了严密的防御阵地,使得陆战队员们的进攻每天都只能以米计算。
■ 上图:在朝200高地上的日军阵地炮击的美军37毫米反坦克炮,这个高地同样可以对向五姊妹山进攻的美军射来致命的侧射火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