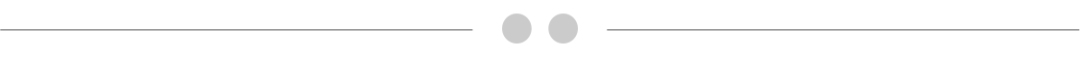九月初,韩国女团BLACKPINK的成员Lisa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则限时动态,她将于本月28日至30日出演法国疯马秀(Crazy Horse)。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疯马秀是以女性半裸或全裸跳舞闻名的表演场所,虽然近些年来,疯马秀积极与各界女性合作,消解了部分色情表演的底色,甚至于疯马秀的品牌经理表示,邀请Lisa是为了吸引年轻女性客户,疯马秀已经成为一个骄傲、自由的女性象征。

但是,这未能打消大众的疑问——即便疯马秀今天正在书写出新的意涵,但它真的已经完全从对女性的剥削转向某种解放了吗?在父权制的背景下,展现女性的性魅力是自由还是陷阱?如何判断商业包裹之下的女性选择是否出自个人意志?
争议仍在继续,但我们可以试着回看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曾面临的分歧与阻碍,或许会受到启发。上世纪80年代,性消极女权主义者与性积极女权主义者之间展开了大讨论,性消极女权主义者反对色情制品、性虐待、性服务,乃至对最寻常的男女异性性行为都持有根本上的负面态度;性积极女权主义者则对性解放、性多元、色情制品、性的商业化持有更宽容的态度。
不过,性消极女权主义、反色情女权主义的思路并没有成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共识;事实是与之相对立的性积极女权主义同样完成了相当有效的思想动员,并且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是更成功地占据了更大的时代观念版图。
今天,我们将一起来回顾这段当代女权主义思潮内部最重要的辩论之一。
讲述 | 陈迪
来源 | 看理想节目《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
01.
性解放成了性变态
反色情女权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安德莉亚·德沃金以及凯瑟琳·麦金农,曾经在1980年代初,一度成功地在两座美国城市通过了色情制品非法化的立法尝试。虽然她们的法律最终在行政与司法力量的反对下失败,但至少立法层面上的成功,已经能够相当说明时代环境的变化。
经历过1960年代的运动浪潮与197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左翼进步主义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但是,与之相对立的右翼保守主义,也已经从最初的进退失据中恢复过来,并悄然积蓄好了反扑的能量。
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出,充分证明了新保守主义回潮的大势所趋。当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被视为叛乱分子,摇滚乐成了靡靡之音,性解放成了性变态。
保守主义思想阵营高举传统道德旗帜,重新大肆讨伐一切异性婚姻以外的性实践。他们认为社会中“不道德”的性导致了美国力量的下滑,同性恋文化导致了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处于下风。如果美国要想在国际政治中占优势地位,就首先需要在国内政治里打赢对同性恋的战争。
《燃烧女子的肖像》
保守派的立法者们在反对色情制品、性教育、堕胎、避孕、同性恋等议题上全线开火。
一些明显出于宗教道德动机的法案在联邦层次得到通过,譬如1981年里根政府的《青少年家庭生命法》(Adolescent Family Life Act):法案反对青少年性行为;但如果青少年还是有性行为,则不鼓励他们使用避孕手段;而如果怀孕了,就更是阻碍青少年获得堕胎的机会。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反色情女权主义者能够从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中寻获丰富的结盟机会,是大可想见的。而处在另一方面的性积极女权主义者,则更有理由认为自己正在逆大势而行;她们如今需要努力守护的,是女性性解放来之不易的历史成果。
1982年4月,一批性积极女权主义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筹备召开了一次性研究学术会议,人称“巴纳德性会议”(Barnard Conference on Sexuality)。
这次会议的目标,主要还是为了讨论女权主义者在保守主义回潮新形势下的思想立场;但不可否认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批评反色情女权主义的用意,毕竟组织者很明确地提到会议目的是要“去到比关于暴力与色情的辩论更高的位置,聚焦区别于生育的性本身”,并且会议也没有邀请任何来自反色情女权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出席。
召开日之前,这个会议的消息被反色情女权组织的成员得知了。她们很快就组织了行动,打电话、寄抗议信给校方、学院、组织者,然后在会议当天聚集在会场外抗议,派发己方立场的材料与传单。这次会议也因此被后人视为女权主义思想阵营内部关于性问题的论战(the feminist sex war)全面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02.
“用新的魔法打败旧的魔法是没有意义的”
在巴纳德会议的参与者当中,一名主要的发言者、同时也是会议组织者之一,是文化人类学者盖尔·鲁宾(Gayle Rubin)。除了女权主义,鲁宾的研究领域多有涉及性虐待、同性恋、商业性行为、色情文化等性的亚文化领域;所以除了女权主义者通常具备的女性视角以外,鲁宾的思考更多时候还带有性少数者、性偏离者的关切,这也因此在她和很多女权主义的作品之间造成了重要的区分度。
在巴纳德会议中,鲁宾作了那次会议上也许最著名的一个发言。两年之后,这份发言被整理成一篇完整的长文章发表,标题是《思考性:性政治激进理论的记录》(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后人在引用的时候,通常只写主标题“Thinking Sex”,就是指这篇文章。
鲁宾的这篇文章成为了女权主义性论战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同性恋研究以及酷儿理论史上的关键性作品。
《思考性》并不是专门针对反色情女权主义的批驳,文章花了很长的篇幅回顾西方历史上对性的贬抑,以及当代的社会与政治,对少数的性、主流以外的性的制度性压迫。
鲁宾分析,在关于性的问题上,人类社会普遍采用一种等级序列形式的系统,来衡量、排列不同的性行为的价值,鲁宾称之为“性的价值等级体系”(the hierarchical system of sexual value)。
《打开心世界》
人类并不是在处理所有日常生活的问题上都会如此。一个人喜欢吃甜还是吃咸、一个人喜欢足球还是篮球,甜咸之间、足球篮球之间并不会存在高低之分,更不会导致偏好不同的人陷入有利或不利的道德处境。
但是,在有关性的问题上,人类却顽固、偏执地为不同的性实践强加了道德与价值的排序:有的性就是更高级,有的性就是更低贱。并且人类绝不仅只关注自己的性,人类还关注其他人的性,人类关注所有人的性。
人类对其他人在看不见的地方、在私密的环境中所采取的性动作保持了疯狂的好奇。他们不仅会指手划脚、不仅会道德评判,甚至在可以的时候,还会不厌其烦地订立法律条款,惩罚那些所谓“偏离规范”的性(sexual deviation)——哪怕这些动作的当事人之间分明就相互同意、也没有人受到伤害。
“性的价值等级体系”是历史的结果。以传统的父权制社会而言,居于价值金字塔顶端的性,是单偶制的、婚姻以内的、异性恋的、同辈之间的、以生育为目的的,而非娱乐的、不避孕的、在私人场所展开的、不使用工具辅助或助兴的、只发生男女生殖器官交媾的性。
这里所涉及的一系列指标,当全部被满足的时候,这样的性就会被评价为好的、正常的、自然的,当事人能够获得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的支持。
然而,当这些指标一个接一个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这样的性以及它的当事人,就会在道德排序的阶梯上一步接一步地向下滑落,从不体面的、到有伤风化、到不正常、到性变态、直至犯罪。这些指标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是全部加在一起算总分,而是很多时候带有“一票否决”的效果,一处不合主流,就要承受指责乃至付出代价。
直到1970年代,在美国的有些州份,哪怕是婚内的、夫妻之间的、私底下的性行为,如果当中涉及到口交或者肛交,当事人属于犯罪,理论上刑期甚至可以高达20年之久。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例子,但看看我们周遭熟悉的道德环境,人们为了一处千方百计打听回来的、属于毫不相干的他人的“不符规范”的性细节,而对其大搞道德批判、试图让其“社会性死亡”,这样的日常舆论难道还少见吗?
《打开心世界》
鲁宾对于色情制品、性虐待、性服务的宽容,首先即是来自对“性的价值等级体系”的反对。在鲁宾看来,性消极女权主义者、反色情女权主义者对很多具体性实践的批判,其方式、方法、以及权力目的,与历史上的父权文化别无二致,是“再造了保守主义式的性道德”。
性消极女权主义者同样创造出了她们的性价值等级体系;只不过在这个体系里,占据金字塔顶端的“至善的性”,由“男女之间的异性之性”变成了“女女之间的同性之性”而已——毕竟根据德沃金式的对异性性行为的警告,唯有女同性恋之间才有机会摆脱男性性权力的阴影。
性消极女权主义者缺少了性解放运动中的宽容与多元视角,她们从女性立场出发开发出了新的性道德,却依然在用新的标准,重复着旧式的、为不同的性行为排列出高低优劣的沙文主义操作。
性偏离者,是因为父权而被迫害,还是因为女权而被压制,对她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哪怕女权主义者有朝一日真的能掌有权力,可是如果她们的愿望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等级体系取代旧的等级体系,那么人类的处境也不过是从一种压迫进入到另一种压迫而已。这就不是解放,这里没有解放。
“用新的魔法打败旧的魔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宾的论述推进到这个环节为止的主题。可是,德沃金式的对性的批判,其最关键的核心还是在于:处在历史上下文之中的人类的性,已经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男性权力的意涵,价值中立的、纯粹的异性之性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03.
通往解放还是奴役?
在同样的意义上,色情制品、性虐待、性服务同样自带偏见,女权主义者当然不可能不戴有色眼镜地看待它们。因此哪怕反抗者借用了与压迫者相似的武器,矫枉的努力也不能被简单等同于“试图成为新的压迫者”。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鲁宾又该如何继续完成她对性消极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呢?应该说,鲁宾对于包括女人在内的人类、其实现自身主体性的能力与愿望,会抱有更强的信心与更乐观的评估——
也就是说,鲁宾眼中的女人不至于会像在德沃金的描述中那样没有办法,鲁宾还是相信性解放的女人能够通过对异性性行为、性虐待、色情、乃至性服务的自主选择而实现身体自决与主权的,即便这些确实都有可能是不公平的舞台。
女人不是小猫小狗,人类社会千百年来都习惯低估、贬低女人,而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是最不应该重复这种针对女人的傲慢与偏见的。
鲁宾非常反感道德社会在性问题上的家长主义作风。她在《思考性》之中援引了一个现实案例:有一名男子,因为他在性虐待活动之中的鞭打动作,而被作出了严重袭击的定罪;但是这起案子其实没有任何受害者控告他,而是检方纯粹根据摄录下来的影片对其发起指控。
男子的上诉意见表示,这些性虐待动作,都是所有成年当事人共同同意的结果,这中间也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但是法庭驳回了他的上诉并表示:在袭击与殴打之中,是没有同意可言的;除非这种物理损伤是发生在“正常”的场景之中,比如橄榄球、拳击、或者摔跤。
法庭继续表示:同意是只能由拥有法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才能给出的;但是“众所周知”——法庭尤其强调了“众所周知”(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一个具有完整精神健全的正常人,是不可能自主同意接受这种针对其自身身体的伤害的”。
《时时刻刻》
言下之意就是说,当你接受在性虐待之中被鞭打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为了法官眼中的精神失常的“不正常人”,你就已经失去了完整的法律责任能力,你就已经没有资格代表自己作出同意了。
如果这都不算家长主义,那什么才能算家长主义?法庭将性虐待的鞭打与橄榄球拳击作比较的逻辑很难站住脚,同样也是众所周知,橄榄球拳击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巨大危险与长期损害,是性虐待的皮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相提并论的。
但是,当成年人自主地选择参与橄榄球拳击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他们精神失常、神志不清、竟然会想去参加这么高风险的活动;而当成年人自己想要享受被鞭子抽一抽的时候,他突然间就精神不正常了。
说到底,还是爸爸妈妈为你好,还是爸爸妈妈才有资格告诉你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还是社会这个“大家长”在独裁它的公民可以喜欢什么、又不可以喜欢什么。
与之相类似的正是,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难道真的就有资格为女人断言,她们所自主选择的异性性行为、性虐待、色情制作、性服务,这当中真的就完全不具有任何身体自决、自由意志的可能,而只能是被诱导而无意识、被压迫而不自知吗?
就算这些选择或多或少可能确实会导向权力不平等的结构性后果,可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主张强行为无数女人的自主选择强加道德评价,施加压力以期待她们为了宏大的事业而放弃个人的意愿,这到底是通往解放还是奴役的道路?
让女人因为有悖女德而为自己的性愉悦感到羞耻,对比让女人因为有悖女权而为自己的性选择感到羞愧,真的存在哪样更高级、哪样更正义的区别吗?
《燃烧女子的肖像》
在《思考性》里,鲁宾针对反色情女权主义者的一个章节,章节名叫“The Limits of Feminism”,“女权主义的局限”:女权主义者要知道自己的局限。
在文章结束之前,鲁宾有一个呼吁,她希望女权主义者不要把性别问题和性问题混淆。女权主义的优势在于处理性别问题,并且是“gender”、也就是社会性别的问题。但是在去到“sexuality”、关于性本身的问题上的时候,女权主义只是诸多视角的其中一种,它并不在性问题上具有超出其他视角的天然权威。
并且,将女权主义分析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习惯作战方式,沿用至更加精致、细微的人类性问题上,女权主义视角所具有的优势和它自带的缺点可能一样多。不同愿望、立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都有陷入沙文主义的机会和风险,女权主义也一样,女权主义者没有理由不警惕这一点。
04.
运动的尾声,历史的选择
以盖尔·鲁宾为代表的1980年代性积极女权主义者,与以安德莉亚·德沃金为代表的性消极女权主义者、反色情女权主义者,她们之间的论战决出是非胜负了吗?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她们双方的论点都各自展现了女权主义思潮的一部分重要关切,但是也都不能完整完满地回应对方提出的质问。
盖尔·鲁宾式的逻辑没有挑战德沃金对于“男女之性自带权力不对等”的剖析,德沃金式的主张也确实无法摆脱有无低估女性主体性、重复保守主义道德专制的嫌疑。
论战的悬而未决应该是可以预见的,毕竟这当中的双方思路,其实很明显带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对阵左翼进步主义的典型风格模式,而这注定会是无法彼此说服的漫长角力。
只不过,如果真要在女权主义阵营中也做左右翼的划分,可能会显得有点奇怪。尤其是考虑到这两者之间的“左翼”、也就是反色情女权主义,竟然会在现实政治中和更大的右翼、也就是和保守主义结盟,那就更加奇怪了。这会呈现出一个无法被连贯理解的价值光谱,就失去了作为有效模型的意义。
《燃烧女子的肖像》
但是现实的历史又作出了怎样的选择?应该说,两相比较,性积极女权主义者最终是赢得了更大的社会观念空间。女权主义者的性问题论战与分裂,标志着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走向尾声。
而在1990年代的第三波女权主义时代中,不少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性气质的态度,已经由第二波女权主义时候所普遍认为的“正是女性气质的要求导致了女人主体性的失落”,转变成了第三波时候的“女人大胆地展现女性气质也是自我表达的一种,而但凡自我表达都是对自身主体性的实现”。
作为结果的就是,你在1990年代遇到的女权主义者,会有更大概率比196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更女人”,更容易接受女性气质,也更有机会正面地、积极地看待性、色情文化、以及各种小众偏离的性乐趣。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回归?都不一定,但的确是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