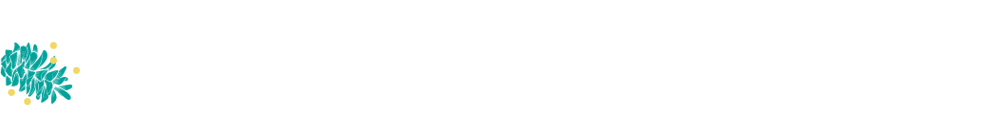这是发生在一个北大毕业生身上的真实故事。记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自己入院一个月的治疗过程,以及抑郁为什么会发生,怎样能让一个人柔软地被接纳并改变。
我们希望通过这篇稿件,打破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想象,也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人陷入情绪的困境,什么样的环境才能真正托住他?这不是一个“天才坠落”的故事,而是关于抑郁、治疗与自我接纳的日常叙事——它关乎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可能经历的风暴。
在精神健康成为公共议题的今天,这样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文图丨李一鸣
编辑丨雪梨王
从大学二年级到现在,抑郁症已经伴随了我七年——或许更久——无论我在其间是否承认过它的存在。我一直羞于承认“抑郁症”的事实,大概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标签,代表着否定和排斥。而且无论如何,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会因为抑郁症住院。
所以,当今年7月,我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听到医生说出“可以考虑住院”时,脑子像被电流穿过一般:我的工作怎么办,我该如何向家人解释这一切——我在想很多,唯一没想过的是自己——和此前走过的那些年一样。
症状
我住进的是回龙观医院28病区,正念静观医学中心。
来描述下我发病时的样子吧,其中一种是:蜷缩成一团,可能在椅子上,在床上,在地上,发抖,会抽自己耳光和打自己的头。目光呆滞,身子佝偻,行动迟缓,听到手机消息提示音就升起剧烈的恐惧。可以在不开灯的房间把自己关上一周,甚至更久。
住院前,这些症状进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高发期。
“你怎么又这样了?”“你能不能别这样?”“你又来了。”这些声音有时来自别人,更多的时候来自自己。我感觉自己跌入一个又一个深不见底的箱子,箱口一扇扇合上,光越来越少。
入院时签字的文件显示,我是自愿住院。“感谢《精神卫生法》,”我心里默念,“所以说我还没那么差对吧。”可有时候我就是想一差了之,在那些下不了床的时刻,我也想过住院,或是逃到一个没人认识我没人能找到我的地方,过一辈子都行,失去自由也行。
帮我办理住院的医生笑起来会眯起眼睛,露出一排上牙。她后来也成为我住院后的主管医生。28区在一间小院里,和其他病房一样,不能随意进出,但病人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参加治疗。更重要的是,能用手机电脑,能远程办公,她这样介绍。
病房内景
接下来的挑战是请假。住院之前,我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正常工作了。我没有能力让自己工作——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每天常常头晕头痛,昼夜颠倒,一天之内情绪总是大起大落很多次。在我毕业后的这五年,类似状况也数次出现,但之前,我把它们归结于我的拖延,而从未想过这是焦虑抑郁的症状。我会在深夜里突然踌躇满志,也会在阳光下感到我触碰不到自己对周遭一切的感觉。
走进领导办公室的时候,正是我感到全身麻木的时候。
“不用有病耻感。”领导说。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很多道理我都知道,比如说“别想那么多”“差不多就得了”“别放在心上”。只是当感官被那些黑暗的胶状物攫住的时候,这些声音被隔离在外了。领导说起他的前同事张进——一位已经离世的、生前患有抑郁症的知名媒体人。那一年,他去世的消息刷屏了我的朋友圈。后来住进病区,书架上还摆着他写的《渡过》等一系列抑郁症的科普书。
“张进刚得病的时候,大家都对抑郁症这种东西还没什么认知,”领导跟我说,“但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对抑郁症已经接纳了很多。”“真的么?”我心里想,然后小心地咬了一口他递给我的香蕉。大概是我没有尝试过被接纳,学校的角落,公司的卫生间,小区的地下室,都容纳过我的哭泣。
“反正医生让你住你就住,让你住一个月,你就正常请病假。”我能感受到他努力想让我放松一些,但我仍然坐在沙发上抬不起头。
“需要停薪留职吗?”这是我想到的最好后果。最差的是被开除,然后被整个职场拉入黑名单。在我看来,抑郁症等同于一种失能,而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我不能做不到,也不能做不好。很长一段时间,面对编辑对我稿件的修改意见,我就像看到试卷上的红叉。
“你去医院切个痔疮用停薪留职么?”他问。
一语成谶,我后来住院的时候真的犯了痔疮。这是后话。
角落
病区环境不错,院子里有好几棵柿子树,只是失去自由的感觉比我想象中难受得多。不能点外卖,定点从食堂订饭,指甲刀和鞋带都要收走,每天定时归还充电线,打火机锁进柜子,每天定点抽烟。有些时候我会想起三年前。
比隔离好些的是能社交,不好的是我当时的状态有些怕人。刚住院那几天,我老是在病区门口的角落处晃悠,听到其他人的谈话声,还会更加慌张。
病区小院
在抑郁状态中,我的身体像是被装了个“放大镜”——负面的自我评价会指数级放大,觉得自己“不配被喜欢/接纳”;对于陌生的环境,我也更加警觉,也许也会把过去曾被伤害过的经历投射进其他场景,总觉得身边有潜在的威胁,会下意识疏远别人,即便对方没有伤害我的想法。
即使面对别人的夸奖——我总会听到“你很优秀”“你都能考上北大”这样的话,但我习惯于在后面脑补上那句“那你怎么还能犯错”“那你为什么做不到最好”。“让自己做得好”,或者说“好”这个标准在时时刻刻困住我。做好一次是不够的,你必须永远展示出让他人满意的那一面。
“抱持”——提供安全感和情感心理支持——这是医生向我允诺我会在这一个月的治疗中感受到的。但我怎么就毫无感觉呢?
我需要让自己放心被接纳。在病房里,至少有一点好,那就是周围人都在吃药。共同的身份是安全的一部分。
让我最先感受到接纳的是医护。住院那天,因为迟到,我错过了取号。我战战兢兢地敲开医生的门,觉得自己一定会被责怪。但她只是帮我找了其他大夫帮忙,最后还让我帮她操作了一下电脑。“谢谢你,你看,让你进来还是有用的吧。”那一句话让我踏实了不少。住进病房后,医护们让我几乎感受不到是在住院,就连广播里对我们的称呼也是“各位休养员”——当然,后来我得知,会因病情轻重不同区别对待,并非所有病区都像这里一样。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很规律。7点起床,9点做八段锦,10点去做工娱治疗,14点做团体治疗,中间穿插包括吃饭治疗在内的其他活动,22点熄灯。但在真正适应之前,我依然感觉自己身处监狱,或者说,我一直被关在几面自己立起的墙里。
第一次发病应该是在2018年夏天,上大二。我在上课时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不敢去上课,幻想很多人都讨厌自己,很难完成论文,走在路上会突然哭泣。整夜整夜失眠,成天沮丧无力,像是支持我活动的绳子突然全断了。
过完暑假,我的状态好了一点儿,可以完成一些学习工作,但依然会突然“断电”。比如说曾经在一门课上,我坐在第一排,听一位我喜欢的老师讲有关社会越轨的内容。“患抑郁症的人都不会说自己是抑郁症的,说自己得抑郁症的人都不是真的抑郁症。”在讲到精神病与社会治理时,他说过这样的话。后来我能回忆起,这不是他的真实意思,但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
那个阶段,我没去医院,但会徘徊在挂号处的门口,心里想的全是如果自己被确诊,那所有人都会离我而去。接着骑上车离开,边走边哭。
惩罚
这里还要感谢一位在抑郁服药的同学。一段时间里,我拿他当作校园里唯一的同类。也感谢他的存在,让我在抑郁半年后,终于有勇气到校医院挂号。
前两次去门诊,我都只和医生说过一句话。第一次是面对“小时候有过什么不太好的经历吗”时,回答“我爸总打我”;第二次是面对“最近有什么不舒服”时,回答“我觉得我找不到工作了”。
第二次发生在2020年5月,毕业前夕。两次回答后,我就一直在诊室里哭。
但即便去过门诊,我也没有把自己当成抑郁症患者。大概我认为那是一种示弱,同时也确实没人看得出来我抑郁。是的,如果认识这位身体里有着你对天津人的一切刻板印象——说话时常阴阳怪气,动不动就讲两个冒犯人的笑话的人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觉得他有抑郁症,连病区里的病友都觉得我“看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住院期间每天的日程安排
可抑郁症就是一种容易被忽视、被隐匿的病痛。诊断结果显示,我在入院时处于重度抑郁、中度焦虑、恶劣心境的状态。
能看到我“肤下一面”最多的是我的伴侣。她和我说过她很疑惑,为什么在外面收放自如,处事游刃有余的人,到了亲密关系里就像“切了个小号”。
证据之一是我总是惩罚自己。我常会因为一点小事道歉个不停,无论事实上是不是我的责任。一旦开始道歉,就会进一步指责自己,持续地自我贬低。“你真废物”“你真垃圾”“快去死吧”这些话像泄洪一样从我脑子里冒出来,然后从我嘴里喷涌而出,继续指向我自己。
当然这些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地铁上或者在路上不小心碰到别人,我即便没说,心里也会道歉个不停,升起一股股对自己的愤怒,想抽打自己的念头越来越强。写稿时过了截稿日,我会觉得一下子天昏地暗,世界末日,然后感觉被打入了一小只黑箱,无法面对这一切。
后来我意识到,这大概是儿时行为模式的复刻。
小时候,我觉得只要考试没考好,整个人生就全完蛋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学五年级一次数学考试,我得了84分,回家后站在房间窗户框上哭,结果被父亲拽下来一顿打。每次挨打,打得最多的是头。后来在病房里,当我停不下来那些黑暗的想法而持续头痛时,也会砸自己的头,直到晕眩为止。
“模式”,这是医生给我总结的词汇。在很多行为背后,都有一些共同的模式。比如说,自己心里有一些严格的条条框框。这体现在我在地铁上对不守规则的人难以忍受,对自己无法按规定完成工作时的强烈自责,对那些“对错”的执着等等。这种条条框框的思维模式使我一次又一次像永动机一样,自动陷入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中。
“放下”,这是医生给出的方案——又是一个很多人都明白道理但做不到的事。当然有很多人和我说过“放松点”“别在意”“差不多得了”,可这些话在我耳朵里就像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一旦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事“做不到”,我的大脑就会像爆炸一样,崩溃而无法理性思考。
“你当然一下子做不到啦。”医生说,“先觉察。”她好像总是在微笑。
“你好像总是在担心别人,担心别人会生气,担心别人会讨厌你。那我想问问,在这些事情和思虑里,”她用笔尖在记录本上圈了圈,“你去哪儿了呢?”
接纳
是啊,我在哪儿呢?在我的治疗中,有一项是跟随引导语进行冥想练习。其中几句引导语的内容是“你可以爱自己,你的身体需要你的爱”。最开始的那一段日子,每次听到“爱自己”三个字,我就会条件反射式地头痛不止。
觉察的大概意思是,有意识地将注意力导向自身内在状态。这也是找到自己的过程。
我开始留意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了。在病区里,度过了最初的尴尬与谨慎,我开始和其他人打成一片。别人知道我是北大毕业生后,和我聊得最多的是韦东奕。
这里住着二十多名患者,年龄横跨高中到退休。我们每天一起排队做治疗、编绳串珠、写书法,定点放风吸烟,在院子里打球、摘柿子,像一个小班级。
娱疗室的一角
我好像不再恐惧集体。并且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面对别人的夸奖时,我不会再感到自责,也能接受其他人给予我的帮助了。有一次,我在病区里惊恐发作。一位护士拉起我的手,帮我梳理我为什么会在面对他人的冲突时如此害怕;一位大姐过来和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是咱病区的开心果啦”。
呼吸回到了我的身体里,原来我可以在别人的帮助下“好”起来。很长时间以来,我都给自己构筑起结结实实的壳子,告诉自己遇事必须靠自己,不能求助他人,不可以示弱,因为这些都可能会给我带来伤害。我总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面对父亲,我期待的是在脆弱时得到关爱与照顾,但迎来的是很多记耳光。
我开始面对从来没有敢面对过的、真实的自己。
很难描述究竟有什么“决定性时刻”让我在短短一个月“改头换面”。改变都在很小的地方。比如做陶艺时,我开始接受自己居然也可以有权利失败,比如团体治疗里的呼吸练习和身体扫描,让我开始触摸到自己的感受与情绪——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大脑麻木,感受不到它们。
娱疗内容包括陶艺、音乐、体育、书画等
那个“内在小孩”被从盒子里解救出来了。病区窗外的空地上,有一窝小猫。一只大号的橘猫妈妈和五只小猫,其中一个与众不同,我们叫它小白。有护士总从窗沿喂猫,我也和其他病友买了袋猫粮跟着喂。住院的时候,我总把那个还在从幼年期成长的自我投射到小白身上。它从来都不知道争抢,只会远远地看着,似乎对周围的环境最为警觉。
窗外的一窝小猫
我想让小白学会保护自己,至少,找回一些自我保护的本能。人是有很多保护自己的本能的,医生告诉我。比如说“战/逃”反应:人在面对威胁时,身体释放肾上腺素,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肌肉紧张,为战斗或逃跑做准备。而当威胁过大时,可能僵住不动,呈现一种“冻结”或“僵直”的状态。
我的状态更多是后一种。我总会因为将一些冲突或威胁幻想得过于严重——心理学上叫“灾难化想象”——而难以思考,甚至行走。但在那个住院的环境里,来自外界的几乎所有潜在威胁都被隔离在外,我能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照护。比如当我一次又一次陷入那种状态时,护士们会问“怎样会让你好一点”,告诉我“休息一下没关系”,病友们也会用他们的行为让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在。
允许、包容和接纳——这也是这个环境希望我学会的事情。
解缚
我经历的精神科是温柔的,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足够幸运。
心理治疗是我在病区里被应用最多的疗法。我会和其他病友一起静坐,尝试让呼吸穿过自己的身体,觉察它覆盖的每一个角落;会到户外感知温度、湿度和风,感受行走时重心的微妙变化。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接受这样的“治疗”。住进正念静观病区之初,我仍抱着“它不会是个宗教团伙吧”式的怀疑。对于住院,我幻想的是拘束、电击,比如说做几次MECT(电痉挛治疗),据说做一次那个,烦恼会伴随着那些痛苦的记忆,通通忘掉。
病区治疗室之一
这正是人们对精神科的刻板印象,或者说,历史与现实。
十九世纪以前,精神疾病患者在欧洲往往被当作“非人”,关进收容所,绑在床上或铁链上。直到法国医生皮内尔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通过医疗改革“解锁疯人”,人们才第一次提出,精神疾病患者应当以人的身份被对待。
但精神医学的现代化也伴随着残酷。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精神科迎来过一个极端的阶段。1935年,葡萄牙神经学家莫尼兹发明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人们更熟悉它的民间叫法:冰锥疗法。手术的方法是从患者眼眶旁插入冰锥样的器械,破坏大脑额叶的神经纤维,以期“切断”情绪与冲动的来源。在美国,这一技术一度被奉为神迹,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它被用于抑郁、焦虑、精神分裂乃至“行为问题”的治疗,患者成千上万。可其代价是巨大的:人格的钝化、智力的损害,许多人变成了“安静的空壳”。
当科学终于被种进更广大人类的大脑,对数据与“成效”的迷恋就替代了宗教,而这一狂热在如今社会的方方面面依然被广泛传播着。
在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被宣传和应用得最为疯狂的年代,这种本该是治疗严重精神病的最后手段,在民众心目中俨然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在日本,许多小孩子被家长送去做前脑叶切除术,而原因仅仅是家长觉得他们“不乖”。在丹麦,政府专门为这类“新型疗法”建造了大量医院,而针对的疾病则是从弱智到厌食症几乎无所不包。在情况最严重的美国,由于科学家们鼓吹“精神病要扼杀在萌芽状态”,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经过仔细检查就被拉去做了这种手术。更有甚者,将这种手术用在了暴力罪犯和政治犯身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手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仍在实施。直到现在,国内很多地方的安定医院原址,都因为监禁、拘束和手术所带来的对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被用作当地最恶劣的粗语当中。在我住院期间,病区主任曾在一次针对住院人员及家属的讲座中提到,在他从医的前二十年中,见证过神经外科手术在这片土地上的狂热,“人类总以为自己能做到对外界的完全掌控,但我们总是夸大了自己的能力。”
我想到了杨永信。在今天,没有任何官方消息透露他的去向。
在病房里,我能感受到我身体里的一些部分在悄悄软化。冲突与挫折不再天崩地裂一样将我轻易摧毁,我也不再常常让自己察言观色敏感多疑,而被牵引进他人的情绪之中。
当然,我也知道,这和我在病区里每天积极参加治疗,完成课后练习,阅读推荐书目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是的,即便那种“要做就必须做好”的执念已经消除,可我还是努力让自己成为了病区里恢复状况最好的那个。
患上抑郁的原因千奇百种,但其康复并不能依靠切除大脑的某个部分来达成。人是完整的、活生生的,而不应该是被现代性的种种体制拆解成一块块具备某些特定功能的零件。在回家的地铁上,看着周围滑动着手机的人,我想,谁身上没有点儿这个社会灌输给我们的焦虑和抑郁呢。
离开医院前,我来到窗边,和那窝小猫告了别。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小白,但我相信,它能照顾好自己,和现在的我一样。
运营 / 张媛 校对 / 李宝芳 美术设计 / uncle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