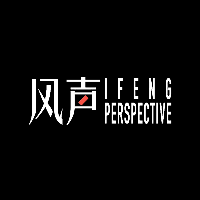作者|萧小壹
青年评论家
昨天傍晚,瑞典文学院将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挪威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他用极具创新意识的戏剧和散文让无法言说之事物发声。”
在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之后,国内舆论终于获得平息:一方面,绝大部分读者并不熟悉晓约翰·福瑟及其作品,暂且不说剧作在国内的阅读接受度,他八九年前在国内出版的剧作选早已被淹没在海量出版物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约翰·福瑟本人所拥有的实力与荣耀,几乎属于无需诺奖加冕的大师级人物。
这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与剧作家等于一身的挪威大师级人物,是挪威史上相隔九十多年之久的第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某种程度来说,这次诺奖的选择,让人既出乎意料,又让人不感意外:在过去十名得主中,欧洲作家占据其中六位;但福瑟所拥有的国际声誉,又让他的获奖毫无争议地实至名归。甚至,连约翰·福瑟自己在得知获奖之后,都自己宣称并不惊讶:“在过去的10年里,我已经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谨慎的准备。”
约翰·福瑟:让人内疚的作家?
对于约翰·福瑟是谁的问题,他自己曾作如是回答:“约恩·福瑟?谁是约恩·福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约恩·福瑟其人都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他既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和写作者。作为普通人的他与芸芸众生一样,有着自己卑微的,或快乐或不快乐的人生,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为某些人所知,但也有人从未耳闻;而写作,则只属于写作本身——与其说这是一种身份,毋宁说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既不与作为普通人的他,也不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相重叠。可是,那么,我到底是谁呢?约恩·福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十年前的2013年,约翰·福瑟曾经登顶博彩公司的赔率排行榜榜首,但那年的诺奖颁给了加拿大小说家爱丽丝·门罗。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福瑟一直都是诺奖热门人选,每年都有媒体声称当年应该轮到他了。
就在去年年初,《纽约时报》的评论就认为福瑟将斩获诺奖:“福瑟是会让人内疚的作家,你还没有听说过他,但有一天你必然需要读到,这事可能就发现于斯德哥尔摩在十月宣读之后”;去年年底,《洛杉矶书评》在访谈按语中就使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宣布福瑟将是下一任得主;就在昨天,瑞典评论家阿格里·伊斯梅尔也直言福瑟获奖的“太过明显了”;去年,译林出版社就购买了他的版权;颁奖前,世纪文景编辑就跟我透露他们押宝在他身上。
尽管如此,普通读者依然逃脱不了“约翰·福瑟是谁”的问题。暂且不说由于全球现实问题而让话题性著作不断升温,剧作本身在全球和国内也越发变得小众,更何况国内对约翰·福瑟的关注和接受也少之又少。
不过,约翰·福瑟的冷门印象,并不独属于中国的普通读者。在诺奖组委会面对全球读者发起的“你是否读过约恩·福瑟的任何作品”投票中,超过90%的人表示从未阅读过他的任何著作。故而,对约翰·福瑟毫无了解也不必“内疚”,毕竟全球读者都对他都是同样的陌生。
作为挪威国宝级作家,他已在全球上演过一千多部话剧,自己创作和改编了七十多部剧作,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乃至儿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是当代欧美剧坛最富盛名、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剧作家。
甚至,挪威政府为了鼓励和奖赏他的创作及成就,特意将一座皇宫宫殿献给他生活与创作,每年还拿出专项资金供养着他,奥斯陆酒店更是专门送他一套以他名字命名的套房任其随意使用,尽管福瑟对记者说他从没入住过,因为他有皇宫宫殿。而他斩获的奖项,囊括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戏剧奖、挪威艺术理事会荣誉奖、瑞典学院的北欧奖、国际易卜生奖等等。这些荣耀,足以说明福瑟获奖之后为何不再像往年一样陷入争议。
很有意思的是,因话剧创作而闻名世界的约翰·福瑟,并不喜欢甚至讨厌剧院。在创作剧本之前,他非常反对创作话剧。因为在他看来,当今世界的话剧充斥着保守,不过是传统剧本的陈词滥调而已。
他之所以闯入剧作行列,是因为生存状况出现危机而让自己不得不硬着头皮加入自己曾经厌恶的队伍。在此之前,他曾经加入过乐队,也进行过绘画,创作过诗歌和小说;如今,在经历过每年几乎一两部剧作的疯狂创作之后,他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被他称之为与快节奏的戏剧完全相反的“慢散文”(slow prose),借助这种不断变化的层次、场景和反思的风格,福瑟创作了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是《七部曲》(Septology),并入围了英国国际布克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
虽说陌生,但早在2010年,福瑟的话剧《有人将至》已在上海公演,他本人也在剧场最后一排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福瑟认为这场演出时对他作品的最佳呈现之一:“最能演绎好我的作品的,是东方的演员。最能理解我的作品的,也是东方的观众。”
除此之外,近些年来在全球掀起阅读狂潮以及国内文学圈知名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及其《我的奋斗2:恋爱中的男人》里,克瑙斯高回忆了他的创意写作老师约翰·福瑟。在他看来,约翰·福瑟羞涩寡言却智慧超群,但也毒舌至极,直接将克瑙斯高的诗歌评为除去某个词汇有点意思之外,其余都一无是处。
但没想到的是,这两位相遇于二十多岁的师生,都成了挪威最负盛名的在世作家:当约翰·福瑟说他诗歌一无是处之后,克瑙斯高对创意写作老师的角色也“反击”:作家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自己领悟成长出来的。不过,两人都记得,“我们一起喝了很多啤酒。”
世界的真相往往无法言说?
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里,“极具创新意识”和“让无法言说之事物发声”是对约翰·福瑟授奖评价的关键语句,不仅是针对他的话剧剧作而言,也用在了他的散文创作之上。也正因这种创新意识,当别人称他为“21世纪的贝克特”或“新易卜生”时,他如此回答:“这对易卜生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因为,约翰·福瑟自成一派。
一个有趣的八卦是,据说同样获得过诺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面对约翰·福瑟这等“极具创新意识”的作品时说:“他创作的现代戏剧,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舞台上说来说去。如果让我去写,我不会写这种类型。演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剧作家未必真能给自己写的东西一个明确解释,没有明确解释可能也正是作品张力特别大的原因。但是,这样的作品究竟能不能留下来,我很怀疑。”
连同样创作剧作且同样拿过诺奖的莫言都难以捉摸他的作品理念,何况普通读者呢?
毕竟,约翰·福瑟的话剧创作,对导演和演员的要求非常之高。由于他的极简主义写作风格,话剧角色几乎连姓甚名谁都并不知晓,他不赋予角色任何命名而只以男人或女人替代,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书写某种独特,而是在书写普遍的人性;而话剧人物又几近以独白的方式进行交流,独白与交流便构成了极端的矛盾,独白的台词又都是诗歌的语言,几乎以诗行的形式呈现,用象征隐喻的哲学方式去抵达人类普遍的困境与真相;除此之外,他的话剧中总是充斥着停顿的静场沉默,《死亡变奏曲》中竟高达近200次静场,借助留白的静默来让人去想象内心的活动或冲突的变化,以致于有人批评他的话语让人看完后心生抑郁。他对话剧的革新,让他游离于任何戏剧流派之外,而又建构了独创一派的戏剧语言。
这种沉默与独白的创作手法,与他所在的北欧挪威生存环境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
在被喻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挪威国度,由于高冷长夜和人烟稀少,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躲在屋内独自与自己对话,或者像他话剧中那样不断透过窗子向外发呆,缺乏日光的寂静暗夜与海浪击打峡湾的阴沉翻腾又加重了个人内心的自我思考。
在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的生存环境下,加上挪威社会的高自杀率,死亡、孤独与希望等关键词便成了约翰·福瑟创作的思考核心。而在福瑟看来,“语言无法匹配人类的情绪。”
对于约翰·福瑟来说,正如诺奖委员会的授奖词所说的一样,“无法言说”才是我们生活中最接近真实的真相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些尚未说出的部分往往比已经道破的部分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何他在话剧中乐此不疲地采取静场沉默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矛盾的真实状态,而不是借助激烈的对话来展现生活冲突的对决场景。
而且,约翰·福瑟的话剧也被诟病为“过于平淡”,他希望在日常平淡的生活场景中去展现更为真实的荒诞状态。在他看来,与其采取外在明显的戏剧冲突,不如注重刻画人际关系的内在张力,更能表现日常生活中那种竭尽全力而无法沟通的挣扎困境。无论是紧张冲突的代际关系,还是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抑或背叛、孤独与死亡的哲学本质,无需过多的戏剧化铺垫,只需要选取日常生活的瞬间便可完美捕捉出来,而且它们往往带着静默的诗意向我们袭来,拼凑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兵荒马乱。
除此之外,重复也是约翰·福瑟经常使用的创作手法。他往往借助同一角色的不同阶段来呈现人生的沧桑,或者将同一角色裂变出另一个虚幻的分体来表达命运的不确定性,用平淡静默而又充满张力的生活瞬间来刻画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将要面临的生命裂缝,因为那些人生的断裂时刻往往最为接近人生的悲欢,也更能呈现生命的脆弱和内在的挣扎,比如我们经受过的愛痛得失、挫败冲突与生死瞬间,往往更加能够反应人类灵魂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就像他在《三部曲》中借助同一人生的两个版本所呈现的追问:是什么造就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过着一种生活而不是另一种生活?
这种日常瞬间的断裂时刻,或者偶尔遭遇的沉默独白,构成了我们对意义的追问。
然而,约翰·福瑟往往借助虚无的困境来展现我们对意义的苦苦追寻而不得的歇斯底里状态。在他看来,如果人类能够获得交流的意义,或者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轻易便获取到意义,那么人类事务便不会那么复杂了,人类社会也不会如此不堪。用他的话说,“意义是奇迹”,关于存在方面的最本质问题往往没能给出真正的答案:“人们能够就此给出的仅有的答案都是矛盾的、毫无意义的,以我们有限的言语绝无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或许,最好的谈论某件事的方式就是沉默,单纯的空白——沉默所能传达的或许也是最准确的。”
甚至,在话剧创作之外,约翰·福瑟依然保持着对“无法言说之事物”的追问与探讨。在他2011年才写完的长达一千二三百页的巨著《七部曲》中,约翰·福瑟借助笔下的天才抽象画家说,伟大的艺术表达了“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发出了“无声的语言”,尽管我们或许可以凭借直觉来进行自我的理解,但这种“无法言说之事物”无法获得转述或解释,它的独特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它的神圣能够唤起“比生命更大的东西”。
尤其在刚刚经历过疫情禁足的当代社会,加上中西世界的矛盾冲突,全球化回归部落化,各国社会内部的隐疾暗痛也越发成为社会议题,社会个体因互联网技术或原子化生活而变得越发孤独,人类社会也似乎越发进入极化思维,约翰·福瑟从九十年代至今的作品,早已一以贯之地刻画着当下的我们必须面临的生活困境。
社会越是进入高速运转,焦虑的心理不断飙升,摆在人类面前的人性问题与生存状况,还有对意义的追问,更甚者是沟通交流的缺失困乏,正是21世纪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迫切议题。
否则,就像无政府主义者约翰·福瑟在接受美国艺术杂志《布鲁克林铁轨》采访时所言: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沟通,那么每个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是我们的幻想之一。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