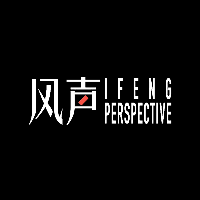作者|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上台之后,对美国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挥起了联邦大棒。特朗普政府一再打压、干扰多所大学,在高达数亿美元的联邦补贴以及其他支持政策将被取消的威胁下,许多被针对的大学选择了低头。
比如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特朗普总统指责其允许“反犹”示威活动在校园内盛行,批评该校没有对犹太学生提供足够的保护后,特朗普政府以停止提供4亿美元联邦资金相威胁,迫使其接受“整改”要求。2025年3月22日,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同意了部分相关要求以寻求继续获得联邦资金。
哥伦比亚大学的让步引来了诸多批评,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已经警告了至少60所其他大学采取类似行动。
当此“万马齐喑”,被针对的大学纷纷低头之际,哈佛大学奋起抵抗,成为全美第一个反击特朗普政府干涉的美国顶尖高校,自然引来了各方的一致赞赏。
智识与“反智”的斗争由来已久
哈佛大学于今年4月初收到特朗普政府“对付反犹联合行动小组”的一份清单,要求校方关闭多元化办公室,配合移民当局对国际学生的审查,并以总值约9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和政府合同相威胁。11日,哈佛再次收到行动小组的信函,进一步要求校方改革治理、招聘和录取程序,并审查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观点。
最终,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于14日正式拒绝有关要求,并向学生与教职员发表公开信说:“不论哪个政党执政,政府都不应干预私立大学所教授的内容、录取和聘用的人,以及对哪些领域展开研究和探索。”
特朗普政府随后冻结了为哈佛提供的22亿美元的拨款,同时冻结总值60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特朗普在其自家的自媒体平台上说:“哈佛甚至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像样的学习场所,它不应该被列入任何世界一流大学名单。”他这样解释何以冻结联邦政府对哈佛大学的拨款:“哈佛就是个笑话,它教授仇恨和愚蠢,它不应该再接受联邦资金。”
有趣的是,在哈佛站出来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代理校长克莱尔·希普曼同样发表了一份公开信,并表示,目前(哥伦比亚大学与政府)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哥伦比亚大学将拒绝任何“严厉的策划”,即“政府决定我们教什么、做什么研究、雇谁”,以及“要求我们放弃作为教育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哈佛大学对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回应再次彰显了美国高等教育一直秉持的对思想和研究自由精神的追求,也是对“追求真理”的哈佛校训的捍卫。
哈佛的校训是拉丁语“Veritas”,意思是“真理”。5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我每次到温德纳图书馆读书,中间休息的时候,就会信步走到陈列着约翰·哈佛先生藏书的纪念馆,默立良久,脑子里常常会不自主地闪现当年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
哈佛大学的创始人约翰·哈佛1607年生于今天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地区。1635年,哈佛在剑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被聘为牧师。1637年11月,他来到今天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的查尔斯顿镇,担任助理牧师和教导长老。1638年9月14日,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不到一年,哈佛就因肺结核而去世,死前将自己的图书和一半的房产(约合780英镑,相当于当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一年的税收)捐给当时的剑桥学院。
为了表彰这一善举,马萨诸塞大法庭于1639年下令将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这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300多年来,哈佛大学一直秉持着自由、开放,探求真理的精神,成为美国伟大的智识传统的一部分。
但今年特朗普再次上台之后,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告诉了我们,美国高等教育所彰显的智识传统虽然是美国社会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美国社会的反智传统也是其不可分割的另一面向,美国政界和普通民众的反智表现也让我们大吃了一惊。
“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这个词进入到论战语汇,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麦卡锡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950年3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幅漫画,漫画家用它指代毫无根据地诽谤和中伤。
历史学家也采用了“麦卡锡主义”一词,用它指代1950-1954年间,美国社会中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潮流——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表,毫无根据地指控和调查“政府中的共产党人”。
麦卡锡主义从1950年初的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前后共五年时间,其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了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麦卡锡主义诱发了美国民众的恐惧,认为知识界一贯的放言高论的作风,是有害于这个国家的。虽然知识分子并不是麦卡锡参议员攻击的唯一对象,但知识分子们无疑身处火线之上。每当麦卡锡尖锐攻击知识分子群体时,麦卡锡的追随者就会欢呼雀跃不已,在全国各地群起仿效,攻击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知识分子。
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反映出来的不仅有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以及两党政治的反共竞赛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社会固有的反智传统。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著名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以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专业眼光,写出了一本在美国并不受欢迎的历史学名著——《美国的反智传统》。
美国社会的4大“反智”思潮源头
该书出版于1960年代,使他再次斩获了普利策奖。这本书也凸显了一个矛盾: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几乎都在美国,而同时,美国却又有着广为人知的反智传统。在霍夫斯塔特看来,这个国家的成长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培养反智传统的历史。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霍夫斯塔特使用宏富的史料,以及各种各样的对比分析,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美国这个国家,成长于宗教信仰、民主体制、商业创新以及教育的普及。而有意思的是,这四点既是美国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推动反智传统的力量所在。
首先来看宗教信仰。美国立国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就是对宗教自由的追求。在这个追求过程中,美国先后摆脱了四种牵制自己追求宗教自由的力量,这四种力量分别是:欧洲的旧教会、天主教的旧体制、神学研究的旧思维,以及理解《圣经》的新视角。
美国宗教界人士不断地来到新大陆,摆脱天主教,并且不受原有知识的影响,单纯地以理解《圣经》内容作为信仰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甚至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知识传统,也一并归入旧社会之中。美国宗教界强调的那种理解《圣经》福音的途径,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的分析,而是所有笃信上帝的人的天启。
这种天启观念,造成了美国反智传统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说,宗教的传播在美国一开始就树立了感动胜于理解的超越知识的传统。
其次是民主体制。民主体制无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庸俗化倾向,这几乎是民主体制内在的必然逻辑。像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身上允文允武的精神,他们所为美国塑造的智识传统,也都被民主政治的浪潮所淹没。
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总是有人以反对精英的心态为由,不断强调政治领袖需要的是领导能力,而非满腹经纶的智识品质。这也是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人能够问鼎乃至再次问鼎最高权力宝座的重要原因。
第三,美国是一个追求商业创新的国度。“美国梦”所强调的白手起家追求商业上的成功,最关键的是个人的努力不懈、踏实肯干。这里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待在学校里越久,做生意成功的机会越小,待在学校学到的不过是空头的理论,美国商业的创新,靠的是实干的人。
最后,是美国的教育反而促成了反智传统。在美国,教师这个职业不但不受尊重,而且还是明显的低薪。霍夫斯塔特说,在雄壮的美国社会,男性甚至不好意思公开自己想当一名教师的意愿。美国社会中的教育,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是任何科目的教学。甚至有些宗教的卫道士,对于学校中的科学与数学这些科目极为反感,认为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真理,一旦接受,就会对纯洁的心灵造成玷污。
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反智传统,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伟大的知识分子传统,都是同一个美国社会所具有的传统。美国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着矛盾的国家。正如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能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我想,现在到了检验美国社会同时存在这两个传统之下,是否还能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的时候了。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