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文化史研究中,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证价值常因“数据碎片化”被弱化,而仲红卫教授的新著《当代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变迁研究》)以图书馆、剧场、广场为核心,依托系统搜集的政策档案、统计报表与微观案例,将空间数据转化为“城市文化史的量化文本”,系统揭示了“空间形态—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的深度联动,为城市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以空间数据证文化变迁”的严谨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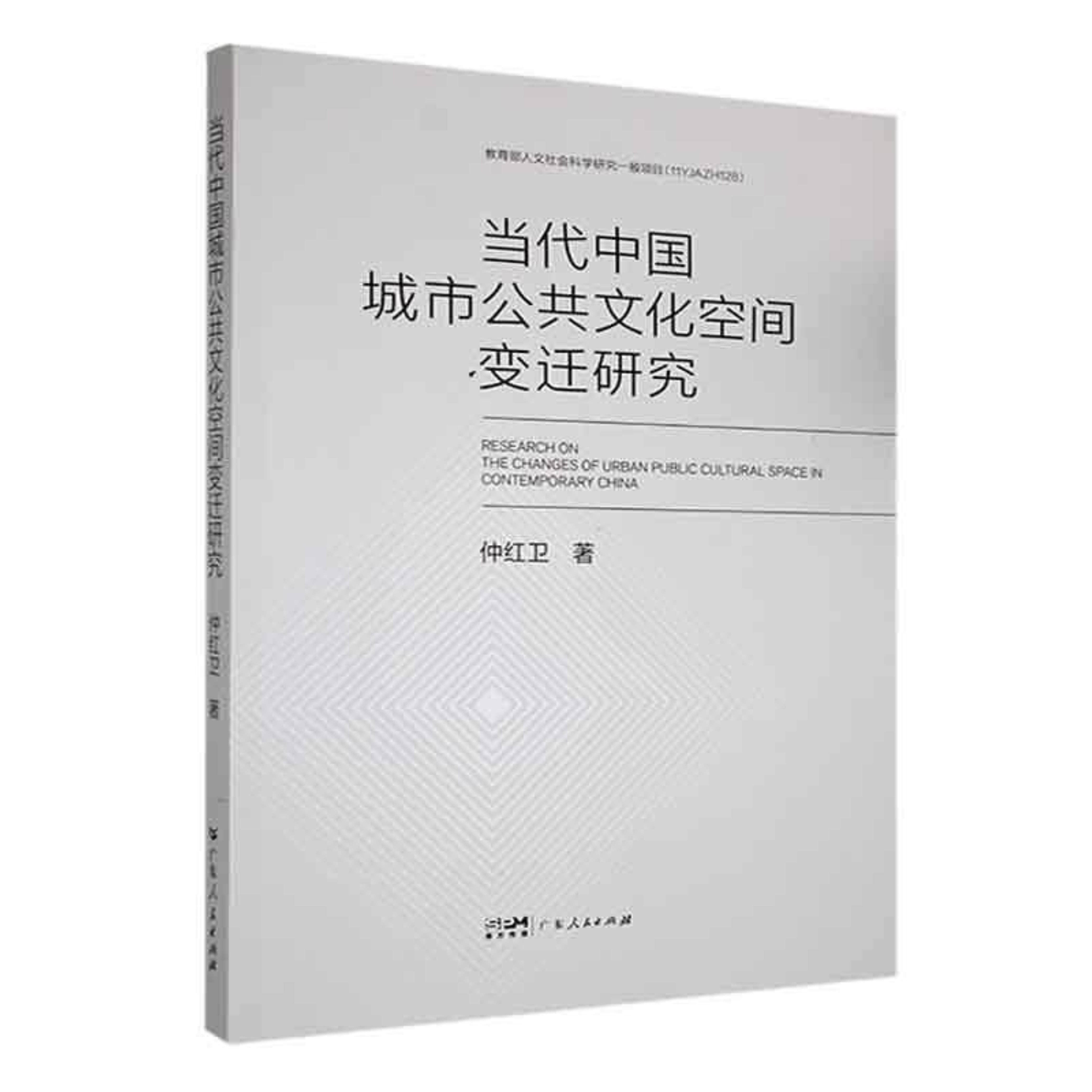
一、1949-1978:新政权文化认同的空间落地
1949年后,新政权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通过中小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填补旧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的“结构性缺位”,从而将“人民主体”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实践。
1949年后剧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印证了这一理论。作者指出,1949-1978年的剧场空间建设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非物理的空间建设,亦即由于戏剧活动的范围扩大而造成的实际上的文化辐射空间的扩大;一个则是物理的、物质的剧场空间的建设。”前者体现在“送戏上门”所拓展的戏剧空间上,如“国营话剧团在一九五四年专门为工农兵巡回演出一千余场,观众约一百余万人。六十八个国营戏曲团全年专门为工农兵做巡回演出五千二百余场,观众约九百八十多万人;终年在农村及工矿区活动的千余民间职业剧团,其演出场次当更多。……由于注意组织了工农兵到剧场观剧和‘送上门去’作巡回演出,话剧的演出阵地在逐渐巩固和扩大,戏曲的内容和形式也在日益丰富和改进。”后者体现在通过成立国家剧场建设委员会,以体制力量推动中小城市剧场建设——首先是缩小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在剧场数量上的巨大差异,如1949年浙江省纳入统计的46个城市中有28个没有剧场,而1958年该省已经实现县级城市剧场全覆盖,同时杭州市的剧场数量从1949年的14座减少到1958年的8座;其次是由省制定规划,分批次改善中等以下城市剧场的设备条件,如1955年省文化局拨款5000元将萧山剧院由草棚改建为瓦房。从文化史视角看,这种“空间建设—文化传播 —意识形态认同”的联动,本质是新政权通过“空间可及性保障”与“资源分配阶级导向”,将抽象的“人民主体”理念转化为基层民众可感知的日常空间体验,进而实现国家认同从政治话语到生活实践的下沉,深刻反映了新政权以空间为中介的基层文化治理逻辑。
二、1978-1998:市场化转型中的文化博弈
1978年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转向引发公共文化空间功能重构,文化生产从“制度单向主导”转向“制度—市场—市民需求”的多元博弈。书中收录的高校图书馆人才流动数据、地方大剧院运营参数等,为这一阶段城市文化史提供了有力实证。
高校图书馆的“人才流失”是市场化转型的直接体现。作者援引的数据表明:“天津高校图书馆专业人员中11%的人表示对图书馆不感兴趣,16%的人抱着有机会就走的态度,50%图书情报专业的毕业生已跳槽,仅1987年,天津市调出图书馆的人数是1986年的4.6倍;在江苏高校图书馆,只有13%的人对图书馆感兴趣,无兴趣而准备调走的占35%,1988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对北京、天津、长春、广州等地高校图书馆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只占47.8%,想调出者占39%。”在计划经济时代,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具有知识传播和政治认同塑造的双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焕发着神圣光芒。而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既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图书馆“知识传播+政治认同”的双重神圣性,也重塑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坐标系——部分从业者从“以文化为使命”转向“以利益为导向”。这种个体职业选择的转向,实质是公共文化空间制度公益属性与市场效率逻辑、政治价值旨趣与经济价值旨趣的多元博弈,折射出市场化转型中公共文化空间功能的深层重构。
三、1998 年后:数字技术赋能的文化平权
1998年后,在数字技术与公益政策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进入“公民公共性”阶段,核心特征是通过建设基于技术进步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经由“文化共享”而实现“文化平权”。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详细梳理了1998年后中国城市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历程,指出:“国家层面上,先后启动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工程’、‘全军院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等项目;地方层面上,广东省数字图书馆、辽宁省数字图书馆、上海数字图书馆、海南省数字图书馆等项目也纷纷启动。商业层面上,众多的电子或者信息或者通讯等等技术公司纷纷将数字业务作为主营业务,形成了数字化建设领域最为活跃的一股力量。到了2006年,我国数字图书馆已经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市,数字化建设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以广东省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为例:2017年该省成人馆中省级馆的数字资源本地存储量达到461.21TB,地市级馆达到2368.83TB,同时自建数字资源总量分别达到176.55TB和295.89TB,“已经建立起了覆盖全省的跨系统联合目录,实现了公共、高校、科技三大系统图书馆资源共享,并与广西、山东、福建、海南、天津等地区多家公共图书馆合作建立了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的无缝连接,服务对象覆盖全国。”数字图书馆通过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地方层面区域联动、商业层面技术支撑的三维体系,不仅打破了传统图书馆地域限制、馆藏局限的物理边界,更通过无差别资源覆盖,将文化资源从“中心城市垄断”转向“全民均等获取”。这种转型不仅是资源分配方式的变革,更是公共性内涵从群体专属到公民普享的质变,成为技术赋能下“文化权利平等”的具象实践。
《变迁研究》之所以启人深思,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在充分吸收西方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形成了自己的分析范式,即以“制度变迁—空间响应—公共性演进”为核心的“国家主导的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理论模型。譬如,作者在讨论1949-1978年图书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时,没有直接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而是通过详细分析1957年《光明日报》组织的关于图书馆性质的座谈会和上海街道里弄图书馆面向工农兵“开门办馆”的实践,指出这一时期影响图书馆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首要因素,是从政治上确立了“人民图书馆”的理念,并在此理念下消灭了图书馆的多元性并进而将其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由此催生了以主动满足工农兵需求为行动理念的空间拓展,即各种形式的“开门办馆”“送书下乡”行动。这充分说明中国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生产遵循着“制度理念—政策设计—资源分配—空间形态”的逻辑,本质是对政治理念与制度导向的主动响应,与列斐伏尔“资本主导空间生产”的理论迥异。这种尊重中国本土经验的治学精神,值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借鉴学习。
撰文:邓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