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宋学者张栻,一个对理学、书院教育以及湖湘学派有深刻影响的大儒,一个与朱熹相知相惜、交互颉颃而影响力被长期低估的思想家。800多年前,掌教岳麓书院的张栻,与远道而来的朱熹同台讲学,留下“朱张会讲”的佳话,由此开创了中国学术和教育史上的“会讲”传统。有意思的是,学界对张栻思想成就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张栻的确切出生地、生卒日及其名、字、号由来,往往被忽略。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立新研究宋明理学多年,慧眼独具,于此细微处设问探幽,将系列问题推衍成一部历史“侦探剧”。全文以《理学家张栻的生卒与名、字、号考述》为题,首发于《中国文化》2025年春季号。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全文转载,以飨学人。图中书影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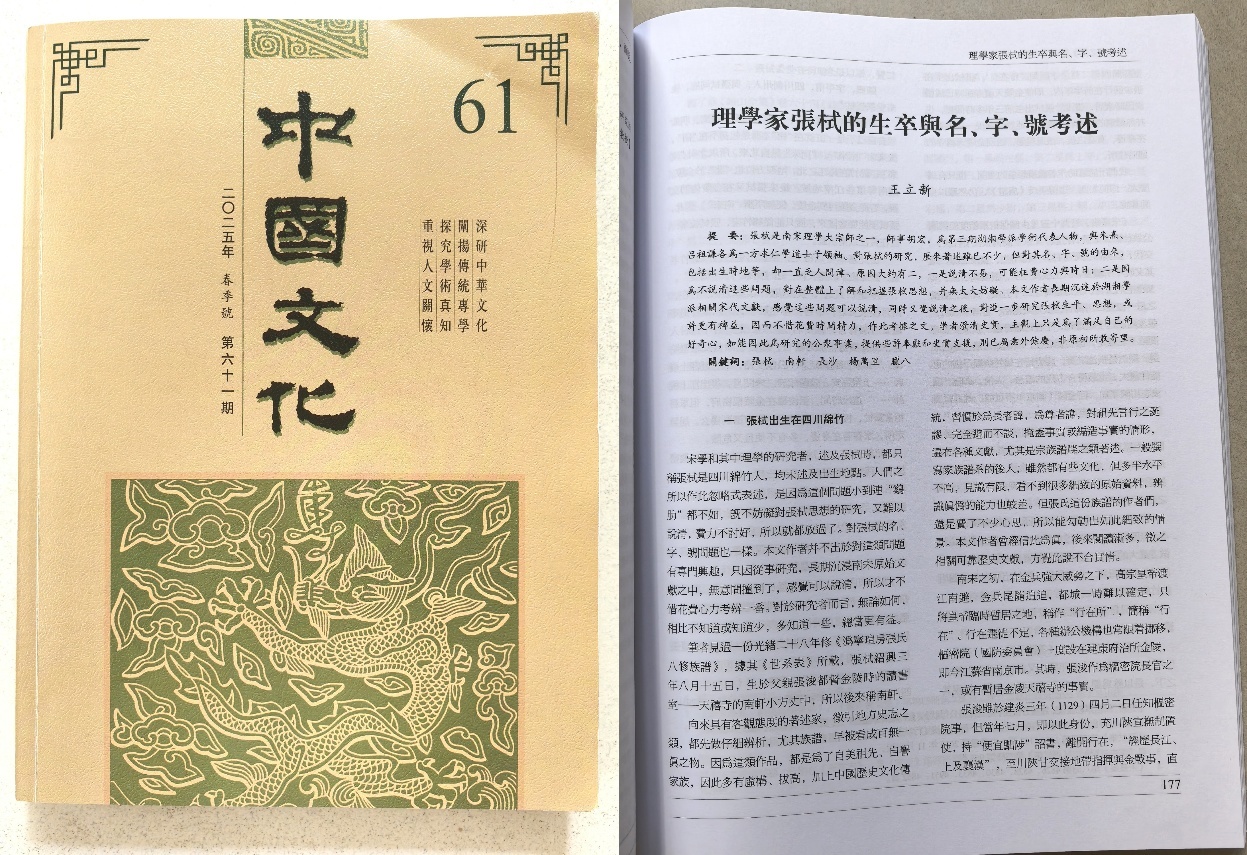

一、张栻的生地
宋学和其中理学的研究者,述及张栻时,都只称张栻是四川绵竹人,均未述及出生地点。人们之所以作此忽略式表述,是因为这个问题小到连“鸡肋”都不如,既不妨碍对张栻思想的研究,又难以说清,费力不讨好,所以就都放过了。对张栻的名、字、号问题也一样。本文作者并不出于对这类问题有专门兴趣,只因从事研究,长期沉浸南宋原始文献之中,无意间撞到了,感觉可以说清,所以才不惜花费心力考辨一番。对于研究者而言,无论如何,相比不知道或知道少,多知道一些,总会有益些。
笔者见过一份光绪二十八年修《沩宁瑄房张氏八修族谱》,据其《世系表》所载,张栻绍兴三年八月十五日,生于父亲张浚都督金陵时的读书室——天禧寺的南轩小方丈中,所以后来称南轩。
向来具有客观态度的著述家,征引地方史志之类,都先做仔细辨析,尤其族谱,早被看成百无一真之物。因为这类作品,都是为了自美祖先、自誉家族,因此多有虚构、拔高,加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习惯于为长者讳,为尊者讳,对祖先言行之诞谬、完全避而不谈,掩盖事实或编造事实的情形,遍布各种文献,尤其是宗族谱牒之类著述。一般撰写家族谱系的后人,虽然都有些文化,但多半水平不高,见识有限,看不到很多细致的原始资料,辨识真伪的能力也较差。但张氏这份族谱的作者们,还是费了不少心思,所以能勾勒出如此细致的情景。本文作者曾经信此为真,后来阅读渐多,征之相关可靠历史文献,方觉此说不合实情。
南宋之初,在金兵强大威势之下,高宗皇帝渡江南避,金兵尾随追迫,都城一时难以确定,只将皇帝临时暂居之地,称作“行在所”,简称“行在”。行在迁徙不定,各种办公机构也常跟着挪移,枢密院(相当于“国防委员会”)一度设在建康府治所金陵,即今江苏省南京市。其时,张浚作为枢密院长官之一,或有暂居金陵天禧寺的事实。

张浚虽于建炎三年(1129)四月二日任知枢密院事,但当年七月,即以此身份,充川陕宣抚制置使,持“便宜黜陟”诏书,离开行在,“经历长江、上及襄汉”,至川陕甘交接地带指挥与金战事,直至绍兴四年二月,才回到“行在”[1]。张栻出生在张浚回行在前半年,即使金陵天禧寺那时已成张浚临时家居,张浚于张栻出生前三年多时间里,也并无归家的机会和可能。只能设想张浚一直将妻带在身边,有身之后,派遣亲随,送回金陵天禧寺的临时住所。
我们所能帮助作者继续想象的空间,也只有这么大。即便如此,这份张氏《族谱》,仍然难以自圆其说。
《朱熹集》卷九十五《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以下简称张浚《行状》)交代,其与四位哥哥并非一母所生,张浚之母,是其父晚年所续妻,只生张浚一子,张浚刚四岁,其父已老病去世,其母当时才二十五岁。此后,张浚之母一直在四川绵竹,依外家过活。当南宋之初,张浚随朝廷不断迁转,不在母亲身边。张浚娶妻时间虽不能确定,但娶妻之后,照顾其母最合适的人选,显然是张浚之妻,将妻留在绵竹照顾母亲的可能性最大,也最符合古代的礼法、人情。那时,张浚在川陕军前,回金陵(南京)不可能,就近暂回绵竹看望母亲却有可能。
不妨再深推一下,张浚如将有身之妻送回金陵,也需要人照顾,谁有资格并且更可信赖?张浚母亲在绵竹,嫂嫂们也都不在金陵,将有身之妻单独送到金陵,由丫鬟们陪伴,张浚会放心吗?张浚之母会同意吗?
张栻自然不会出生在军前,这样会使张浚分心,妨碍军务,同时也会惹人非议。张浚不会这样做。最大的可能,就是张浚将妻留在绵竹或中途送回绵竹照顾母亲。也就是说,张栻出生在老家四川绵竹的可能性最大。
以上只是分析可能性,下面再就有效文献来判断一下事实。
《南轩集》卷二十六《答陈平甫》:“某自幼侍亲南来,周旋三十余年间,又且伏守坟墓于衡山之下,是以虽为蜀人,而不获与蜀之士处,以亲其仁贤,每以是念。……”[2]
陈概,字平甫,四川剑州人,与张栻同乡,后来受学张栻[3]。
“自幼侍亲南来”,张栻这句自述信文,明显包含自己不是一直就在“南”,而是起初不在“南”,后来才“南来”。“南来”是自北来,所以才叫“南来”。绵竹在长江之北,地理方位也“北”于金陵、湖南等这些江南地域。后来张栻又在金陵佐助父亲,若从金陵再到金陵,便无所谓“南来”。因此,张栻不能从金陵来,而只能从绵竹来,张栻后来一直在长江以南活动。
由此基本可以确定,张栻出生于四川绵竹老家,数岁后才跟随父亲一起“南来”、“周旋”。
再看《行状》,张浚绍兴四年二月回到行在,两月后被奏贬,不再知枢密院事,“以本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福州居住。……十一月十四日入见,玉音抚劳,加于畴昔,即日复除公知枢密院事。”重新回到朝廷。“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视师……上还临安,公留相府。未阅月,复出江上视师……”这段时间,张浚虽在金陵枢密府,但军务相当繁忙,接着又前往湖南,指挥清剿杨幺。居无定所,家眷若在身边,多有不便且又危险。
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丞相,仍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当年七月,张浚上奏杨幺已荡平,十一月,张浚还朝。绍兴七年九月,张浚被奏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建州太平兴国宫、永州居住。“太夫人以公退处,欣然从之,八年二月抵永,左右侍劳,凡所顺承亲意者,无不曲尽。夫人安之,不知其为迁谪也。”[4]
据此知张浚大约于绍兴七年底回老家,将母亲接出绵竹,于绍兴八年二月到达贬谪地湖南永州。张栻就应当在这个时候,才与母亲、祖母一道,跟随父亲一道南来。此时张栻虚六岁。这应该就是张栻《答陈平甫》信中所说“某自幼侍亲南来”的具体时间。也就是说,张栻绍兴三年(1133)出生在四川绵竹,绍兴八年初离开绵竹,从此再未回四川。

二、张栻的生日
前引《张氏族谱》,称张栻绍兴三年八月十五日生,后来感觉可疑,产生新想法,发现新材料,故于此处详细辨析、说明如下。
《朱熹集》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称张栻“淳熙七年二月甲申”卒,“卒时年四十有八”。宋人虚说一岁,淳熙七年二月在公历1180,倒推四十七年,知张栻生于1133,即绍兴三年。《神道碑》虽然未及张栻出生具体月日,但却有据可查。
乾道二年(1166)冬,杨万里自庐陵专程赴长沙看望张栻,期间曾与另外五位友人,在张栻城南旧家之南轩相聚,杨万里称作“南轩之集”。这次参与“南轩之集”的七人姓字,前已述及。其中一位侯彦周,是杨万里旧交。《诚斋集》卷四有《和侯彦周知县招饮》诗:
“乘兴山阴更灞桥,人间此事久寥寥。客心也欲将归去,小为故人留一宵。”
杨万里这次看望张栻,被大雪困在长沙,月余将归,临行前一日,被侯彦周请去家中饮宴,留宿了一夜。由杨万里此诗,知侯彦周当时是湖南某县知县。
张栻《南轩集》卷四有《寄侯彦周》,诗称:“塞雁仍南去,殷勤问耒阳,催科应独拙,理发讵能长。邑古弦歌地,年丰鱼稻乡。婆娑还得不,三径未云荒。”诗中有问“耒阳催科”事,结合杨万里诗,可知侯彦周当时是耒阳县知县。
“彦周”是字。《全宋词》有:“侯置字彦周,晁谦之甥,东武(山东诸城)人。南渡后居长沙。曾官耒阳县令。卒于乾道、淳熙间。有《嬾窟词》。”
侯置是位了不起的词作家,《全宋词》据汲古阁本《嬾窟词》,录其所作95首。其中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标注“耒阳至节戏呈同官”,说明当时正在担任耒阳县令。
侯置与张栻关系很亲密,《嬾窟词》中有《水调歌头》一首,标注“为张敬夫直阁寿”而作,全词如下:
“天地孕冲气,霜雪实嘉平。粹然经世才具,应为圣时生。妙处为仁受用,颠倒纵横无壅。一笑泮春冰,袖手无一语,四海已倾情。紫岩老,游戏事,悟诚明。当年夷夏高仰,玉振更金声。家有渊骞高第,可但闻诗闻礼,衣钵要相承。周扆绚余彩,商鼎味新羮。”
需要加句闲话,四库本《嬾窟词》所存侯置本首,与《全宋词》所“校辑”,有一个“词”不同,《全宋词》侯置本词中“当年夷夏高仰”,四库本《嬾窟词》作“当年华夏高仰”,大约是“校辑”时出现失误。
侯置在这首《水调歌头》词里明确交代,张栻生日在“霜雪实嘉平”。霜雪是深冬景况,嘉平为腊祭的别称,也就是说,张栻的生日,在腊月初八。
古人大约不像今人一样,年年岁岁总过生日,但赶上特殊年份,或者逢十、五岁时,多牛都很看重。侯置的这首贺寿词,当为张拭三十岁生日所事作。何以见得?因为标题称张栻为“直阁”,直阁,是直秘阁类官阶的简称。
朱熹为张栻所作《神道碑》,称张拭“少以荫补右承务郎,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张栻的上述职位,都是绍兴三十二年所获。就在这年冬生日前不久,张栻受到孝宗皇帝首次召见。召见时张栻奏称:“陛下上念租宗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也。栻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焉,毋使其少息也。则不惟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建炎以来繁年要录》卷二百称,“上大异之。”
有关张栻这次被召见,《宋史全文》和《续资治通鉴》均有同样记载。朱熹为张栻所作《神道碑》,载记更为具体:“上异其言,盖于是始定君臣之契。”
因为首次面见皇帝而且受到嘉赞、授官“直秘阁”,又逢自己而立之年,张栻心情高兴,回到金陵(南京)后,兴奋地将消息快速告知好友,以宴饮方式庆贺,实在情理之中。
侯置这首《水调歌头》的贺生词,盖即席间为张拭所作。四库本《嬾窟词》中,有不少描述金陵风物与集会之类词章,如《暮山溪•建康郡圃赏芍药》、《点绛唇·金陵府会鼓子词》等,说明侯置当年就在金陵,很可能也是张浚幕府中人士。
宋人虚加一岁,整十生日,逢“九”过。张栻生于绍兴三年(1133),绍三十二年(1162),既是张栻“而立之年”,且又逢其志得意满之时,侯置故而专门郑重作词致贺。
既已查证出张栻生在腊月初八,不妨顺此送给张栻一个有趣的绰号“张腊八”。料想张拭泉下未必介意,或因自己生日被查证出来,反觉高兴亦未可知。
三、张栻的逝日与疾症
魏了翁《鹤山全集》卷六十四《跋张宣公帖》:“公(指张宣公即张栻)……七年二月七日易箦。”
此说有误。《朱熹集》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以下简称张栻《神道碑》)明确交待称:“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阁修撰、荆湖北路安抚、广汉张公卒于江陵府舍。”[5]
查《宋史•孝宗本纪》和《宋史全文》,均称淳熙七年“二月癸未朔”。“癸未”既“朔”,则“甲申”为二日,而非七日。
张栻究竟死于何种疾病?
宋末赵溍《养疴漫笔》引《坦斋笔衡》,谓“张南轩晚得奇疾,虚阳不秘,逾年卒。就殓,通身透明,脏腑可数,莹彻如水晶。自昔医书,不载此疾。”[6]
看来可能是严重水肿,不知由肺、肾、肝何种病症所导致。大约是染上了肺疾。张栻安抚湖北之前,刚刚送走儿子。其子张焯,即因肺疾而卒,张栻料理完丧事后,才去江陵府赴任。

四、张栻与其弟之名
张栻(1133—1180)的“栻”,为古代占卜时日的器具,木质,亦称星盘。张栻的胞弟名“杓”,指北辰(北斗星)柄上三星。“栻”与“杓”,均非树木种名或普通木器,皆与占测时日及天候有关,均指把握“天象”以决定人事,俱含“操握天柄”以指挥下方之意。张浚不只自己“幼有大志”[7],为二子取名若此,立意同样高远。《胡氏传家录》载有胡安国当年教导子侄、门生话语:“为学当以圣人自期,为政当以宰相自任。降此不足议也。”[8]与张浚给儿子取名,可谓用心一致。只是胡安国明言不讳,张浚以取名方式隐约表达而已。明言不讳,更显直大刚勇;隐约表达,终不免遭人猜测,疑对权位驻心过深。
且看《宋史•天文志》:“紫微垣东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左右环列,翊卫之象也。一曰大帝之坐,天子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东蕃近闾阖门,第一星为左枢,第二星为上宰,三星为少宰,四星曰上弼,五星为少弼,六星为上卫,七星为少卫,八星为少丞。其西蕃近闾阖门,第一星为右枢,第二星为少尉,第三星为上辅,第四星为少辅,第五行为上卫,第六星为少卫,第七星为上丞。”
又有:“北极五星在紫微宫中,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为天枢,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枢星在天心,四方去极各九十一度。……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杓携龙角,衡卫南斗,魁枕参首,是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以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乃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原本也。魁第一星曰枢,正星,主天,主阳德,天子象。二曰璇,法星,主地,又曰璇为地。三曰玑……又曰一至四为魁,魁为璇玑,五至七为杓,杓为玉衡,是为七政,星明其国昌。第八星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见,……第九星曰辅星,在第六星左,常见。……”
魁星即极星为帝,另外八星名虽不同,但皆是辅星,佐帝者。
又称:“南斗六星,天之赏禄府,主天子寿算【或为筹算之误】,为宰相爵禄之位。传曰天庙也。丞相、太宰之位,褒贤进士,禀受爵禄,又主兵。一曰天机。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廷也。又谓南星者,魁星也。北星,杓也。……”[9]
张浚精研《周易》象数,对天文自有算计。在以天象比附人事的浓重传统氛围里,将两子取名栻、杓,明显有寄望两子,都能操持国柄,把握乾坤的用心。
张栻虽然精通义理,但在用天象比附人事这一点上,与其父张浚有同样的用心。在自己作成后,托付朱熹“审阅”、签名的父亲《行状》中,就有多处表现。如描绘其父出生前,其祖父“得异梦,若有告者曰:‘天命尔子名德作宰相。’”张栻父张浚出生后,其祖父遂据梦境为张浚取字“德远”[10];又称张浚再度罢相,被贬判福州,中途在江西余干赵氏家中休歇。六月末,“有大星陨于赵氏养正堂之北,光芒如昼。赵氏一家尽惊。”第二天张浚到来,后果逝于其家[11]。
取名既涉嫌“干天”,又常怀上述用心并书成文字,未免惹人生疑,遭人猜忌。此种情况张栻生时即有证验:“洎(张)栻复出荆南,(赵)雄事事沮之。时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张栻当之。’人愈忌之。”[12]
但张杓的“杓”,却经常被错写成“枃”,盖缘两字形近而易混。南宋文献,将张杓错写为张枃的很普遍,连《宋史》本传都没例外。
奇怪的是张栻也经常写错,不知是否为躲避猜忌而故意为之。如《悫斋铭》:“家君命枃以悫名其斋,而命栻铭以告之。”这篇文字不在《南轩集》中,是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九所载,也可能是刘昌诗书写错误。但朱熹为张浚所作行状,竟然也如此:“生子男二人,长栻,……次枃,……”张浚《行状》,显然是张栻手笔,朱熹只是润色、签名,如果误书,也是张栻误书,与朱熹无关,但也可能是刊刻致误。
未将张杓错写成张枃的不多,朱熹张栻《神道碑》属其中之一:“淳熙二年二月甲申……广汉张公卒于江陵府舍,其弟衡州使君杓护其柩以归葬……”[13]。朱熹作张栻《神道碑》,看上去比作张浚《行状》改动稍多,但底稿一定是张栻弟所作,他没有将自己的名字写错。没写错的还有魏了翁为张杓子张忠恕所作《墓志铭》,称张忠恕,“祖浚……父杓……”[14]。张忠恕临终嘱托墓志铭由密友魏了翁审核签名,而原稿一定是张忠恕之子张献之所写,张献之没写错祖父之“名”。
尽管宋人多将张杓错写成张枃,但“枃”虽亦木品,却为梳理线丝之器,即民间所谓“木梳”或“梳子”,与“栻”不在同一层级。以此判断,张栻之弟,实名“杓”而不名“枃”。但张栻同辈堂兄中确有名“枃”者,是张栻大伯父即张浚长兄之子。张栻同辈堂兄弟,均以木边单字作名,其大伯父张澥子张枃、二伯父张潮子张柶、三伯父张潞子张桿。此三位均为张浚亲侄。张浚另有同祖父兄张濩,其子张椿,为张浚堂侄;张浚同曾祖兄张注,其子名张棁,与张栻亦有联系。
宋人也有知道张栻弟名“杓”不名“枃”的士人。周密《癸辛杂识后集》称:“枃音进,凡织前授以枃梳,系使不乱也。出《埤仓》,见《唐韵》。近世张定叟所云则杓字,一点,三音标的,若非此枃字也。”[15]张栻弟张杓,字定叟。

五、张栻的字
张栻本字钦夫,后避钦宗庙讳,改字敬夫,准确时间,当在绍兴三十一年秋末冬初。
有关钦宗庙号所定时间,诸书说法不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一:“(绍兴三十一年七月)癸未,宰相陈康伯率百官为孝慈渊圣皇帝请谥于南郊。谥曰恭文、顺德、仁孝,庙号钦宗。”《东都事略》卷十二“绍兴三十一年”条下称:“金国使来,言皇帝去冬崩,圣寿六十一。七月癸未谥曰‘恭文顺德仁孝’,庙号钦宗。”所记相同。《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也将此事记在同日。
《三朝北盟汇编》卷二百九十,记在绍兴三十一年七月甲子。《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十九、《宋史·高宗本纪》,则记为同年九月甲午。《文献通考》单记七月,《宋诗纪事》卷九十八钦宗条,仅记绍兴三十一年。
本文作者以为,第一种说法应当是精准的。张栻改字敬夫,当在闻听靖康皇帝庙号确定之后。
据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十六《张左司传》:“三十一年春,命浚自便。浚归至潭,奉钦宗讳,号恸不食。”[16]但绍兴三十一年春,钦宗庙讳尚未确定,杨万里的说法是连带性的,其中有时间省略。钦宗庙号确定以后,通过官家朝报传递各路、州、县,传到长沙至少需要一个多月。
张浚曾任宰相,被贬之后尤其在秦桧病死之后,时刻寄望复出,对这类事件最当敏感。既得消息而“号恸不食”,数日之内,一定会给张栻改“字”,不会迟缓。
如果上述判断不错,那么张栻改“字”的具体时间,就应当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冬之际。此后的隆兴、乾道年间,刘珙、张孝祥、朱熹、吕祖谦等,依然称张栻“钦夫”,或不知其改“字”,而沿袭过去称谓;或虽知此事,而一时改不过来。这也说明南宋高、孝年间,避讳不很严格,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继续称张栻“钦夫”,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中有名“张构”者,也可证明这一点。如果避讳过于严苛,李心传的著作恐难通过审核。
六、张栻的号
张栻一生称“号”不少,主要有五个,一时习,二不二,三乐斋,四葵轩,五南轩。
(一)时习、不二
张栻曾自扁读书之所为“时习”,自扁卧室为“不二”。《南轩集》卷十三《名轩、室记》称:“名吾轩曰‘时习’……名吾室曰‘不二’。因书此自勉焉。”[17]取《论语》“学而时习之”和“不迁怒,不贰过”,虽然立意很高,但“张时习”或“张不二”之类自号,由外人称之,总觉不太像话,因此未得广传。此盖随父谪居,自连州再度转回永州时事,张栻二十岁上下。张栻那时虽然勤恳读书,但于取号自况,明显不甚在行。
(二)乐斋
“乐斋”是张栻第三个自“号”,后世有以“乐斋”为张栻另外一“字”者,本文作者从前未加辨识,草率袭用,后见杨万里载记,乃知其非:“乾道丙戌冬,予自庐陵抵长沙,谒乐斋先生侍讲张公……”[18]“乐斋”明显是号,不是字。杨万里这次拜会张栻归去后,又寄诗张栻,继续称其为“乐斋先生”,诗在《诚斋集》卷四,称《寄题张敬夫春风楼》,有“乐斋先生子张子,独立春风望洙泗。四海无人万古空,一声满天地不应”云云。
《论语•雍也》:“贤哉,回也!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绍兴二十九年,张栻裒辑先秦诸子书中有关颜回的言行,合成一部小书,赋名《希颜录》,以表达效法颜回的坚韧求道之志。绍兴三十一年,张栻得拜胡宏为师,顺将《希颜录》呈示胡宏。
胡宏特为作《题》:“敬夫著《希颜录》,有志于道。大哉志乎!”肯定其志向远大与“考稽之勤”,同时也告以“先贤之言,去取大是难事。”[19]指点张栻,有关颜回的言行,还是要以《论语》中的记载为主,先秦其他诸书中的说法,须经仔细辨别才能取用。胡宏还信告张栻,“于未精当处求精当”,将“学圣人”当成终身事业,只须孜孜不舍,不必急于求成:“天地日月长久,断之以勇猛精进,持之以渐渍熏陶,升高自下,陟遐自迩,故能有常而日新,日新而有常。从容规矩,可以赞化育,参天地而不过也。”[20]

既得胡宏勉励,张栻效法颜回,乐学圣人的情绪愈加高涨,遂将所居扁为“乐斋”,以此自号。具体时间当始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
“乐斋”实际处所,即在长沙张栻家中,亦即后来称作城南书院的张家宅院之内。该处住宅,是张浚绍兴十二年,为“奉母”于长沙城南所筑,共六十楹,张浚《行状》有记[21]。“乐斋”当为最南端一排房舍。
张栻后来不再称“乐斋”,盖与张孝祥有关。
隆兴元年(1163)八月,张孝祥之友赵再可,被任命为钟离县主簿。钟离在隋朝大业间为郡,南宋时降为县,属濠州,即今安徽凤阳。当时是金宋边线,常受金兵侵犯,几无宁日可过。亲友俱不希望赵再可赴任,赵再可却坚持要去。行前特意与张孝祥告别,称自己到任后,将于濠州“营一椽之屋以庇风雨”,并向张孝祥表达自己的想法:“夫濠上之乐孰知之?使吾于濠,官守得其职,固乐;不幸而不得其职,而不害其为赵再可者,再可亦乐也;又不幸而虏入塞,再可与民以心为城,择险而守,再可之志如此,再可亦乐;又重不幸,再可力不支而见得于虏,再可以得死为所幸,再可弥乐。夫无往而再可莫不有以自乐,再可兹行,其策得矣!”
张孝祥闻而感慨,为赵再可将“营”之“屋”命名“乐斋”,并作《乐斋记》以相赠:“彼纡珠怀金、驾高车、从卒吏,号称大官,平时冒爵位、取富贵,一旦赤白曩至,股栗心悸,谋自窜之不暇,闻再可之乐,可愧死矣!”[22]
后来张孝祥主政湖南,常与张栻共处,盖告知张栻,有人先以“乐斋”名所居,取为国忘身,风雷不动,生死不渝,皆会乐在其中。
张栻或因闻听此事,又见张孝祥为赵再可所作《乐斋记》,豪迈之气甚于自己,加以父亲去世不久,“乐”字不便常用,从此不再称乐斋。也就是说,张栻自号乐斋的时间,大约只是从永州搬回长沙城南拜胡宏为师之后的绍兴三十一年,到乾道四年(1168)夏前后。

(三)葵轩
“葵轩”作为张栻之号,学界似乎知者不多,但张栻确曾以此自号。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张浚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获恩湖南路“任便居住”,张栻随父从永州搬回长沙旧家。张氏在长沙宅第很阔,比后来重修的岳麓书院还大,内有池沼、园林之胜,张栻和朱熹题咏城南书院的相关诗歌,均可为证。张氏父子于自家待客厅堂旁,栽植葵花,遂扁客厅为“葵轩”。取意应出《诗·小雅·采菽》“乐只君子,天子葵之。”借葵花属性向阳,表达一心向君,忠诚不二。
《南轩集》卷一有《安国晚酌葵轩,分韵得成字》,显然是邀请张孝祥来家饮宴时所作,宴饮地点明标“葵轩”。张孝祥《于湖集》卷五《葵轩观笋》诗,正与上述张栻“分韵诗”合。《葵轩观笋》中有“黄梅四月雨”字样,虽然未标年份,但可推知作于乾道四年四月。因为《于湖集》卷十五《送野堂老人序》称“乾道丁亥六月,予来长沙。”而《于湖集》卷十四《金堤记》又称(乾道四年)“秋八月,某自长沙来。”由上两条,知张孝祥担任知潭州的实际时间,在乾道三年六月至乾道四年七月。中间只有一个四月,即乾道四年四月。据此推断,张栻不再称“乐斋”,而以“葵轩”代之的时间,大约就在乾道四年四月之后。很可能就是张孝祥这次赴张栻家宴,观其所谓“乐斋”,将自己为赵再可题名“乐斋”并作《记》之事,说与张栻。或即在此后,张栻不再称“乐斋”,而改署“葵轩”了。
张栻父子曾于葵轩前,置块状大石,既是景观,又表正直坚定。此事《南轩集》卷三十六《葵轩石铭》足可为证:
正尔衣冠,毋惰尔容。谨尔视听,毋越尔躬。尔之话言,式循尔衷。尔之起居,式蹈尔庸。敬尔所动,毋窒其通。贞尔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肃,攸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率从。天命可畏,戒惧难终。勒铭于石,用儆尔慵。[23]
张家院内虽很早便有葵轩客厅,但张栻自署“葵轩”时间,当在自号“乐斋”之后,亦即张孝祥乾道四年四月赴宴之后。此时张浚已去世五年。
《南轩集》卷十八《名周集说》有“乾道壬辰十一月甲申书于葵轩”[24]字样。壬辰是乾道八年,即1172。《南轩集》有《答陈平甫》两封,第二封在卷三十,是应陈平甫所求,开列书单,包括程颐、张载、朱熹关于《论语》和《孟子》的解说,胡安国《春秋传》、老师胡宏的《皇王大纪》,还有张栻自著的《洙泗言仁》、《论语解》和《孟子解》。自称所著《论》、《孟》解,为《葵轩孟解》和《葵轩语解》[25],这是张栻自署“葵轩”的又一证明。此信具体时间虽难确证,但大致在乾道末淳熙初则无问题,约略在1174-1175间。
后来人们虽主要以“南轩”称张栻,但仍有人知其曾经自署“葵轩”。
嘉定三至五年(1210-1212),曹彦约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任职期间,与胡大时交往深密。胡大时是胡宏季子,又是张栻门生。胡大时去世时,曹彦约曾作挽诗,其中一首如下:“天地开南学,葵轩接五峰。淳熙亡一鉴,盘谷有真踪。庭立心传鲤,门乘玉润龙。风流遮不断,堂斧若为封。”诗中“五峰”指胡宏,“葵轩”指张栻,“盘古”,则为当时湖南学者对胡大时的尊称。此诗描述的,正是湖湘学派真正创立后,三代学术领袖前承后继的情形。
(四)南轩
南轩,是张栻最末也是传扬最广的一号。此“南轩”,究指何处?此号因何而来?自何时而始?
第一种说法,指金陵天禧寺朝南小方丈室,张栻出生于此,因以为号。此说来自《沩宁瑄房张氏八修族谱》。
本文开篇已考证,张栻出生于四川绵竹,此说因而不能成立。退一步说,就算张栻出生在金陵,“南轩”的称号,也不应与出生地有关,因为如果有关,“南轩”之号早就流传起来了,可是直到此后二、三十年间,张栻仍在以“乐斋”、“葵轩”等为号,说明“南轩”之号,不是张栻出生即取。如果是后来为纪念出生地而取号“南轩”,亦不符合“号”之为“号”的取义传统。向来自取之号,多为警戒或激励、劝勉自己,故必待有人生自觉之后。如张乐斋、杨诚斋、陈止斋、李肯斋等。若为他人称呼而成,则必于已有成就和影响之后,主要以其读书、讲学之地指称。如胡宏被称五峰,陆九渊被称象山等。宋代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单纯以纪念出生地而取号的,实在很少见。
第二种说法,指认地点虽与第一种说法地点相同,都在金陵。但其理据,却不是因为张栻出生在父亲读书的南轩,而是因为后来他自己曾在这个“南轩”中读书。
此种说法又分两叉,两叉虽都指认张栻以“南轩”为号的南轩在金陵,但一说是保宁寺,一说为天禧寺。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张浚《行状》,张浚于绍兴三十一年十月重起判潭州,十二月,改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八日进封魏国公。此后世人尊称“张魏公”。隆兴元年(1163)正月九日擢枢密使,十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升任右丞相,仍兼枢密使,离开建康赴临安[26]。由此知,张栻随父亲在金陵居住的时间,主要就是绍兴三十二年前后近两年。相传张栻这期间曾于金陵两处暂住,一处在保宁寺,一处在天禧寺,两处均有朝南房舍,即所谓南轩。
东京学艺大学教授高畑常信,是宋代湖南学研究专家,在所著《宋代湖南学の研究》一书中,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相关中国地方史志,认真辨析了两处寺院在历史上的变迁。
高畑常信首先陈列历史上两种相传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出自嘉庆十六年刊《新修江宁府志》第九卷《古迹》,称南轩在保宁寺:“宋朝张浚开府时,其子张栻曾在保宁寺方丈的小室里读书,因此被称为‘南轩’。”
高畑常信考证,保宁寺自宋代已改名报恩寺,当时“位于城内新桥南,但到了清代嘉庆年间,已经不存在了。”【原文:“南軒、保寧寺に在り。宋の張浚、府を開く時、その子栻、書を保寧寺の方丈の小室に読み、南軒と号す。……とあり、保寧寺は宋代には城内の新橋の南にあったが、清代の嘉慶年間にすでに存在しなかったことがわかる。”[27]】
高畑认为,以保宁寺为张栻因读书处而号“南轩”的说法,起自清代,因而不足为信。
第二种说法,称张栻于金陵读书之所,不在保宁寺,而是天禧寺。
“袁枚序の乾隆十三年序刊《江寧県新志》(内閣文庫蔵)巻二十二、寓公伝には、張栻、宇は敬夫。忠献公浚の子なり。䕃を以て右丞務郎に補せられ、直秘閣に除せらる。孝宗、即位し、忠献公、府を建康に開くとき、栻、内に密謀を賛じ、外に庶政に参ず。……栻、建康に在りて、父を幹し、国を謀るの暇に、かつて城南の天禧寺の竹間に遊び、その清邃なるを愛し、石を掃い書を読み、名づけて南軒という。後人、因りて祠を建つ。”[28]
上引高畑原著文字,翻译过来意思是:
“张栻,字敬夫,忠献公张浚之子。以荫补官,任右丞务郎,除直密阁。孝宗即位后,忠献公在建康开府时,张栻内赞密谋,以参庶务……张栻在建康时,辅佐父亲参与国家事务,闲暇时喜欢到城南天禧寺竹林中游玩,喜城南天禧寺清邃,扫石读书,因而取号南轩。后人因此建祠祭祀他。”
高畑行文相当谨慎:
“关于张南轩在南京读书的遗址,存有保宁寺和天禧寺两种说法,也可能张南轩在两地都有读书经历。但因城内的保宁寺早已消失,而位于南门(聚宝门或中华门)外的天禧寺一直持续至清代,所以关于张南轩读书之地的传闻,多倾向于天禧寺。然而,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天禧寺已被真德秀和杜杲确认为张南轩遗址。可以认为张南轩读书之地正是天禧寺。”
这段说法的日语原文如下:
“さて、以上に見てきたように、張南軒が南京で読書したとされる遺跡は、保寧寺とする説と天禧寺とする説とがある。張南軒が読書したのは、どちらか一方ではなく、保寧寺と天禧寺との両方であったかも知れないが、城内にあった保寧寺が早く亡失し、南門(衆宝門、また中華門)外の長千里にあった天禧寺が清代まで長くつづいたために、張南軒が読書したのは天禧寺であったとする伝承が有力になったとも考えられる。しかしながら、それにもまして、張南軒が読書したのは、南宋時代にいち早く真徳秀と杜杲とによって、張南軒の遺跡として確認されている天禧寺であったと見る方が説得力を持つものと考えられる。”[29]
高畑所引袁枚的《江宁县新志》,虽然也是清代作品,但因袁枚是以南宋《景定建康志》为依据,《景定建康志》称,南宋真德秀曾确认张栻在天禧寺读书。该《志》还辑录了南宋杜杲所撰(建康府)《重建南轩先生祠堂记》。“人证”加“文证”,使高畑常信因此确信,张栻在金陵读书地点确为天禧寺,并顺此认定,张栻的“南轩”之号,得自于曾在金陵天禧寺南轩小方丈内读书。
高畑常信辨识谨严,无确凿证据不轻下判断,为学精神值得钦佩。但他忘记了一点,就是真德秀和杜杲的确认,同样需要辨析。宋代人错记同时代人与事的情况并不罕见。
《景定建康志》,是宋理宗景定年间,江南东路安抚司幹办公事周应合,受安抚使马光祖委托按照朝廷指令所撰,大约成书在1261年。中有《真德秀祠堂记》。真德秀于嘉定七到九年(1214-1216)间,曾任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于金陵建“贡院”,但未见其于金陵确认张栻读书处并“建南轩祠”事的记录,真德秀《西山文集》中,亦无相关载记。古人文集收罗不全的情况很常见,或许遗失亦未可知。但《景定建康志》却有杜杲于金陵修建南轩祠的记录。
《宋史•杜杲传》,称其“字子昕,邵武人”,曾任江西提点刑狱公事杜颖之子。本传称杜杲于理宗淳祐元年,以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乞去愈力”,不久“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景定建康志》称杜杲任建康知府的时间,为“淳祐二年四月”至“四年三月”,且收录杜杲所作《重建南轩先生祠堂记》全文,标注写作时间“淳祐三年”,即1243年“七月丙子”。此时距离张栻去世六十四年,距张栻随父居住南京时,有八十年余。杜杲所作《记》标示“重建”字样,似乎南轩祠在金陵原本就有。但《宋史•杜杲传》却作如下载记:“首谒程颢祠。总领所即张栻宦游处,陈像设祠焉。”观本传说法,似乎并无真德秀设祠于杜杲之前意味。金陵南轩祠,盖由杜杲所初建,似乎从前并无,就算有,也无关本文论旨。真德秀是否曾在金陵建造南轩祠,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真德秀的“确认”和杜杲的记述,应该不枉。张栻在金陵佐助父亲时,曾在天禧寺南轩读书,当属事实。高畑常信教授的考辨,应当是真实可信的。但张氏曾在金陵天禧寺南轩小方丈读书,就能说明张栻后来称“南轩”的南轩,一定是金陵天禧寺的南轩吗?张栻一生所到之处不少,这些地方或许都有南轩,张栻是读书人,这些“南轩”,可能都曾是他读书的场所。
惠民与兴学,是宋朝廷对地方官员的两大要求,也是宋代地方守令的两大政绩考核指标,同时又是地方官员表达自己忠君爱民的两个主要举措范域。除了剿匪、除恶、减税、劝农之外,为表达尊贤之意,并借以劝勉学子,用心圣贤经典,从而为曾在境内为官,或曾借居辖境内有影响力的古今先贤设祠,是宋代地方守令的惯常做法,也是他们赢得士林声誉的重要途径。行久之后,已成崇尚甚至“官规”。只要看几篇宋人所作各种《学记》,就能了解这一点。
杜杲任知建康府时,张栻去世虽仅六十余年,但却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得道真儒楷模。张栻又确曾在金陵天禧寺的南轩中居住、读书,杜杲自然会想到为张栻立祠,用来劝勉后学。杜杲这样做,是表达自己为官之忠敬、尽职,但却并不足以证明张栻被称作“南轩”,是因为曾在金陵天禧寺之南轩读书。
如果张栻果然由此自号,或因此被称为“南轩”,那么杨万里早就在金陵修建“南轩祠堂”了。

杨万里对张栻情深义重,虽然相互讨论义理不及朱熹、吕祖谦频繁,但与张栻感情深挚程度,实非朱、吕所能及。朱、吕为张栻的道义之友,而杨万里则是张栻的情义之交,道虽重而情更浓。
据《宋史•杨万里传》,杨万里于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初仕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杨万里是感恩戴德、知恩图报之人,曾不顾自身危殆,在朝堂上与翰林学士洪迈辩论,争取张浚配享高宗神庙。因为坚持过甚而又情绪激荡,颇涉触犯天威,至孝宗皇帝有“万里以朕为何如主”之语,因此被贬离朝,出知筠州。杨万里的刚直不阿,在当时人所共知,对朋友的情谊更如山高水长。他为张浚争取配享高庙,并不完全出于私心,理据也很充足,只是情绪过激。《宋史》称其性格“刚而偏”,后来在对待韩侂胄方面,体现更充分。当韩侂胄网罗天下士人之际,曾筑“南园”,嘱杨万里作《记》,且许以“掖垣”高位。杨万里竟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被贬归家之后,闻韩侂胄对金用兵,“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孝宗皇帝虽曾受杨万里冲撞,但深知其人,称其为“仁者之勇。”光宗亦曾亲书“诚斋”二字,赐赠万里。
绍兴二十九(1159)年,杨万里在永州结识张栻[30],从此密切往来,从未中断。乾道七年(1171)三月,閤们使、高宗吴皇后之妹丈张说,除官签书枢密院事。张栻时为侍讲,赴都堂指责宰相虞允文,坚持宋廷“内侍”不可干政“家法”,因此被贬,出知袁州。杨万里时为国子博士,“抗疏留栻,又遗允文书,以和同之说规之。栻虽不果留,而公论伟之。”[31]杨万里努力挽留张栻,未能奏效。
张栻去世后,在既不出于张家礼请,又不出自朝廷指令的情况下,杨万里自己忍不住,为张栻专门写了一篇传记,名《张左司传》。这种情况,无论在宋前、宋代还是在宋后,俱属相当罕见。杨万里跟张栻的个人交情之深重,以及对张栻了解之精细,由此便可知晓。
绍熙元年到三年(1190-1192),杨万里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官任和权责,同于二十多年后的真德秀。如果张栻果然因曾在金陵天禧寺读书而自号南轩,杨万里不可能不知道,既知道便不会不在金陵建造“南轩祠”,不必等到近二十年后的真德秀(1208),更不必等到五十多年后的杜杲(1243)了。何况杨万里任职期间,庆元学禁(1195以后)尚未开始,并无客观阻拦。
抛开理学成就,以及官位和世俗功名业绩不论,能交下杨万里这样一位通心共情的高格调、优品质朋友,张栻已经不枉一生了。可惜张栻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更看重朱熹和吕祖谦,他们要一起担待孔孟之道的弘扬和传承。张栻对于道统,远比对人间真挚情谊看得更重。理学家们看问题,多半都从价值、意义等宏大处入眼,很少体察微细的人间情感和个体生存感受。在这一点上,不同个体表现虽然略有所异,但整体状况并无太大差距。
由上所陈述可以肯定,张栻之号“南轩”,跟曾在金陵天禧寺南屋读书并无关系。金陵天禧寺之南轩,跟张栻之号南轩,并非同一个南轩,如同蔺相如和司马相如,名皆相如,实非同一相如。
但杜杲却在所作《重建南轩先生祠堂记》中,几乎认定张栻就是因为在金陵天禧寺南轩小方丈中读书,从而称作南轩。且看他的表述:
“……中兴以来,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开明大心;南轩先生张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与发明,以续周、程之学。于是道学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海之沛。妇人、孺子闻先生之名,皆知其为贤,譬之景星、麟凤。不以为瑞者,妄人也。凡讲习之地,皆有祠宇,崇尚严洁,足以启人之敬仰。百年之间,儒风彬彬,岂无自而然!独金陵天禧寺之侧,有屋六、七楹,曰南轩,实先生讲习之地。想其朝思夕惟,参前倚衡,天地之运化,圣贤之传授,父子讲求乎尊君、救时之策,友朋发挥乎垂世、立教之序,关百圣而不违,通万世而无愧。是轩也,岂容使之荒芜而不治?”
杜杲还在文末大张其势说:
“我宋立极,曰义与仁。教风德雨,太和蒸薫。笃生巨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学中兴。伊昔宣公,诵学斯轩。南轩之名,与道俱尊。胡未百年,栋宇摧倾。今我来斯,载瞻载颦。亟命匠氏,斩然一新。有隆斯堂,锵锵其门。像图惟肖,奠位妥神。遂使先师,不窘暑寒。牢醴时荐,觞豆序陈。岂轩之新,轩存敬存。礲石琢词,以告后人。”[32]
后人遂因此文,以为张栻的“南轩”之号,起因是曾在金陵天禧寺之南轩读书。日本学者高畑常信即因信赖杜杲此文,从而确认张栻的“南轩”之号,得自于金陵。
我们再来深入考量一下,当年张栻在金陵读书时,未及三十,思想远未成熟。当时张浚复出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不久又兼枢密使,又不久再升右相,正准备对金用兵,以图“恢复”。张栻当时“内赞密谋,外参庶务。”据杨万里的了解,张浚幕府中,虽“参佐皆一时之选”,但“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张栻)”[33]。可见张栻用心和繁忙程度。如此忙于军中重大事务,哪有可能另起炉灶,专注读书、讲学?就算当时有些来访者偶或谈及学问,但讲论学问,也绝不应是当时主要心思之所系。据此可以判定,张栻“南轩”一号的由来,实不当在金陵。
杜杲于建康府学中筑“南轩祠”纪念张栻,用以感召来学,举措自然可嘉,但遽称张栻绍兴三十二年(1162)前后便在这里自号“南轩”,应属渲染过当。
无论是真德秀确认,还是杜杲建祠并作《记》,其实都无法作为有效论据,用以证明张栻的“南轩”之号,是因其曾在金陵天禧寺南轩小方丈内读书。
张栻的“南轩”之号,另有来处,来自何处?来自长沙旧家,即后来的城南书院,那里才是张栻“南轩”称谓的真正由来处。
张栻在长沙旧家的“南轩”,杨万里是最早的熟知者之一,也是最初,也最有力的传扬者。
乾道二年(1166),杨万里专程赴长沙拜望张栻,在张栻旧家之南轩,留住一月余。杨万里有回忆性文字记录:
“乾道丙戌之冬,予自庐陵抵长沙,谒乐斋先生侍讲张公,公馆予于其居之南轩。”[34]
当时赶上长沙大雪,杨万里被困在长沙,“僵卧南轩之东窗,足未出门而心己入门。”于此期间,杨万里与张栻并张栻邻人及友人吴伯承、邢鲁仲、侯彦周,还有刘炳先、刘继先兄弟等相互往来,讨论学问、人生和时势等。杨万里后来称此事为“南轩之集”。
当时刘炳先、刘继先邀请杨万里赴家中作客,杨万里见其兄弟友爱、和洽,“雍睦、怡怡”,遂“索笔为书其楣间曰‘怡斋’。”刘炳先兄弟请杨万里为题《怡斋记》。因为住久天晴,杨万里将归庐陵,未能及时着笔。
九年之后(1174),刘炳先参加科举,经过庐陵,不知杨万里当时正在家乡,错失见面之机。又过三年(1176),杨万里同乡友人周直夫,自长沙归庐陵,刘炳先委托周直夫,携带书信给杨万里,称“顷失一见,甚恨。”刘炳先于信中,继续向杨万里催讨《怡斋记》。杨万里“得书喜甚”,顺便问询长沙旧友情况,方知侯彦周、邢鲁仲、吴伯承,“皆死久矣”。回想当年“南轩之集”,原本七人,却只剩“侍讲与予,与炳先兄弟四人在尔。”
杨万里大发人生感慨:“今侍讲官八桂,予居庐陵,炳先兄弟在长沙,交游之存亡、离合,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讲亦年过四十,炳先兄弟其尚少也乎?其亦似予之老乎?”以上是杨万里淳熙三年(未明标月日)所作《怡斋记》中话语。
详审此文,乾道二年杨万里专程赴长沙拜会张栻,张栻留宿杨万里在长沙家居之“南轩”。此时张栻尚未号“南轩”,所以杨万里因循旧日称谓,依然称张栻为“乐斋先生”。
杨万里于此文中,数次声称,曾居于张栻长沙城南旧家之“南轩”,且称当年七位友人,同在张栻家中之“南轩”雅集。张栻家之“南轩”,作为张栻长期读书、会友,包括讲学之真正的所在,自当由此渐为时人所知,亦渐为时人所重。
应该就是由于杨万里这篇文字的流传,世人才渐称张栻为南轩,时间当在杨万里作成《怡斋记》传回长沙之后,即淳熙三年(1176)以后。其时,张栻已不常住长沙,而在知桂林府、广西安抚使任上。
“南轩”不是张栻“自号”,而是学者对他的“称号”,是由杨万里这篇文字传扬到朋友间之后,渐渐被友人们叫熟而成固定称谓。
乾道三年(1167),朱熹赴长沙拜会张栻,可能也是住在张栻家中之“南轩”,但他并未因此称张栻为“南轩”。直至淳熙三年之前,朋友间书信往来时,还是满口“钦夫”、“敬夫”,未见有称张栻为“南轩”的记录。可见在淳熙三年杨万里《怡斋记》传扬出去之前,学者们仍未以“南轩”称呼张栻。
张栻当年都没有想到,乾道二年与杨万里等的“南轩之集”,竟然是自己后来得号“南轩”的导因。淳熙三年,杨万里同样没有想到,自己这篇记述与张栻等在张家之南轩聚会活动的文字,竟然意外送了张栻一个震响后世的雅号。由于杨万里在当时士大夫间的名望和影响,使得他所称说的张栻家的“南轩”,很快出名并传扬出去,成了人们对张栻新的称谓。
张栻最后,也是最响亮的一号,就是“南轩”,所指即是张栻长沙城南旧家之南轩。此号是被人们“称出来”的,如同其师胡宏被称为“五峰”一样,不是由自己“号出来”的。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张栻一生,自己取了那么多号,最终一个也没站住,倒是杨万里无意间作文,才使他得了一个流传千古的雅号。始所未料,料亦难及。当秋成之际,人们往往沉浸于丰收的欢喜,对于初春无声润物的知时好雨,却很少再会有人着意想起。
张栻去世,杨万里已不再称其为“乐斋”,而开始改称其为“南轩”。《诚斋集》卷一百零二《祭张钦夫文》称:“具官某,谨以清酌之奠,致祭于近故钦夫安抚左司之灵。……紫岩有子,紫岩是似。紫岩南轩,胥为后先。圣域有疆,南轩拓之,圣门有钥,南轩扩之,圣田有秋,南轩获之。……”

张栻谢世时,“南轩”之号已成流行称谓,广为人知了。
《朱熹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南轩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后书,犹未有他。不数日闻讣,则以二月二日逝去矣。闻之痛悼不可为怀。……”
陈傅良《止斋集》卷四十五,吊祭张栻之文,称作《祭张南轩》;
吴儆《竹洲集》卷十三,吊祭张栻之文,名为《祭张南轩先生文》;
彭龟年《止堂集》卷十六,吊祭张栻之文为《挽南轩先生八首》;
“南轩”作为张栻之号,已广为所传,几乎无人不以“南轩”称呼张栻了。
《陆九渊集》卷六《与包显道》,谈及张栻去世的感受时,亦以“南轩”称张栻:“南轩物故,何痛如之!近方欲通渠书,颇有所论,今遂抱恨矣。”
根据以上的描述与分析,可以肯定“南轩”作为张栻之号,初为人们所传称,约当在淳熙四年(1177)以后;而“南轩”所指,乃张栻长沙旧家即城南书院南侧读书之室,而不是金陵天禧寺、保宁寺或别处另外的“南轩”。并非哪里建了南轩祠,张栻的“南轩”之号就源自哪里;也并不是张栻曾在哪里的南轩里读书,张栻的“南轩”之号就来自哪里。
更有趣味的是,杨万里后来一直跟着别人称呼张栻为“南轩”,直到辞世(1206)都丝毫没有察觉到,张栻“南轩”之号的最早传扬者,竟然是自己。这也算是学林一件优雅的轶事了。
注释:
[1]《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朱熹集》卷九十五,第八册第4815、4821、4826页。四川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以下再引张浚《行状》,不另注出版信息,其他引用书目均依此例。
[2]《张栻集》第四册第1156-1157页,中华书局2015年11月出版。
[3]见《洁白堂记》,《张栻集》第三册第953页。
[4] 《朱熹集》第八册第4826、4828、4830、4833、4951、4852页。
[5] 《朱熹集》第八册第4544页。
[6] 魏了翁与赵溍说法,均引四库全书本。
[7] 《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第四册第72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8] 真德秀为袁燮作墓志铭,称袁燮“每谓为学当以圣贤自期,仕宦当以将相自任。”此语原本出自胡安国教育子弟、门生,只是略微降格借用。见四库全书本《西山文集》卷四十七《显谟阁学士致仕赠龙图阁学士开府袁公行状》。
[9] 以上天文星宿话语,分别在《天文志》,见《宋史》第四册第973、974-975、1011页,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出版。
[10] 《朱熹集》第八册第4801页。
[11] 《朱熹集》第八册第4895-4896页。
[12] 《赵雄传》,《宋史》第三十四册第12074页。
[13] 《朱熹集》第八册第4544页。
[14]魏了翁《鹤山集》卷七十七《直宝章阁提举冲佑观张公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15] 《周密集》第三册第9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16] 以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汇编》、《东都市略》、杨万里《诚斋集》等,均用四库全书本,或未出版,或未得见。
[17] 《张栻集》第三册958页。
[18] 《怡斋记》,《诚斋集》卷七十二,四库全书本。
[19] 《题张敬夫希颜录》,《胡宏集》第193页,中华书局1987年6月出版。
[20] 《与张敬夫》,《胡宏集》第234页。
[21] 《朱熹集》第八册第4857页。
[22] 《乐斋记》,在《张孝祥诗文集》第161-162页,黄山书社2001年12月出版。
[23] 《张栻集》第四册第1317页。
[24] 《张栻集》第四册第1037页。
[25] 《张栻集》第四册第1230页。
[26] 《少傅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朱熹集》第八册第4869、4875、4880、4889-4890页。
[27] 《宋代湖南学の研究》第194页。
[28] 《宋代湖南学の研究》第195页。
[29] 《宋代湖南学の研究》第197、198页。
[30] 杨万里《顺宁集序》,有“余绍兴己卯之冬,负丞永之零陵,偶过张敬夫……”云云。己卯,是绍兴二十九年。见《诚斋集》卷八十二,四库全书本。
[31] 《宋史》第三十七册第12863、12864、12868、12870页。
[32] 以上所引杜杲《重建南轩先生祠堂记》中话语,均在《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
[33] 《张左司传》,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一十六,四库全书本。
[34] 《诚斋集》卷七十二《怡斋记》,四库全书本。
*本文首刊于《中国文化》2025年春季号,凤凰网国学受权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