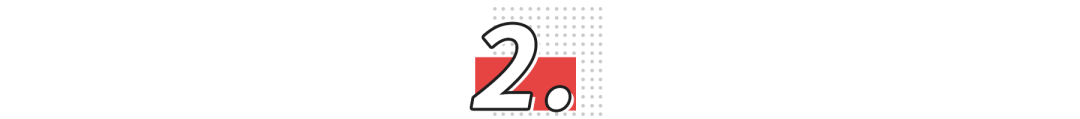文/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胡毓堃
核心提要:
1. 以杜金为代表、在后苏联时代再度兴起的“(新)欧亚主义”,是一个关乎俄罗斯文明与国家定位的宏大命题,在俄罗斯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欧亚主义的思想中,俄罗斯从来都不只是狭隘的(东)斯拉夫文明,也不是广义西方文明的成员,而是与东西方并列、平起平坐的“欧亚文明”。
2.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代表了欧亚地区特有的历史和多元文化传统,对过去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大意识形态中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保留和发扬,但去除了他眼中走向极端的“腐朽成分”,试图在这种“杂糅”的体系中寻找不同文化传统的融贯性,最终是要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
3. 学者认为,普京的“帝国热”所依托的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斯拉夫主义潮流,而并非杜金所设想的欧亚主义地缘范围,更不可能西至都柏林、南下印度洋。同样,在实际的国际关系环境中,俄政府更多地是利用“新欧亚主义”作为内部动员和对外行动的正当性论述,而非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
“普京的大脑”?他的思考超乎“大国外交”
“普京的道路上不再有反对者,如果有的话,这些人便有精神疾病,需要送去接受临床检查。普京无处不在,普京就是一切,普京是绝对的,普京不可或缺。”
这是俄罗斯哲学家、政治学者和战略家亚历山大·杜金在2007年对普京的评价。
那一年也是俄罗斯和普京的高光时刻:对于俄罗斯来说,国际油气能源价格持续飙升,带动经济连续第九年高速增长,GDP总量超过1.3万亿美元、人均GDP逼近一万美元大关,国家各领域的复苏势头明显;
即将完成上一个总统任期、未来生涯尚不明朗的普京,也因为其领导俄罗斯快速复苏、恢复国际影响力的八年,当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人物,后者高呼“新俄罗斯的沙皇诞生了”。
▎ 2007年,普京唯一一次当选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图源:TIME/Reuters
15年后,“二进宫”出任总统又十年的普京在2月21日的电视讲话,再度让西方舆论界惊呼其“重建俄罗斯帝国”的野心与行动。这一次,与普京一样引发全网关注的,还有被称为“普京大脑”的杜金。
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京所采取的地区对外政策与行动,几乎都应和了杜金曾经的“语出惊人”:
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爆发之前,杜金便访问了“火药桶”南奥赛梯地区,预测俄军“将占领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拿下整个国家,甚至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半岛,毕竟历史上它们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格鲁吉亚五日战火停止后,杜金多次强调俄罗斯应在乌克兰重复“格鲁吉亚的剧情”,毫不吝掩饰他对普京不能“扔掉另一只鞋”、“重建帝国”的气愤;
到了2014年10月,随着克里米亚入俄和乌东地区冲突的公开化,杜金宣称“只有大俄罗斯,即欧亚联盟之后,我们才能成为可信的全球玩家。现在进程减缓了不少。乌克兰的广场抗议便是西方对于俄罗斯整合进程的反应”;
就在俄乌本轮冲突尚未激化之时,杜金便在去年底发表了《大博弈中的乌克兰》一文,其中反对乌克兰国家历史存在的论调、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回溯、对于俄罗斯行动为”大地缘政治进程“的必要性阐释,与2月底至今普京的讲话和行动惊人的一致。
然而,如果把杜金理解为普京的”国师“和”外交政策制定者“,那便太过狭隘了。作为一名哲学家和当代欧亚主义的领军人物,杜金的关切,从来都不只是为俄罗斯制定外交政策。
▎ 杜金(右)被称作“普京的大脑”,图源:Modern Diplomacy
事实上,以他为代表、在后苏联时代再度兴起的“(新)欧亚主义”,是一个关乎俄罗斯文明与国家定位的宏大命题,在俄罗斯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俄罗斯思想史上,欧亚主义与融入西方“大西洋主义”和捍卫自身独特传统的“泛斯拉夫主义”具有相当的重要地位。与后二者不同的是,欧亚主义对俄罗斯文明的定位便是“非东也非西”: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欧洲,而是属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欧亚大陆。
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想,欧亚主义由斯拉夫主义发展而来,但又反对将民族主义作为俄罗斯文明建构的第一要素;虽然不排斥学习西方,但也不想用复制西方文明来取代俄罗斯的社会文化传统。
▎ 2019年杜金访问中国时所做的演讲内容。
简言之,在欧亚主义的思想中,俄罗斯从来都不只是狭隘的(东)斯拉夫文明,也不是广义西方文明的成员,而是与东西方并列、平起平坐的“欧亚文明”。
用杜金在其1997年代表作《地缘政治基础》(后成为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科书)一书的话说,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俄罗斯就是这个“欧亚帝国”的“心脏地带”,而他本人则用这本书重申了英国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1902年提出的“世界岛”和“心脏地带理论”。
英国《金融时报》更是在2011年煞有介事地指出,杜金的这种“重生俄罗斯”设想,不仅是苏联的重制版,更是呼应了英国著名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代表作《一九八四》中的“欧亚国”。
不可否认,杜金们的欧亚主义设想,源自于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观察,也的确呼应了这片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
▎2019年杜金访问中国时所做的演讲内容。
就俄罗斯的历史而言,“诺曼起源说”还是“斯拉夫起源说”,固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为不同的国家建构叙事方式服务,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斯拉夫人共同塑造的基辅罗斯,本就体现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的多元民族与文化交融的传统。
历经来自南方的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文化融合,以及东方的蒙古游牧民族统治,如今俄罗斯人也很难轻言自己是某种单一文明的复制品。加上俄罗斯历代政权在欧亚大陆上地缘政治权力和影响范围的变迁,自古典欧亚主义者开始,他们便将自己视为一个“民族融汇”的发展空间,一个本身的“文明有机体”。
因此,杜金们便可以公开表示,俄罗斯和俄罗斯(俄语)世界,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自己的“欧亚主义者”。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早期欧亚主义者,因为其强调“非欧性”,一度支持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认为秉持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神论的苏维埃政权是俄罗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而杜金在求学和治学生涯中,曾在不同程度受到海德格尔“此在”观念、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标榜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是古希腊文明所定义的“傲慢”。尤其是他在欧洲新右派的思潮中找到了多样性和等级制的正当性论述,将西方推行的自由主义、平等理念,尤其是以自由民主制为特征的“历史的终结”,视为西方基督教的虚假叙述。
▎ 比如杜金认为,自由主义正试图让身体的器官摆脱大脑的控制,需要将个体从理性观念与思考中解放出来。图自杜金Facebook页面
将自己明确定义为“保守主义者”的杜金,充分利用欧洲新右派、“深奥纳粹主义”(对纳粹主义的一系列神秘解释和改编)、宗教长青主义(存在恒久常青的哲学和智慧,且是所有宗教传统的起源)、德国保守革命(反对基督教平等主义、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和西式资本主义等现代性的多个面向)、超国家主义(对内支持威权、对外将本国本民族置于其它所有国家和民族之上)中不同的思想元素,反对美国的大西洋主义“文化霸权”及其对世界文明“标准化”的威胁。
▎ 在杜金眼里,“我们(俄罗斯)需要......回归神圣,回归新的中世纪——因此才能回归帝国、宗教和传统社会结构(阶层、崇拜、精神主导物质等等)。现代性的所有内容:是恶魔主义和退化。没有任何价值,全都应被净化清除。从科学、价值观、哲学、艺术、社会、模式、模型、‘真理’、对存在的理解、到时间和空间,现代性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现代性埋葬了一切。它应被终止。我们会终止它。”
杜金用《第四政治理论》描绘出他的新欧亚主义愿景和秩序:
不同于20世纪的三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欧亚主义代表了欧亚地区特有的历史和多元文化传统,对过去三大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传统和“民族特殊性”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保留和发扬,但去除了他眼中走向极端的“腐朽成分”,试图在这种“杂糅”的体系中寻找不同文化传统的融贯性,最终是要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主义。
为了抵御这些“西方但非普世“的价值观,以及“美国策划的第五纵队”,杜金这位东正教“旧礼仪派”的拥抱者,在斯拉夫本土信仰的影响下,发展出了自己的欧亚主义哲学,并在积极在其政治生涯中加以贯彻。
▎ 杜金与友人在1994年成立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图自https://antimodern.ru/dugin-aleksandr-gelevich/
无论是他自苏联解体以来便先后参与组建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和欧亚党,还是通过著书立说影响俄政府和军方的决策理念,亦或是他早在十五六年前便积极在乌克兰多地活动,发展欧亚青年联盟并因此遭到乌克兰政府禁止入境五年,杜金从来都不是一位纯理论家,而他的视野,早就超出了具体的外交政策。
更重要的是,生于苏联时代、求学于苏联晚期、治学于后苏联时代的杜金,见证了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地缘政治权力的衰退。普京口中“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也看在眼里,自然深知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俄罗斯无法抵御大西洋主义这个强大的敌人。
▎ 杜金与泛非主义领袖凯米·塞巴会面
同时,作为苏联时代的“异见青年”,看到列宁式的“苏维埃联盟”无法整合俄罗斯帝国的地缘势力范围时,杜金发展出自己的欧亚主义哲学,鼓吹高于血缘、超越民族但又基于地缘文明传统的新型欧亚政治共同体,成为他眼中抗衡西方霸权的愿景。
为此,他甚至提出要与土耳其为首的图兰主义文明圈结盟,联合伊朗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权力抵达印度洋,而在面对中国和东亚地区,他有些矛盾但不断调整的态度,也体现了这种浓厚的地缘政治逻辑。
从历史到哲学,从宗教到地缘政治学,不同学科理念和人生经历潜移默化的影响,便塑造了这个“普京的大脑”。
新欧亚主义来袭,世界如何认识今天的俄罗斯?
思想归思想、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杜金在90年代中后期办刊物,公开赞誉比利时政治学家让-弗朗索瓦·蒂里亚特所支持的“从都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甚至向南扩张至印度洋的欧洲-苏维埃帝国”,那时候恐怕主流媒体和各国政坛也就一笑置之。
然而,当俄罗斯开始在前苏联地区积极布局,从最西边的德涅斯特沿岸、到西南方向的高加索地区,从中亚再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逐步行动,当普京2014年说哈萨克斯坦是“(纳扎尔巴耶夫)在从来没有过国家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国家”,2022年再称“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造的”,全世界都感受到“新欧亚主义”的来袭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层面。
就连普京在2014年“瓦尔代论坛上”所说的“俄罗斯需要扎根本国传统价值观的务实的保守主义”,也让人很难不发现杜金的影子。
也难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发文,不仅正式提出了“普京的大脑”一说,认为杜金用自己激进的欧亚主义思想,为俄罗斯的“扩张”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开脱。
苏联解体后涌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确在近年来有来势汹汹之势,杜金现象引发的关注便是一个确证。当前的俄乌局势,近年来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实践,似乎都流露出一个“欧亚帝国”的野心。
但随着西方世界始终无法与俄罗斯形成良性互动,以致于乌克兰局势走到今天,更值得国际社会思考的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将要按照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指导思想走下去,世界又当如何认识当下和未来的俄罗斯?
关于普京是否在追求新欧亚主义的道路,早在其第一次担任总统期间便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和舆论界的关注。
美国纽黑文大学国家安全与政治学副教授马修·施密特早在2005年便发表了论文《普京正在追求欧亚主义政策吗?》,回溯了自彼得一世时期以来的俄罗斯身份定位问题,指出普京实际上有效地把欧洲-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引导至不同的方向:经济上融入前者主导的西方社会,而在政治与思想领域更强调后者。
尽管此文在当时便已经注意到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的行动,但作者认为这并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杜金式欧亚主义思想,而是一种介于欧亚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之间的理念。
毕竟时至今日,普京无论是谈及欧亚经济联盟,还是多次强调“乌克兰是我们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是同样的人民”,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个“大俄罗斯(俄语)世界”。而真正的“欧亚主义者宣言”,还包括俄罗斯历史学家、早期欧亚主义代表人物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口中的“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黑人”。
马修·施密特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普京使用的是“伪欧亚主义哲学叙事方式”,但俄政府不会贯彻杜金的欧亚主义运动及其政策理念。白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舒什克维奇也在2004年指出,普京针对前苏联国家特定政权的支持,并不是出于哲学逻辑意义上宽泛的欧亚主义,而就是一种“泛斯拉夫沙文主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苏联/俄罗斯及东欧问题研究专家金雁也曾就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新帝国综合征”进行过分析。她指出,在普京的内外政策与俄罗斯帝国时期看起来高度相似的背后,是“帝国价值”成为后苏联时代国家凝聚力的唯一力量。
随着后冷战时期国家领土的收缩、“特殊利益区”遭到西方的无视和打压,加上叶利钦时代的“非军事化、非布尔什维克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四大目标并没有换来预期的西方支持与援助,北约的东扩更是震撼了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令民族自豪感极强、具有弥赛亚救世情节、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罗斯人深受触动,为欧亚主义和帝国价值创造了市场。
这也能解释为何从左翼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到坚持自由主义的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如今都强调“帝国”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不可或缺性。
金雁所举的典型案例便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她在采访中发现“帝国”简直就是一个高频词汇:
“我爱帝国,没有帝国,我的生活很苦闷”,“在我们的精神细胞中,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因”。“俄罗斯需要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思想——帝国”,“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作为一个帝国存在”,“反正我是帝国主义者,没错,我想生活在帝国”......
但与马修·施密特相似,金雁认为这种“帝国热”所依托的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斯拉夫主义潮流,而并非杜金所设想的欧亚主义地缘范围,更不可能西至都柏林、南下印度洋。
普京本人也多次说过,“复旧的保皇主义”和“帝国的野心”都不可取,“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理解我们的国家利益所在,讲清楚,并全力争取”。
跳出学术界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与探讨,在实际的国际关系环境中,俄政府更多地是利用“新欧亚主义”作为内部动员和对外行动的正当性论述,而非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
去年,英国《国际政治》期刊便发文指出,自2007年以来,俄罗斯在外交实践中奉行的便是战略现实主义。在美国和西方放弃了北约不东扩这一口头承诺,而俄罗斯加入北约甚至欧盟的意图也被断然拒绝后,俄罗斯试图迅速恢复强国地位的目标也是基于现实主义考量,而非“欧亚主义”思想的图景。
至于俄罗斯近年来在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乌克兰乃至英国的活动,则是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下的常见做法:试探现有的国际秩序,再根据国际社会的反应,衡量得失,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因此,根据该文的总结,俄罗斯始终在做“战略性考量”,在避免与西方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对俄罗斯有“长期利益”和俄罗斯族人居住的“弱小邻居”采取行动。
这显然不能满足杜金宏大的“欧亚主义”帝国构想,也难怪他曾不止一次批评普京过于谨慎、保守、动作太慢。
与其说俄政府和普京沉醉于欧亚主义设想而冒进,倒不如说普京的现实主义撞上当下美国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价值观外交”,正在擦出越发激烈的火花。
▎ 叶卡捷琳娜二世,图源:Wikiwand
更重要的是,如今的国际社会早已不是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所处的时代: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得到公认,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赖,安全不可分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基本人权越发赢得重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谁也无法轻言改变......面对本国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状,俄罗斯的决策者们也应该知道“欧亚帝国”不是自己当下所能承担之重。
当然,没有人能知道“欧亚主义”在普京心中到底占据怎样的位置,杜金的理论未来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至少从过去、现在和可预见的后续发展来看,“欧亚主义”的确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自我身份定位的一种探索,或许可以为俄罗斯社会打上一针“兴奋剂”,但与“大西洋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类似,它现在谈不上是俄罗斯走向“强国之路”的“灵丹妙药”和宏大蓝图。